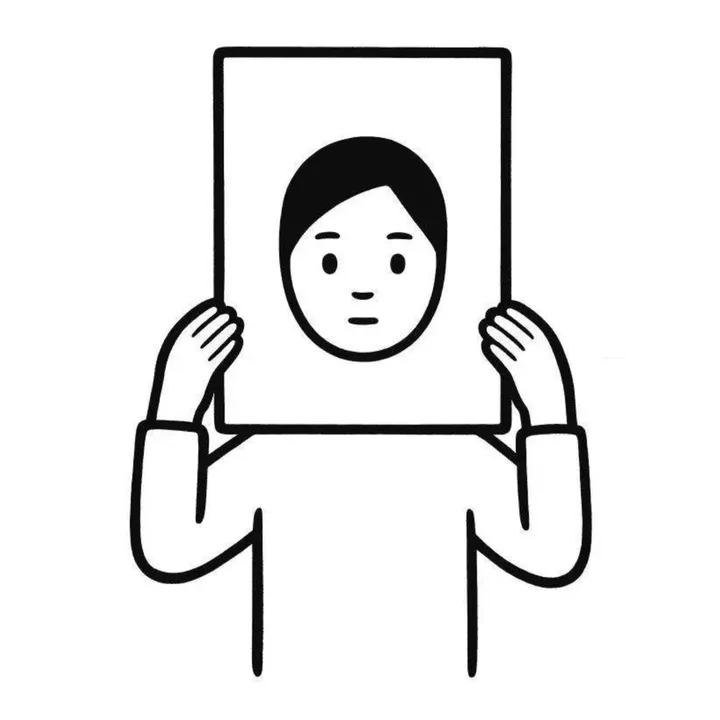为了新的马戏团节目,“我”找了个脸上有文身的女人当托,把胳膊放进老虎嘴里。但是训练过程屡生变故,「笼子」的存在成为人和虎都无法躲避的问题。
一进门我就找到了周丽,她在大厅角落里坐着,头发是蓝的,耳垂上挂有一对月牙形银质耳环,穿一件白色卡通体恤。走近看,更确信就是她,跟照片上一致,右侧眼睑下方有星形文身,一直延伸到太阳穴。两杯咖啡摆在小圆桌上,我那杯是美式,不加糖,电话里提前跟她说了。她看着我坐下,翘着的二郎腿摆平。我先拿起吸管,插进塑料杯里,喝了几口。我说,天真热啊。她说,给你要的大杯。我低头看了看,比平常我喝的杯子大了一号。我说,还没跟你谈酬劳呢,你这就破费了。她说,没所谓的,交个朋友,我也喜欢动物。
咖啡厅空调很足,后背下了汗,我重新打量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一些,个人信息里写的二十五岁,看着也就二十,也可能是穿衣打扮,比较潮。尤其是脸上的文身,当时发来的照片我就放大数过,还真是七星北斗,像个勺子印在脸上。照片上头发是黑色,现在是蓝色,加上星星和月亮耳环,怀疑是复刻了梵高的星空。这个女人有点意思,挺合我口味,不过这些外貌不作人物考量,仅仅算是我个人喜好。
周丽说,我就直说,你那儿老虎吃人吗?我说,不用怕,一点脾气没有,温顺得很。她说,我不是怕,就是好奇。我去过动物园好几回,每次看见老虎都好奇,那么个庞然大物,懒洋洋的,养得就跟猫似的。我接上话,说,还不如猫呢,猫还会挠人,我上次喂流浪猫,你看给我抓的。我伸出胳膊给她看,小臂上三道红印,还没褪完。周丽说,需要我做什么?我开始正式给她介绍。
我说,我们这不是动物园,你从网上应该了解过了,马戏团里的动物跟动物园里的不太一样,那个是散养,我们这都是笼养,还有每天的课程给它们安排,做动作,点头,作揖一类的,相对都很简单,每天都训,做对了给奖励。周丽说,搞得像培训班。我说,差不多一个意思,根据物种不同,项目也不同,比如说吧,狗熊,喜欢踩篮球,蹬单车,鹦鹉,就嘎嘎学人说话,猴子,玩倒立,还会喝啤酒。周丽插话,说,你逗我玩呢?我咬住吸管,又吸了几口咖啡,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牌,递给她看。她右手捞起来,凑近了念,李建德,国家一级驯兽师,顶真不?我指着这张证,说,实打实的,编号在这呢,国家发的,网上可查。周丽接着说,行,大师,你继续。我清清嗓子,接着说,我们安排的是钻火圈,三个铁圈,间隔两米,上面沾满汽油,一根火柴划拉燃,熊熊大火,小孟一下子钻三个,还能整一个来回,就是有时候惰了,跳得不起劲,背上的毛能焦那么一下子。周丽问,小孟是谁?我说,老虎,孟加拉老虎,黄色,黑条纹的,我叫他小孟,它自己也知道,但最近出了问题。
我摇着手里的咖啡,只剩冰了。周丽喊服务员,要再给我续一杯,我跟服务员说上杯水得了。服务员在柜台后面喊,我们这儿没有水,还要咖啡吗?我冲柜台喊,不要了,我等冰化一化,当水喝。周丽笑了,说,你挺有意思,说话都不在点儿上。我说,要不要听了?你认真点,也算是岗前培训。周丽说,行,继续。我顺着往下说,最近小孟有点罢工,火圈都燃起来,硬是不往上跳,主管拿着鞭子抽,我都心疼,屁股抽红了,硬是趴在地上不动。周丽问,打它,它不挠人吗?我答,不挠,挠也没事,指甲都拔掉了,跟用枕头砸你差不了多少。就是挺影响效果的,观众不买账,说就是来看老虎的,结果还是个纸老虎,这话我听了挺别扭,这老虎五岁半了,跟我时才两岁,算是我养的,谁要是说他不中用,我还真挺来气的。周丽说,你还挺仗义。我说,好了,关键到了,于是我想了一个好主意,你知道越南旅游,有个动物园项目,鳄鱼张大嘴,人把头放进去,提心吊胆的,观众又害怕又爱看,挺变态的。周丽说,明白了,你是想把头放进老虎嘴里。我说,答对了一半,老虎的嘴张那么大太累,放胳膊就行,得放你的胳膊。
周丽愣了一下,眼珠子瞪得极大,眼睑下方那颗星星都移了位置。她说,这老虎拔牙了没有?我说,没有,老虎不能拔牙,它还得吃东西,关键是锋利的虎牙加上你娇嫩的胳膊,这才是看点。我说完伸手拽住她拿着咖啡杯的右手,拉过来,看了看她白皙的胳膊,又觉得这么做是不是有点突兀,当即松开了手。周丽的胳膊像个弹簧般缩了回去。我说,你胳膊上没有文身呢。她说,身上还有。我问她,哪儿呢?她笑起来,说,我怎么感觉你这人有点毛病,还要体检吗?我连忙摆手,捏了捏瑞辛的塑料杯,打开盖子,吞进一口冰块。我咬碎冰块说,我就是对你的文身挺好奇的,怎么还纹脸上呢。周丽说,你家小孟脸上不也有个王吗?我大笑。周丽说,我还以为是找人给老虎梳毛。她拉回话题,于是我继续说。不能用现场观众,不事先培养感情,我估计小孟连嘴都不张,不知道是倔了还是老了,所以提前找人,到时候你就在台下坐着,不收你门票,我这边喊,有没有志愿者,你就举手,上前来,小孟一张嘴,你把胳膊伸进去,假装吓得不行,都得给你鼓掌。周丽说,明白了,当个托。我拍了一掌,说,还是你会总结,前期培训互动不给钱,后面表演一场给你五百。她的咖啡也喝完了,吸管抽出气流声,说,行,听着不费劲。
临走时我夸了她的文身,她说她老公给她纹的,确实是北斗七星,大概是怕她迷路。我又夸了她老公,挺有艺术细胞的,但心里想这男人也真下得去手,脸上的皮肤那么薄,这得多疼。出门后,再想起周丽,脑子里像有个橡皮擦似的,自动把文身从她脸上给擦除了,竟觉得这女人还挺漂亮的,小孟兴许也会喜欢。
马戏团并不是常驻,不过待这县城里也有半年了。大篷布就在西郊水厂那边,利用废弃红砖房搭建的,还算和谐,有种古斗兽场的既视感,除了表演中心,还有员工宿舍和动物厂房。老板先前还在,近两个月见不着人,遥控指挥,给我们发工资,有卡车给动物们定期送补给,除了特殊的饮食,一般我们也去附近村子买几只鸡鸭,像熊,老虎,这些都能将就吃。主管姓马,四十出头,叫马戏,开始觉得巧合,后面他说自己就是为马戏团而生,从小就喜欢和动物打交道,甚至懂得动物语言。我倒是觉得他纯粹瞎扯,手里拿着鞭子,别说动物,是人,常年被抽,也能懂得鞍前马后。除了表演的时候,急了他会抽小孟,其余时间,我不会让他打。那只老虎更像我的朋友,是一只大猫。表演下来,我领着它到后台,它都会自己走到笼子里,坐在自己屁股上,开始舔爪子。我扔只活鸡进去,它也不着急吃,一手按住它的翅膀,像和它玩一样。我就靠着笼子和它说话,往往也是些打气的套话。你真棒。你表现真好。你好乖。你超越了百分之九十九的老虎。甚至把手伸进笼子再拍拍它,它就把头靠上来,卡着铁栏杆,让我摸。手指插进毛发里,头盖骨温润,一下子意识到它是活的,但又如机器般顺从,多少生出了些怜悯,一只老虎,本该如此吗。等夜里,我回到厂房宿舍,能听到它低声嘶吼,饥饿裹住了它,那只鸡会被啃成骨架,我知道它在证明自己同样用力活着。
周天上午,周丽准时到了大棚布。她换了身装扮,穿着宽松的工装短裤,一双麻黄的工装靴,上身是带领子的Polo衫,戴一顶黑色的棒球帽。上衣很短,感觉故意买小了一号,能看到肚脐,肚脐上方有一条条黑线,又像是文身,向上辐射出去。她推我一把,说,往哪看呢?我没回话,把她往里领。厂房门口竖有马戏团的牌子,上面印有很多卡通动物,色彩艳丽,足够吸引人。四周每天喷一遍消毒水,里面掺了劣质香水,为了掩盖后场成片的动物粪便。周丽抽了下鼻子,说,这什么味道?我还是没回话,帮她撑开门帘。周丽站住了。我跟着她的眼神看。整个半圆形的表演场地,有五排交错递增高的塑料座椅,场地中间是一根巨大的铁柱,成年人腰那么粗,窜到天上,从顶端又垂下伞状的枝干,和座椅后面的砖墙相连,覆着红蓝的棚布。这就是马戏团活动中心,地面铺着柔软的细沙,动物踩着软糯,能舒缓情绪。穿过去,正对面,有另一扇铁门,动物都是从那里上场和退场的,包括道具,工作人员,还有马戏和我。我继续领着她走。她说,地方比我想象的大,你们挺场面呢,难怪能在这儿待这么久。这下我应她了,说,那是,你以为呢。马戏正从后场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根长鞭,后面领着一头黑熊,母的,圆滚滚,穿一条粉色格子裙,直立行走,脖子里拴着铁链子。步子迈得小,两只小手垂在胸前,挺滑稽。猛一看,这俩长得差不多,马戏也是个胖子,就是毛发不如黑熊旺盛,头发早已稀疏了。黑熊也歪头看我们,我喊它名,灰子。它翘翘头。马戏站住,灰子就俯下身子恢复了一头熊样。马戏说,你是周丽吧。我跟周丽说,我介绍过你。马戏解开黑熊脖子里的链扣,灰子一下窜出去,开始围着场地转圈,最终会去攀住立在墙角的一辆小自行车。周丽说,刚才我还害怕来着,现在看怎么像一条大狗。马戏说,所有看似凶猛的动物,都能训成一条狗。他说这话的时候抱起胳膊,显得很骄傲。我不太认同,觉得他嘴里的狗字,不只是另一种动物,在这里好像代表了一种妥协和愚蠢。马戏又说,建德跟我说过你的文身。他说着凑过来看,周丽的帽檐很低,马戏还要往前凑。我站过去说,差不多得了。马戏挺直身子,说,没见过嘛,头一回见脸上有文身的。我说,也算咱的员工了,有的是机会。马戏点头,说,你也是勇敢,我看你胳膊挺细的,不知道那头老虎牙缝够不够塞的。我说,去一边。接着拉起周丽的胳膊往后场走。
别怪他,干马戏团这行,好奇心太重,猎奇,才能想出点子,怎么让这些动物哄观众开心。我替马戏解释。周丽说,油腻。我说,对,你又总结对了。她把胳膊从我手心里抽走,插到短裤口袋里,说,感觉你还好。我笑起来说,那是你不了解我,没关系,带你了解小孟就行。
穿过一条走廊,有两道闸门,过了以后,味道就更浓了。所有动物都在一块,但后场空间倒是不小,算是另一栋废弃厂房,有宽大横置窗户,玻璃都被敲碎了,阳光可以随意穿透,动物喜阳。笼子与笼子间隔约十米,够宽敞,方便喂食和挪动。每个笼子底下都带有轮子,有卡扣可以锁死,因此也被抬高了十几公分,屎尿自然就落在地上。清理时,只需要推动某个动物,把地上的排泄物铲走即可。后来都懒,干脆直接掩埋,再把动物推回来,导致味道越来越重。老虎就在角落的笼子里,懒洋洋的,所有的动物都懒洋洋的,只有三只猴子在笼子里互相找着虱子。我对周丽说,到了。她打量着这些笼子。有两匹马,一头山羊,一只真正的狗,一窝鸽子,两只鹦鹉,三只猴子和老虎小孟。还有一个空着的笼子,非常大,高五米,她正在盯着它看。她问,这是关什么的?我说,大象,会踢足球,上个月刚走,得病了,不吃不喝。周丽说,挺可怜的。我说,还行,打了麻醉,就是安乐死,其实没啥痛苦,象牙还卖了点钱。她把帽子摘了下来,说,我说这些动物,都挺可怜的。我不知道怎么接这话,没有它们,我连饭也吃不上。我拿过她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她往后捋了捋头发,蓝色的海洋倾泻在肩膀,映着午后泼洒进来的光,像泛起层层的浪。
我敲了敲铁栏,盘卧的老虎伸长了头,喘出一阵粗气,哼哧哼哧的。我伸手进去,摸摸它的鼻头,红色越来越淡,有点干。我又看了看笼子里的铁盆,早上加的水保持着水位。我说,多喝水啊,这天多热。周丽也靠过来,弯下腰。老虎晃荡起身子,围着笼子转了一圈,正对着我们,把头抵在两个铁栏的缝隙里,正好伸出个鼻子。周丽说,这是让我摸的意思吗?我说,正式介绍一下,周丽,小孟,小孟,周丽,接下来一个月,你俩得好好配合,关键是你。我说完拍了拍它的鼻子。周丽也学着我,拍了拍它的鼻子。老虎轻抬下颚,咧开嘴唇,用牙蹭了蹭周丽的手。她赶紧站起身子,吓了一跳。老虎鼻子抽动,四下寻找。我看着有点不对劲,说,你手上有什么?周丽说,没什么啊。我捧过她的手闻了闻,说,猫?她说,这都能闻出来?我养了一只美短。我从腰包里掏出一小瓶消毒水,给她的双手喷了喷。我说,同属猫科动物,问题不大,猫也是小老虎嘛。我又跟小孟说,同类同类。
我打开笼门,放小孟出来。它坚实的脚掌踩进沙地,开始围着周丽转圈。我告诉周丽别怕,它得先认识你,就当你家猫。但还是看得出来她有点害怕,毕竟是一个庞然大物。小孟毛发已经不如以前柔顺,背部的毛还有烧伤的痕迹,它走到我身边时,我习惯性地捋了捋它的尾巴。那尾巴像把小扫帚一样左右甩着。我说,坐。小孟便不再走动,坐在我的对面。我从腰包里掏出一块肉糜饼干递到它嘴边。我跟周丽说,你再摸摸看。周丽缓慢伸出手掌,放在老虎头上,小孟发出了轻鼾。周丽说,我从没摸过老虎。说完又用两只手捋住小孟的胡子,向后给它刮了下脸,说,你好乖啊。我把腰包里零食盒递给她,让她喂喂。周丽照做。小孟打了个哈欠,张开利牙大嘴,口腔里还有黑色斑块。周丽说,我看见它的牙了,它能把我咬死。我大笑,说,它不咬人。我们从动物笼区出来,到厂房后面的小土坡。小孟撒花跑了一阵,我拿起哨子一吹,它便乖乖回来,坐在脚边。屡试不爽。我把哨子在胸前擦了擦,递给周丽。我说,走。小孟又开始往外跑,直到跑到土坡后面。我让周丽吹哨子。随着哨音响起,小孟重又出现,跑回来。周丽说,太像一条狗了。我说,聪明吧。她问我,有没有围栏,你不怕它跑掉不回来吗?我拍拍它的屁股,说,它能跑哪去呢。
有时候我也想,这些被我们关久了的动物,还知不知道跑,往哪儿跑。除了我们设定好的目标,一根木棍,一只彩色的气球,一个观众手里拿的苹果,洒在地上串成线的诱食剂,它们还想不想知道有另外的门,其他的路。周丽和小孟玩了一下午,后来我站在一旁看,她已经可以单独下达命令,小孟站,坐,卧,都可以达成。当然,小零食是一部分原因,我更愿意相信周丽和小孟是有缘分的,也相信周丽的胳膊放进小孟的嘴里,这样的设想是万无一失的。
连续互动了一周,每次周丽来,小孟就会提前从笼子里站起来。我也打趣道,你们老相好了。周丽问我,明明不会乱跑,为什么还需要笼子。我说,培养它笼居的意识,就永远锁住它了。给你讲个故事,以前有个小象,从小拴着象腿,绳子只有五米,挣扎过几回,都脱不开,就这么长大。成年象体重七八吨,儿时的绳子根本不结实,那根绳子早就在地上磨得残破,形同虚设,稍微一使劲就会断,但它也不会挣脱。这在心理学上叫习得性无助。周丽重复了一遍说,习得性无助。我解开铁笼,回身看周丽,发现她的腿上多了两处瘀青,我没问。她帽檐压得也比平时低。小孟出了笼子就围着周丽转,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开始让老虎学会张嘴。不能咬合,尽管懒惰,那牙齿的咬合力也是惊人的。我拿来一个抱枕,递给周丽。我让小孟趴在地上,然后双手掰开它的上下颚。它摇着头,多少有点抗拒。我吼它,然后让周丽把抱枕塞进它嘴里。上下贯穿,尖牙刺透,抱枕直接露了海绵。周丽说,这么刺激。我拍了拍小孟的头,它低吼了一声。我们重复以上动作,抱枕再次被小孟咬破了。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今天的老虎朋友有点反常。周丽蹲下和它说话。她说,张嘴,别动,不放抱枕了,我把胳膊放进去,你别咬我,我挺怕疼的。她摸了摸小孟的头,手指在毛发里抓了抓。我看到周丽的脖子里有一道勒痕,鲜红色,不太像猫抓的。我再次掰开小孟的嘴,但不放心,又给它合住。老虎起来,扒拉我身子。我给它喂了吃的。我说,我有点怀疑自己了。周丽说,咋了,关键时候打退堂鼓了。拿着被咬破掉出碎海绵的抱枕,突然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小孟牙齿锋利,万一走了神,周丽的胳膊就废了。我说,我给你五百块,项目不搞了,你走吧,也算没白忙活。周丽说,你这是不相信它,还是心疼我了。我搞不懂。正念着这事儿,周丽拍拍小孟的头,说,张开。小孟张开嘴,周丽把小臂伸进去,胳膊抵住老虎的牙齿。宽大的舌头被压在周丽胳膊底下,老虎哈着气,微微合着嘴。我被这一幕吓得愣住,回过神来大喊,你不要命了。赶忙拽住周丽的胳膊,抽回来。她的小臂瞬间多了两道血印。老虎缩着身子,蜷在原地。我说,你疯了。周丽倒很平静,说,这不是你想要的吗?我说,什么?她继续说,你们男人太善变了,还不如一只老虎,你刚才不拽我,我相信它不会咬我的。我回身拿起墙边的鞭子,抽了老虎两下。它站起来挨着,眯着眼,盯着我。我冲它吼,看什么,你就是个畜生。我又打了它两下,它低着头回了笼子。周丽说,你说你不会打它。我说,上医院。
医生给周丽做了简单的包扎,小臂的血印不深,算是虎牙磨破的,我们谎称是锋利物划的。医生又盯着周丽的脸和脖子看。我给周丽摘了帽子。医生问她,眼睛和脖子怎么回事,我也凑近看。周丽的右眼,下方文身泛红,那颗北斗星好像变大了,脖子勒痕清晰,围着一圈。医生看着我,又看着周丽,问,要不要报警?我咽下口水,顺着医生问她,要不要报警?医生又问,是不是你打的?周丽站起来拉住我的手往外走。
我们赶回马戏团已经傍晚,周丽坚持要我跟小孟道歉,它不能白挨那几鞭子。我问她疼不疼。她说小孟根本没有咬她,这事她很清楚。我问的是她身上。她没有正面回答,从我身上摸走钥匙。天色已经暗下来,所有动物都回了笼子。马戏估计出去喝酒了,马戏团也找不到人。厂房外大灯亮起来,笼子的阴影一个个打在地上,像地上长出了一个个的围栏。我模糊中看到周丽打开门,钻进了老虎笼子。我说,你干啥?周丽回身把锁重新扣上,钥匙扔给我,我没接住,掉在地上。她坐在小孟身边,开始摸它的头。老虎试着往她怀里钻,用舌头舔她包扎后的胳膊。周丽把头靠在小孟头上,又去捋它的胡子,说,你疼不疼?你就一点脾气没有吗?我大喊,它是个老虎,你快出来。周丽站起来,看着我说,它哪一点还像个老虎?她用力扒开老虎的嘴,小孟张着大嘴,上下牙齿全部露出来,舌头两侧流着口水。夜开始钻到屋里,脚下生出阴冷的风,外面的灯光晃了几下,地上的影子变暗了。周丽把另一只胳膊放进老虎的嘴里。小孟就保持着张嘴的姿势不动,口水沾在周丽的手背。她说,你咬啊。你看啊。我说,周丽,你别闹。老虎仍旧保持张嘴的姿势,喘着粗气。我去开室内的灯,光亮起来,老虎被晃了眼,向后挪了一步,避开周丽的胳膊,才合上嘴,靠在铁栏上。周丽摸摸它的头,冲我说,你应该相信你自己说的,它永远不会咬人了。
猴子在笼子里上蹿下跳,发出吱吱声。黑熊也站起来,扒住笼子。拴在倒吊木桩上的鹦鹉扑腾起翅膀,开始学人说话,它说,永远不会咬人。我被突然躁起的声音裹挟着,捡起钥匙,走向虎笼。周丽在笼子里面站直身子,面向我,开始解上衣领口的两粒扣子。我愣在原地。老虎在她身后踩着笼子,发出吱悠声。她捏住衣摆,双臂向上伸,把衬衫脱下,只留着一个黑色的胸罩。接着,她又褪去长裤,用鞋底左右踩下,只剩有一条同样黑色的三角内裤。她把两件衣服揉成一团,手臂伸出虎笼,递给我。我下意识去接,衣服上还有医院回来的消毒水味。我没说话,手里攥着她的衣服站在原地。她身体瘦削,皮肤极其白皙,锁骨清晰可见,胸骨随着呼吸若隐若现。腹部纹身是一串英文,在肚脐眼以上。她缓缓转身,背部也有,文着几个圆形图案,左侧后背同样也有淤青,脖颈一圈像被绳索套过。周丽撩起蓝色的头发,它们飞起来又轻柔地落下,像泼在她身上的一抹颜料。她再次面朝我,伸展开胳膊,抓住铁栏。老虎在她身后开始哈气,用头顶她的大腿,她蹲下抱住小孟的头,和它说着话。我走近,把衣服重新递给她,说,你快穿上。她把头从铁栏间隙里伸出来,两只耳朵卡在两侧,说,我和这只老虎一样。我没理她,准备直接开锁。她说,别开,让我说完。
ITSMINE.这是我肚子上的文身,他刻的,花了三个小时,我躺着没动。他拉着我的手,告诉我,我归他所有。每当他压在我身上,看到这句永恒地印在我身体上的句子,他会满足地说爱我,坚信我哪儿也跑不掉,我从没想过跑。针刺穿我的时候,我挺幸福,我不相信爱情,但我愿意尝试。后背看到了吗,是太阳系,漫天的银河,繁星,碎石,他要把宇宙刺在我背上。这儿,脸上是北斗七星,那是他最满意的杰作,他说,我的眼睛就是他的北极星,浪漫吗?我知道你可能觉得我是疯子。但我挺喜欢的。他掐住我的脖子,我会窒息,他也会怜悯地松手。我不要,我求他勒住我。他买来麻绳,系个套索,拴住我。他买来鞭子,也会像你那样,抽打我。我会淤青,会疼。他甚至会把我吊起来,紧紧捆绑住我,我动弹不得,我兴许生来就动弹不得。他会冲我说,你真是个贱货,用最大的力气攻击我。我会窒息,感觉空气已经无法再进入身体,我缺氧,昏迷,一切事物变得扭曲。我大口喘气,咳血,心脏像被钉子钻了孔洞,我难过起来,我不明白,这是爱情,还是虐待,我为什么不会反抗。现在,我的胳膊一点儿也不疼,我已经慢慢变成了铁笼。
我拉周丽出来,给她往身上套衣服。她推开我,又上前搂住我,吻我。我侧头躲掉,她双手按住我的脸,嘴唇贴上来,牙齿狠狠咬住我。我叫了一声,她松开,拿过自己的衣服。我摸了下嘴唇,手背上沾了血。周丽说,替小孟咬你的,你还没道歉。我吐了口血水,说,你赶紧把衣服穿上。我转身去关虎笼的门。又吐了两口血,转回来,我说,他真不是个东西,我陪你报警。抬起头,周丽已经不见了。我叫她,没人应,厂房里只有动物的骚动。鹦鹉说,咬你,咬你。
虎嘴含人的项目没能进行。马戏说早就知道我白搭,选的那女人花里胡哨的,看上去和个妓女一样,估计是骗钱的。我懒得解释。周丽没再来,电话打不通,按信息的地址去找过一回,是个老太太开的门,我递上马戏团表演的海报就走了。小孟没别的会的,在马戏团长期不表演,结果我不知道,也许会像大象一样。我拉小孟出来,让他张嘴,我把胳膊放进去。它好像知道什么似的,张倒是张,但是我一准备伸胳膊,它便死死合上嘴。仿佛因为上次误伤了周丽而表示愧疚。我蹲下来,它也跟着趴在地上。我摸着它的头,对它说,你到底是倔,那你还记得怎么咬人吗?来,你咬我一口,就随便咬我一口行不行。它挤着眼,身子一动不动。我又说,活该我总夸你,你真的越来越像一条狗了。
月底下了一场雨,三天后出的太阳,清理了活动场的积水,我和马戏摆好了道具,都是些常规的项目。小孟依旧是三个火圈,但是它训练的时候就不好好跳,我示范了好几回,爬过一个个铁圈,它勉强跟在我后面跳。真到了现场,点上火,我就跳不了了,只能靠它自己。据说这次老板带着合伙人来,马戏说情况不太好,有可能要取缔我们。我跟团了好几年,头一回听说这个事。马戏说顶多算是散伙,如果我们这里的动物表演效果不好,都跟不上了,就没必要投资了,该处理的处理,我和他可能就要分到其他团里,当然,如果不乐意跟,也无所谓的。我听着心里一颤,问他该处理处理是什么意思。马戏笑嘻嘻说,象牙卖的钱不是给你分了一部分奖金吗,就这个意思,熊掌是药材,猴脑可以吃,虎皮可以做地毯,懂了吗?我攥紧了拳头,说,懂了。
表演前的晚上我睡不着,月光照在脸上火辣辣地疼。起身,去动物厂房。我打开虎笼的门,钻进去,躺在小孟身上。全程它都没醒,还在打鼾,呼吸声急促又粗壮。明明是个壮年。我侧了个身,枕着它的肚皮,它后脚蹬了两下,踹了我的屁股。我笑了笑,拍了拍它的头。小孟睁眼瞅了我,又把头埋进胳膊,继续睡。我说,周丽那天跟你说了什么?我找不到她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这人确实不靠谱,你说她脸上那北斗七星有什么用,还是丢了,是不是。没人喜欢挨打,她浑身都是伤,浑身都是啊。对了,你好歹还算咬过她一口,她又咬了我一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咬你一口,这个环才给闭上,对不对?我上前抱住小孟的头,咬住它的耳朵。它甩了甩头,我吃了一嘴毛。重新躺好,我自言自语。说说你的家吧,你哪儿来的?是孟加拉国吧,那里远不远,是不是晚上漫天繁星的。周丽背上就是。你我有什么区别?笼子多安全。你睡得真香。你怎么不说话呢。
过了许久,小孟站起来,顶开笼门,我随它一起出去。它说,上来。我跳上它的背。它朝土坡冲去。我说,你慢点。它说,快不了,我爪子都被你们拔了。我拽着它的耳朵,它的耳朵开始变得越来越宽大,像我看过的动画片小飞象。刚来时,马戏给它打了一针麻醉,我按住它的四肢,指甲是一根根剔除的,血肉闭合不上,打了一周的凝血剂。它说,你抓紧点。我问它,上哪去?它说,你没听见吹哨吗?我说,什么?突然耳边有哨音响起来,我挺直腰背,竖起耳朵听。是周丽,她在吹哨。我一下兴奋起来,跟小孟说,走。它说,坐好了。小孟速度越来越快,满地的砂石在月光中飞溅。冲过马戏团后面的土坡,有一道亮丽的白色光道,我们犹如坐上了传送带,快速地向着天空飞去。远处明亮的繁星开始在月后挨个显现,巨大的光环在缓慢萦绕,浮石都在闪烁。银河。虎身温热,毛发如一团嫩草,纹路在脊背流动。我俯下身子,搂住小孟的脖子,听着它闷哧哧地喘气。我说,周丽,找到你了。
小孟在舔我。我睁开眼,天还没亮,它拿头拱着我的肚子。我揉揉眼,坐着它的饭盆了。我挪开屁股,它叼起一只鸡的尸体。我拍拍它,走出了笼子。
表演傍晚正式开始,座无虚席。老板果然来了,带着同行七八个人。他们坐在第一排,开场前马戏和他们聊了聊。随着场内从天而降的烟火,整个广场被点亮,四处都事先挂满了五彩的条幅,气氛热烈极了。所有动物依次出场,马戏在现场指挥,手里紧紧捏着鞭子。我配合着上前递自行车,篮球,香蕉,和几个宽大的手绢。马戏也玩出花来了,让三只猴子都学会了二人转,它们围成圈,红色手巾在猴子食指上疯狂转圈,随着马戏的指令,三只猴子同时扔起手绢,又落在旁边猴子手上。观众起着哄,热闹极了。马戏时不时用鞭子抽打地面。黑熊骑车时摔倒了。马戏一鞭子抽下去,打在它的后腿。它趔趄着要往后台跑。马戏又一鞭子抽下去,黑熊爬到篮球上,直立起来,两只脚开始在篮球上前后挪动。又一阵欢呼声。我退到后场,小孟在过道里来回踱步,显得急躁不安。我摸摸它的头,给它吃了口零食,说,一会儿轮到我们了,跳起来,跳。说着我把手掌举高,让它复习指令。
火圈全部被点燃,观众一下又起了热情,后排还有站起来的,伸着脖子。我额头上起了汗珠,不知道是不是离得太近。火光耀眼,悬在空中,还有火苗随着油滴在地上。我领着小孟站在第一个火圈前,深吸了口气,它配合着坐下来。我按了一下它的头,说,跳。我把手举过头顶,示意它跳过第一个火圈。小孟一动不动,抬头看着我。我看着观众,他们还在期待,全场没有任何额外的动静,火焰在铁圈上噼啪地燃着。我又说,跳。接着做了个跳的动作给它看。小孟伸出右爪,舔了起来。观众有了唏嘘声,老板在前排嘀咕着。我有些着急,总觉得下一秒小孟倒在地上变成一张虎皮。我拍打它的屁股,说,你今天别倔了,跳。马戏走上前来,看了看铁圈。火焰都快燃尽了。马戏用长鞭开始抽打小孟。我朝马戏说,你干什么?马戏不说话,继续抽打小孟。它趴在地上,蜷缩起来。我挪过去,挡在小孟前面,说,打够了吗,我不演了。马戏恶狠狠盯着我,说,毁在你这儿了,早他妈看你们不顺眼了。他扬起鞭子,抽在我身上,我感觉左脸到右下肚皮瞬间滚烫。我抬起手臂,挡在脸前。下一秒,马戏极为惨烈地喊了一声。观众惊叫起来。火圈灭了,烟雾缭绕在篷布下,我放下手臂,在烟雾缝隙里瞥见了小孟。它一爪子将马戏按倒在地,整个嘴死死咬住了马戏的右臂,马戏在挣扎,双腿向后蹬着,左手捶打着它的头。我反复吞咽口水。观众已经开始往外逃窜。马戏又喊叫了几声,在地上打滚。小孟退回来,站在我身旁,侧头看我。它嘴边满是血,我下意识去摸它的头,它便靠过来蹭。鞭子撇在一旁,那只手还在紧紧握着,和断臂一起丢置在沙地上。
老板打了急救电话,马戏和断臂一起送进了医院,当场的急救人员就说了,动物撕咬的伤口太不规则,接上的可能性不大。警察也来了,我留下配合了一系列调查。小孟也锁进了笼子里。监控拆下来都作为了证据。他们也不好定性,马戏团动物过失伤人,赔偿就老板自己定了,你们内部处理,还不算危害社会。人没死,就算好的了。临走时,他们还问,怎么没咬你?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又想起周丽说过的一句话,于是我说,我相信它永远不会咬人。警察那边就笑了,说,别闹了,胳膊都没了,起码五级伤残。老板准备了三针麻醉,交代给我,说,这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我不太明白。他又说,马戏跟了我十年了,这事你不用担心,就给你一个任务,把针推进去,解决这个畜生。我应下来。等老板走后,我把三针都摔在了地上。
夜里,我把虎笼门打开,领它到后院水池旁。我让他坐下。它就坐下。水龙头上接了一根皮管子,我拧开,对着它冲洗。小孟不太喜欢,扭着屁股要跑,我死拽住它的胳膊,抹了一把水擦着它的脸。嘴唇上还有血。我放下水管,两个手给它抹净。它转着圈,一只脚踩住了软管。水流变急,翘起来,冲到我身上。调皮了啊,我说完把上衣脱掉。肚子上被马戏抽打的红印还在。我用手摸了摸,心想,不知道周丽身上的好了吗?冲开小孟身上的毛,我去摸它的屁股,问它,你身上的疼不疼?我又说,你真他娘的傻啊。不知道是水还是泪,脸上湿乎乎的。我坐在地上看它。小孟像狗一样抖了抖身子,缓缓走过来,舔我脸上的水。我闭上眼,感受着它舌头的倒刺。疼痛,刺痒,温热,分不清是身体的感受还是心里的。我说,一会儿你就跑,我带你到坡上,你好好看看,什么也拦不住你,没有笼子,没有铁栏,没有。小孟还在舔我。我睁开眼,抱住它的头。我说,你洗干净了,你从来不会咬人,也没咬过人,你不在这儿住,你家是孟加拉国,你是孟加拉虎,听见没?我站起来,光着膀子领着他往前走。它跟着我,毛湿漉漉的。我俯下身子给它用上衣擦了两把,它太大了,无济于事。我继续走。到了坡顶,我往下指,一边是城市,还亮着光,一边是黑的,大片的玉米地。这回你得听我的,别倔,我把手指再次插进它头顶一缕缕湿发里说,跑!跑起来!小孟像是听懂了一样,一下蹿出去,地面上带动的尘土渐渐飘在空中。在明暗交界的地方,小孟停住了,回头看我。我去摸腰间的哨子,又松开了手。我大喊,小孟,跑!它扭回头,一下跳进黑夜里,不见了。我站在原地,又闻到了马戏团腐败的臭味,风徐徐吹来,我身上的水渍干了,觉得冷,抱起胳膊。我等了一会儿,什么动静也没有,随后有夜鸟鸣叫,月亮被一团阴云遮住,天上开始落下雨来。我往回走,走得尽量慢,我希望小孟可以赶在我之前抵达。直到雨密集地落在脸上,我才真的放开,任眼泪流下来。一只老虎,它能往哪里跑啊。
上午九时,一只孟加拉虎因闯入村子偷鸡,村民报警,民警赶到,经判断,并确认该虎曾伤人,因害怕再次出现类似事件,危害公共安全,果断予以击毙。
马戏出院后不再干这行,老板赔了一笔钱,他开了个小卖部,在县城落下了脚,因为跟动物打过交道,还找了个对象,是宠物店的老板娘。马戏团取缔了,老板收回了所有的动物,留了个鹦鹉给我,还安慰我说,这头老虎太会装了,不怪你,当时就该直接处理的。我点点头。西郊水厂拆干净了,挖掘机第一天上场就挖出了一卡车的粪便。鹦鹉挺有意思,有时候能跟它对话,也算解解闷。我带着鹦鹉到处走,也没什么目的,我说,东还是西,它说,东。我们就往东去。有时候在人多的地方摆个摊,逗鹦鹉学舌,能赚几个零花钱。没什么别的本事,有些事久了就不记得了。我问鹦鹉,你记忆力好不好。它说,好不好。我说,你还记不记得有个蓝头发的姑娘。它说,蓝的,蓝的。我说,看来你是个傻子。它说,傻子,你,傻子。我就能笑上一阵儿。
冬天,老板又联系上了我。他找我回来,说马戏团他又敛好人了,就差个会驯的,你不是有证。我问他驯什么。他说其他动物都办妥了,但这个一般人还真般不了,老虎。我听了心里一颤。我问他,在哪,老虎不是伤人了吗,还能办?老板笑着说,半年前了,谁记得住,这次是个小白虎,几个月大,你就陪着它玩玩,我给你发钱,机会难得,你考虑考虑。我连夜坐火车回来,肩上扛着鹦鹉进了新的马戏团。小老虎像只小猫,走路都不稳,关在笼子里,它甚至可以从铁栏之间钻出来。虎太小了,笼子没用,跟着我就行,老板应了。我把它捧在手心里,头蹭着它的头。它发出奶音。我跟它龇牙哈气,它也装模作样龇牙。我说,这就对了,倔起来。鹦鹉在我肩膀立着,我给它看小老虎。我说,嗨,认识认识。鹦鹉晃着头,在我肩膀上左右挪了两步,说,小孟,小孟。我心头一紧,决定不再重蹈覆辙了。
每个休息日我都会背着包去文身店,县城的文身店很多,未成年的孩子也有,生意都很好。我进门就找老板,先打量他一番,再问他会不会纹北斗七星。鹦鹉也跟着我说,北斗七星,北斗七星。有的会和我探讨一番,有的就直接撵我走了。在城南,有家文身店,老板娘是个女的,一进门就应了我,我转身就往外出。她又喊住我,说,你这个鹦鹉挺有意思啊。我附和几句,马戏团的鹦鹉,没人要了,我带身上。再抬头看,女人一头黑发垂在肩膀上,穿着高领毛衣,长筒靴,右脸有七星北斗的文身。我说,周丽。她默不作声。楼上走下来一个男人,看着有二百多斤,胖乎乎的,不高,头发很长,手里拿着一把针枪。他说,老婆,什么好玩的?我接上话,说,鹦鹉学舌,卖艺的。周丽说,它都会什么?我跟鹦鹉说,叫美女。鹦鹉说,美女,美女。周丽笑了。鹦鹉又说,周丽,周丽。男人凑近了看鹦鹉,说,神了啊,怎么还知道你叫啥。我说,它比人都能。男人说,真他妈神奇啊,行,我里边儿还忙着,一会儿再唠,别走啊。男人上了楼。周丽点上了支烟,抱起胳膊。她说,怎么找来的?鹦鹉说,周丽,周丽。我跟鹦鹉说,消停点。周丽欠了欠身,说,没少念叨我啊。我说,一家家店转,有事找你。
我把背包转到身前,松开抽绳,给她看里面。她吐出口烟,说,老虎?我说,嗯,小老虎,还叫小孟。周丽眯眼又看了看,老虎还在睡,她伸手摸了摸它的头。她说,你贩卖老虎啊。我说,想啥呢。马戏团的小老虎,我驯,长大了住笼子,钻火圈,还得拔掉指甲,这次估计还要拔牙,因为上次…周丽说,我知道,我看新闻了,你想说什么?我说,我想带你走。鹦鹉在肩头左右又挪了几步,说,周丽,周丽。她弯腰在茶几上灭掉烟头,深吸了口气,说,去哪里?我说,去哪里都行,别在笼子里。你看看,她笑着说,然后转了个圈,指了指门头的柜子,茶几,沙发,落地灯,两盆绿萝。我挺好的,她补充说。我拽住她的胳膊,撸起她的袖子,露出两条白皙的胳膊。周丽说,你想找到什么?证明你是对的吗?我说,我不想你骗自己。她说,你走吧,他一会儿就要下来了。
我系好背包的抽绳,小老虎在里面动了动,我把它提起来,重新背在身上。出门前,我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放在了茶几上。我说,咖啡钱,谁也不欠谁了。周丽说,行。鹦鹉说,走,走。我捏着鹦鹉的腿,把它换了肩膀。它说,疼,疼。出了门,我左右看了看,却不知道该往哪去了。我问鹦鹉,东,西,南,北。鹦鹉不说话。我从口袋里掏出小把米,递给它吃,它啄着。我心想,往南吧,把小孟送回去。过了马路,我仿佛听到一声哨响。背后周丽喊,李建德,别再回来。我摆了摆手,头也没回,把背包往肩膀上拽着。鹦鹉吃完了米,开始啄我的头,它不停地说,周丽,周丽,周丽,周丽。直到一辆货车从身边驶过,带出的风,猛烈地把一切彻底覆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