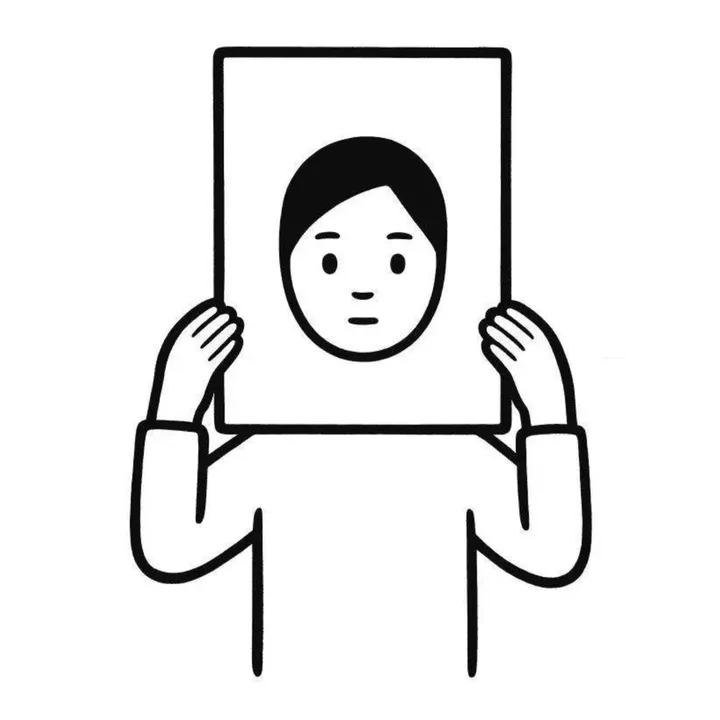结婚、离婚,生产、养育,相遇、别离,普通人彼此碰撞,火花点燃了日子。
我坐在小转椅上,手伸进羽绒服内里口袋,想抽根烟。场所内外禁烟,标识就在头顶的侧墙贴着,又把烟盒放回去,无精打采地看着游乐场。场子里的海洋球是蓝白的,一大片挤着一大片,有黄色的橡皮艇勉强漂浮在表面,孩子们抢着爬上小艇,释放表演欲,风来了,雨来了,手动摇晃。乐乐站在海里,海洋球没过双膝,距离小艇有一米,他往前一步,想同样爬上小艇,但跌落原地,脸埋进蓝白色球里,许久没有起身。孩子们跳下来,绕个圈,再次冲向小艇,更多的球溅到屁股上,乐乐消失了。
海洋球左侧是双滑道滑梯,十几阶,孩子们争先恐后,乐此不疲。我看着两群孩子,总觉得他们都一样,高高矮矮,男男女女。这也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我对孩子的辨识度有所下降,也许是刻意的,面部五官和棱角像面糊,立不住,越这样,越感觉安全。我从椅子上下来,迈进海洋球,往乐乐沉没的方向去,弯腰,胡乱伸手,抓住裤带。乐乐闭着眼睛,像只拎起的乌龟,四肢扑腾,说,你干嘛拉我,我在潜水。我轻轻放下,他又钻回球里,似乎是感受到了某种乐趣。你游走吧,就从这一堆海球里,最好海底通着地球的另一端,你游上岸后还能被其他肤色的伙计救起,我心想,但眼睛还是始终盯着乐乐蹬腿时弹起的塑料球。
时间是下午四点,商场里的暖气不太足,羽绒服穿在身上还是有些打颤。再过两个小时,赵英会来接孩子,她没有给我们一起吃饭的时间,晚上她有个应酬,得带乐乐去。我没问为什么要带孩子去应酬,兴许对方也有孩子,两个孩子玩一块,两个大人玩一块,想到这,索性退缩了。离婚已经一个月了,每周六我都可以陪儿子玩一下午,有时候还可以坐在乐乐对面看他一口一口吃着汉堡,他的脸不像五岁,是个小胖子,脸颊总是鼓鼓的,嘴里像塞着个气球,我不记得儿子以前是不是这样,感觉是离婚以后才变的,离婚以后什么都变了。每次看他吃,我都会问好吃吗。乐乐总是没空回答,继续吃汉堡,小平头的发根汗涔涔的,在麦当劳的灯光下不停地闪烁。怎么看怎么不像,这个想法大概是在和儿子如此面对面的时候产生的,我本身瘦削,胳膊手腕都细,坐着能感觉肋骨顶着胸膛,单眼皮,鼻梁和颧骨很高,总之跟面前这个嘴里塞满汉堡的儿子不太像。我还会带着他再去买个玩具,小汽车或者奥特曼,然后坐在商场门外的长椅上等赵英来接。我从来没有提起这个话题,关于儿子的长相,也许是我在瞎想,徒增烦恼,长得不像的多了去了,也不差一个两个。我开慰自己,有什么东西也逐渐在开慰中离去,乐乐变形了,还有什么正在扭曲,我抓不住的,也许不止这些。
乐乐从海洋球里钻出头来,冲着我喊,说什么东西在抓他的脚脖子。爸爸两个字他叫得极为大声,我多听了一会,才伸手把他拉上来。他说这里面有东西,我问他有什么东西,他说怪兽,我让他少在妈妈家里看些奇奇怪怪的动画片,俯下身子在塑料球里摸了几下,捞出一只蓝色的小鞋子。游乐场没有穿鞋的,鞋子不知道哪里来的,我又扔了回去,它像只鱼,钻进了深处。
我说,出去吧,再玩一会,你妈该来接你了。乐乐极不情愿,扭着小屁股,我不知道他在赵英那都吃了些什么,好像只长肉了,本想劝点什么,可他才五岁,怎么知道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生活该怎么做,不是谁一教就会的。这样也好,说明赵英待她挺好,不受委屈。我给他穿上小羽绒服,拉链有些紧,乐乐抻了抻身子,我们从游乐场出来,往玩具店走。都在同一层,玩具店常去,有公主娃娃和变形金刚,乐乐在里面跑了一圈,地板都在震。我是有多讨厌这个儿子,有些奇怪,也表达不出来。女店员没见过,像是新来的,站在门口的柜台里,眼睛盯着乐乐,又看看监控器。我说,他不会偷东西的,你不用担心,他才五岁。女店员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帽檐上是两颗钻石,经典的奥迪双钻,我的伙伴。她抬头看我,说,三岁就会偷东西了,这个跟年龄没关系。我说,是,万物皆可偷,还有偷人的。女店员斜我一眼,我往店里面走。乐乐蹲在一辆消防车前面,摸着玩具盒子的塑料薄膜,手指粗胖,抚在上面发出沙沙声。
我不确定赵英是不是偷人了,当然我也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公平。两个月前,我把赵英这件事告诉李翠红的时候,她帮我分析过,我们面对面在马扎上坐着,等了半天烤串才上来,凉飕飕的,我跟老板吵起来。李翠红一直拽着我,起先是胳膊,然后是小臂,再是手腕,最后紧紧拉着我的手。我收敛愤怒,坐回去,她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什么也没说,手也没松。两只手腕穿梭在毛豆花生、羊肉串、啤酒、烟盒、打火机的小桌板上,像丛林里交汇的猎豹,彼此是猎物也是猎人,关系在指尖升温,我的愤怒被稀释了,随之取代的是一种龌龊的想法。李翠红说,关于赵英,你也别太当回事,再观察观察,大家都是同学一场,这种事丢人。我手心里冒了汗,她攥紧了我,我把头侧向室外,雨从窗户上开始下起,玻璃被蝌蚪般的雨线爬满,我转回头对着李翠红说,我们换个地方。
房屋在震颤,隔壁动静比我们大,钟点房只有两个小时,声音起伏不断,被子卷成一团。李翠红的眼镜找不到了,我们花了好大一阵忙这个事,她没有再对赵英发表其他的看法,而我也更加笃定这个事情的真实性。那天夜里十一点,我妈把乐乐哄睡着后,我听到楼下的汽车声,趴在窗台上看,赵英从黑色越野车上下来,关上车门前又把头凑回去,我心里咯噔了一声,好像掉到了地上。等她开门回来,我坐在沙发上抽烟,她把白色的尼龙大衣脱下来挂在衣架上,看了我几眼,就往厕所走,我拉住她,想质问她,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说出口。那时已经开始谈离婚了,原因说不清,不到万不得已,谁想走这一步。
帮李翠红戴上眼镜时,我开始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更期望眼前这个女人是我不认识的,她看着我发呆,摇了摇我肩膀,说,你别有心理负担,算是对她的反击,反正我高中那会也不喜欢她。我点点头,算是达成了一致,一种反击,对生活的反击吗,我问自己。李翠红已经开始穿衣服,隔壁仍旧发出无休止的呻吟声,听上去比我们年轻很多,我重新扑上去,把李翠红压在身下。她笑着说,就两个小时,我们找眼镜花了二十分钟,我还得上夜班。
那一阵李翠红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她有过一次婚姻,没有孩子,生活比我自在,夜班就给人打针,换换吊瓶,深夜给我发信息都改语音了,好像盼着我早点离婚,也一个劲夸乐乐,想认干妈。我摸不着头脑,但也深陷进去,事情哆哆嗦嗦,赵英不问,我也不问,越野车来得更加频繁,茶几上的烟灰缸里都是烟头。最后两周赵英把乐乐带走了,我妈搂着枕头睡觉,睡不着,坐进客厅沙发上哭。声音呜呜咽咽,是哭给我看的,我把烟点起,就干看着烧成烟把,满屋子都是烟,云里雾里,看什么都不真切,自己也像是在哭,发信息给李翠红,总说忙,靠不住,我也明白,不长久。
乐乐把手从消防车上挪开,说想要手枪,店里没有手枪,商场就这一个玩具店,要那玩意干啥。乐乐说叔叔家里有,他摸过,妈带他去的。我问他,怎么去的,坐的车大不大。乐乐说,挺大。我又问,什么颜色的。乐乐说,忘了,我就想要手枪。我随便给他买了个会爬的兵人,也端着个枪,又花五块钱买了两节电池,女店员帮忙换上,兵人在地上边爬边突突,乐乐不喜欢,我捡起来,关上电源,带他往商场外走。又和乐乐聊了一会,才知道他说的手枪是真枪,凉冰冰的,沉甸甸,就放在沙发上,梭子口空着,剩一空壳。乐乐还把手往里伸,夹住过好几回。我问他,你玩枪的时候,妈妈在哪?乐乐说,跟叔叔在屋里。我没往下问,枪是真枪,是个警察,开的车挺大。
赵英是走着过来的,穿着长款大衣,毛绒领,高跟皮靴,挺直腰,能有我高,戴一墨镜,大冬天看着别扭。乐乐看见就往处跑,兵人也没拿,我走上去递给她,说,给儿子买的玩具,老规矩。赵英说,你该刮刮胡子了,邋里邋遢的。我说,你这是还想管我呢。她说,我没那个闲工夫。我从羽绒服口袋里掏烟,点火,说,是个警察。赵英把墨镜摘下来,眼睛像是刚动过刀子,肿了一圈,倒是漂亮了,说,别老从儿子那里套话,有事你直接问我。我吐口烟到天上,想问问关于孩子的事,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乐乐就站我旁边,脸往赵英大衣上蹭。于是我说,李翠红你还记得吧。赵英说,你和她搞上了?我说,差不多。赵英沉默,没再说话,爱搭不理的,准备带乐乐走。我还是憋着一口气,感觉不顺畅,看着乐乐跟在身后的样子像个小企鹅,哪点也不像我。
回到家,我妈在厨房做饭,弄一屋子油烟,抽油烟机嗡嗡直响,管子从沿口掉下来,耷拉着。我说,妈,管子掉了。我妈不吱声,继续炒着锅里的一捧菜花,肉都糊了,葱花发黑。我走近再说,妈,管子掉了,管子。指了指抽油烟机。我妈把勺子往锅里一扔,火也没关,转身就往卧室走。房子就一套间,一大一小,平时乐乐跟妈睡。我把火关上,打开厨房的窗户,油烟里外都浸满了,抽油烟机也关上,顿时安静不少。我跟着进屋,妈坐床沿上,什么话也不说。我问,想乐乐?下周六我把他带家里来,不在商场玩了。妈不说话,胳膊肘撑着膝盖,手捂着头,知道也管不了。我接着说,乐乐又胖了,越来越不像我,不知道是不是个野孩子。妈站起来盯着我,我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但是我接着往下说,妈你知道吧,每次赵英回来晚的时候,都有辆越野车,停在楼头,这事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俩感情淡也就淡了,婚姻里哪有输赢,我现在怀疑孩子不是那么回事。我妈终于说话了,你这人真不要脸。我听了浑身发颤,回自己屋里,躺在床上,胡乱想着,也不饿,花菜还在锅里晾着,母亲屋里没有动静,像是又在哭。说不出的烦躁,床头拧开瓶盖,吃了两片药,最近睡不安宁,心里还犯嘀咕,怀疑得了抑郁症,把被子蒙住头,打了两圈身子,钻出来给李翠红发了信息。我需要你给我打两针,很急。李翠红在上夜班,夜班永远比白班多,搞不懂为什么,也没问。她回,夜班,人不多,你来吧。
郊区医院豆点大,开车四十分钟,找到藏在树林后的低矮建筑,医院共两排,一排诊所,一排住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得的也都是老病。我把车停在门口,叼着烟走进医院,保安在看手机,问也不问,我按李翠红说的,往后排建筑走,她在一楼领我,穿着一身护士服,带着小白帽,没披大衣。我小跑过去,把烟掐掉,上去搂住她,她有点抗拒,推开玻璃门,带我往里走。二楼保健科,护士站一共两个人,一个在更衣室眯睡了,一会才来换她。我陪李翠红坐在圆形小凳上,她整理着手里的几张图表,像是夜晚哪个时段的几瓶点滴。我把羽绒服脱下来,放在台子一边问,有几个住院的。她说,今晚一共十一个,一会儿有两个需要换吊瓶的,你来找我干啥,有这么急吗?我把凳子往她身边挪,靠紧她说,你说,乐乐会不会不是我的孩子。她扑哧笑出声,说,你觉得自己是个冤大头?我说,是啊,我总觉得乐乐越来越胖,脸往宽里长,多少变得不像。赵英跟了个警察,我没见过,他那车我见过,又大又宽,和乐乐一样。李翠红说,你什么意思,她俩早就认识?我说,我就是猜测,这个我也说不准。李翠红把图表收进抽屉里说,你要早这么上心,你俩也离不了。我说,那不也没你了。李翠红说,什么没我,我这不好好的,就在这当护士,什么叫没我。我又上去搂她,她没有反抗,我把手从她扣子缝里伸进去,她转回来看我,说,你干什么呢。我说,咱俩凑一块,也挺好的,我今天见赵英,跟她说了。李翠红问,你说什么了?我说,我说我和你好了,还准备结婚。李翠红把我的手从衣服里拉出来说,婚姻就是个坟墓,谁往里跳谁傻逼。我听着不舒服,李翠红又说,孩子也是,我这一辈子不会生孩子,子宫我都切了,你别想太多,我是肿瘤,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知道我为啥离婚吗,就是嫌我不能生,你也别在我这吊死,乐乐是不是你亲生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是给你生不了。不知道是不是环境不对,她说话带着气,夜深了,医院走廊里有机器的滴滴声,从病房里传出来,听上去瘆人。李翠红接着说,等一会,我去换个吊瓶,这里不能抽烟,你别偷着抽。我点点头,看她到换液室忙活,拿一托盘和一瓶药水出来,拎着往走廊尽头走。李翠红很瘦,像是营养不良,还不如我,上次折腾的时候总是担心折断她的什么骨头,拿被子和枕头垫着,很小心。怎么说呢,兴致没了,不知道是刚才她说的话,还是有节奏的滴滴声,这里的暖气比商场的足,我的额头开始冒汗,坐不住,李翠红去了很久,拿出手机给她发信息,声音从抽屉里响起来。她把手机落在这里,我打开抽屉,锁屏的手机上都是信息,我是其中之一而已,大脑空白,突变尘埃,无处可落。
我捡起羽绒服,穿在身上,往楼下走。保安还在看手机,像是睡着了。我敲敲窗户,他愣着瞪起眼睛,隔着玻璃看我,大概觉得我是个神经病,我贴着玻璃哈气,窗户一片模糊。保安是个老头,把帽子戴好,准备出来问候我。我继续往外走,躲进车里,打开玻璃,手伸出去抽烟,烟火忽明忽暗,冷气直往车里钻。引擎刚启动,李翠红裹着大衣跑了过来,拉开车门坐在副驾驶,小白帽还戴在头上。她推了推眼镜说,怎么不说一声就跑。我给她递一根烟,她接过来,吸一口,把烟吐在挡风玻璃上。我说,刚才不小心看了你的手机,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李翠红说,没想到你还是个这种人,没少查赵英手机啊,那还没有什么发现吗?我说,不小心,我没那个习惯。李翠红又吸一口烟说,你车上真冷,能开个暖气吗?我把车窗摇上去,打开空调,李翠红又把车窗摇下来,留了个缝,可以跑烟。她说,什么不好的感觉?我说,有种过日子的感觉。她说,我可不会过日子,我日子过得一塌糊涂。说完把烟头从车窗缝里弹出去,摇上了玻璃。她说,赵英抢了我男朋友你知道吧?高中那会,我谈了个体育生,练长跑,跑得特快,每天下午太阳最毒的时候出现在操场上,背上的皮肤晒得黢黑,我还帮他挑过皮,一层一层的,爱得不行。赵英和他在厕所搞的,就咱那个操场最角的厕所里,她俩还真是不挑,至于具体做了什么不清楚,反正亲是亲了,我朋友亲自撞见的。你想想,乌泱泱的粪水在池子底下,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咳嗽了几声,这事没听她说过,我说,我在哪?李翠红说,谁知道你那会在哪,时光都让狗吃了,你能和她结婚,其实是她的福气了。你刚才说乐乐的事,我又仔细想了想,我知道你想要什么答案。孩子就是负担,你始终不能像我一样轻松,如果你有子宫,你也应该切掉的,乐乐胖成那样,八成跟你不一回事,你养了几年,五年了。我说,你话突然多了。李翠红把身子侧过来,朝向我说,是,你这一跑,我才发现,咱俩可能就不是一类人,你和赵英也不是,她能跟你生个孩子就很不错了,也不对,孩子还可能不是你的。我说,你别说了。李翠红好像激动起来,说,我就是觉得这样公平了,互不相欠,你们离了,我就没什么兴趣了,我不是故意报复谁,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女人也差不多,我不针对你,你是个好人,我说这话你能听明白吗?我没回答,车座往后撤,把她从副驾驶直接抱过来,她靠在方向盘上,脱掉白色的护士服,身子一用劲,喇叭滴滴响起来。她说,你扶好方向盘。我说,然后呢。她说,赶紧进来。
暖风一直在吹,车子打着火,不停地抖动,玻璃都是白气,里外看不见。保安大概是觉得好奇,三番五次往这走,试图贴着窗户往里看。李翠红说,你来是这个意思吧。我瘫软在座椅上,说,差不多。她说,我认识一个老师,比你这个药厂的强,你浑身都一个药味。我说,处方药我能拿。她说,我也能拿。说的不是这个事,我认识了一个老师,比我大五岁,教导主任,他对我挺好的,没有生育能力,精子活力太差,又总想试试,离了两次,想栽在我这。这事你怎么看?她说完,把衣服拾掇到身上,爬回副驾驶,重新点上一颗烟,把玻璃摇下一条缝。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不会过日子,你有句实话吗?她说,他父母双亡,有车有房,我就提了一个条件,别管我太多,我也不会往外跑,自由惯了,天蝎座,有时候也毒,怕他受不了。我说,这就替他着想了。李翠红撇着嘴笑。我说,你们是不是做过了。她说,这个倒不如你。我说,那你跟我过吧。她说,那就是我栽给你了,你想得美。
回家已经半夜了,我悄声开门,油烟散尽,厨房的风呼呼往里吹,屋里冷得不行。我喊着妈,没人应。推开卧室的门,床上被子叠得整齐,妈不在。锅里的花菜也处理了,底洗净。我关上厨房的窗户,坐在沙发上抽烟,给妈打电话,关机。时间十二点四十二分。等到一点,我觉得不太对劲,平时没有这种事。我给李翠红打了个电话,她把班翘了,打车过来,进门时羽绒服上还有一层薄雪。我翻着妈屋里的衣柜,想着她出门穿的衣服,厚大衣没几件,都数得过来,应该是穿着藏青的棉衣。衣柜里还有乐乐的衣服,码得整整齐齐,放在一侧。我又给赵英打了个电话,问问我妈有没有去她那里,许久才接,又不耐烦地挂了电话。李翠红跟着我,一会儿坐,一会儿站,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她也不说话,就是陪着。我说,我们出去找找。
马路上已经多了一层积雪,有手指厚,踩上去咯吱响。小区的树枝低垂,昏黄的灯光裹着纷飞的雪片,落在肩上。李翠红拉着我的胳膊,我们出了小区,往青年路走,南北各一半,无车,路牙上也没有行人,抬头往天上看,雪像细密的飞蛾,往脸上扑。我蹲下来,突然就觉得累了,身子像散架一般,李翠红用力托着我。我说,我觉得我妈被雪埋了。
24小时后,才可以去派出所报案,算是失踪,警察问了我很多问题,我能答上来的都答了。年龄七十,穿藏青色棉衣,白色运动鞋,可以沟通,没有语言障碍,儿媳离婚带孩子走了,心情不好,做饭菜都糊锅了,没有精神病史。警官做了登记,我看到他腰间别着手枪,黑色漆,皮革枪套,我问,你那枪是真的吗?他愣着看我,整理了一下帽檐,我抬头看他,发现他脸庞硬阔,眼距宽,颧骨高。我说,你是开着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吗?警官不知所以,我也糊涂,登记完就出了派出所,头脑昏昏的。李翠红来了电话,问我找到妈没有,我说没有,都登记好了,准备再贴寻人启事。外面雪大,一天一夜,有十厘米厚,陷了脚面,天空像裹了白糖,磨砂感极强,就是没有甜味,到处都冷清清的。
药厂不怎么去了,效益不好,又拿了几瓶治神经的药,放在床头,没有时间概念,躺在床上,反复睡不着,做了个梦,梦到我妈在下河桥上站着,雪厚到膝盖,她抽出双腿,爬到石柱上。桥下河水早就结了冰,雪落上就化,固不住,几只鸭子被冻在冰面上,一半在水里,一半在冰上。我妈就站在石柱上看鸭子,没穿鞋,脚冻得肿起来,眼看就站不住了,准往河里掉。我就在身后,慢慢靠近,我妈猛一回头,吓我一跳,脸上都是雪,开口说话才能看清嘴,眼睛睁开,雪哗啦啦往下掉,说,你真不要脸。我被吓醒,推门就往外跑,羽绒服也没穿,就一卫衣,拿个围巾上车,往下河桥开。雪太厚了,车轮不停打滑,天上煞白,按时间应该是晚上,判断不出来,又把车停在楼头,跑着去,到了下河桥,一身汗,不觉得冷。桥上一个人没有,桥下早就没水了,雪积得很厚,才反应过来梦就是梦,跟生活没什么联系。总期待能看到我妈,走一天一夜了,要是不停,能到北京,再往北走,兴许回东北老家了,就是路上太冷,拿什么取暖呢。把我妈想象成一辆火车,轰隆隆一直开,过了漠河就是俄罗斯了,再想就是北极了,只要不停下来就行,我就算不找也行,寻人启事也不贴了,别停,停下来就泄气了。雪在肩膀上落了一层,卫衣浸透了,扯紧围巾,视线模糊,才发现下大了,身子发抖,打了几个喷嚏,想再跑回去,兴许能暖和些,但是没劲儿,索性站在原地,让雪落满全身。不知道该怪谁,这事就真至于吗?
太阳几天后才出来,雪化又用了几天,铁轨附近有一冻僵的尸体,派出所通知去认尸,我自己去的,没叫李翠红。尸体肿得很大,脸变了形,认不出来,藏青色棉衣在身上裹着,太阳照着亮闪闪的,有一些没化的冰晶。哭不出来,就是有点失望,总觉得不应该这样。草草签了字,殡仪馆的车在旁边等着,单趟200块,我和妈一起上了车。车上就司机一人,胖乎乎,戴个黑色墨镜,小声说,老年人就是容易走丢。像是在安慰我,我没吱声。他按开音乐,低沉、舒缓、宁静,车开出小路,他继续说,前几天还大雪,这个真没办法,节哀。我谢过他。一路什么话也没说。流程走完,把我妈收拾进铁盒里,带回家,接下来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几天不见怎么就对不上话了呢,脑子里一直回响着那句,你真不要脸。我愣在客厅,声音一直停不下来,好像是铁盒在说话,我趴在地板上,把铁盒放进沙发底下,回卧室,关上门,吃了两片药,还是静不下来。我给赵英去了电话,说我妈冻死在铁轨上了,应该是去你那迷了路,她想看看乐乐。赵英沉默了一会,说,乐乐幼儿园吃不饱,都是在家喂的,现在不能让老人喂孩子,一口口往嘴里送,自己都不知道吃。我说,是,老人都怕吃不饱,不喂心里也不舒服。电话里杂音比较大,房产中心好像在搞活动,赵英说,你妈想看乐乐,就别抽饭点了,习惯不好。我说,是,习惯不好。她挂了电话,我再打过去,就不接了,大概在忙着卖楼。
还是让雪埋了,李翠红说这话的时候,我才有点想哭,雪是个好东西,白乎乎的,往上一盖,啥也看不着,但总有天晴的时候,太阳一晒,人都不是人了。她选了个正规地方,西餐厅,桌子上还有朵花挡着,手也伸不过去,就看着她。她翻菜单的时候动作收敛,穿一白色坎肩,眼镜好像换了。我说,这地方不适合我。她没理我,点了两份牛排,还有一瓶红酒,几个红薯球。她说,老师找她了,给她买了辆车,就停在楼下,红色的,和个虫似的。我说,甲壳虫。她说,就是那,我收了,你明白吧?我说,我明白啥?服务员把红酒领过来,还有醒酒器,我说,能换个啤的吗?服务员说,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啤酒。我摆摆手。李翠红说,我以为自由挺好,可能那是我没见过。我说,你没见过什么?她说,就是以前没见过那些,我前夫是个窝囊废,干个体户,一会儿开水果店,一会儿卖电子产品,就是那些二手手机充电宝,放裤兜里都怕爆炸的那种,还嫌弃我。你说这是不是PUA。我说,有点高级了。李翠红说,也不是高级不高级,这车我开了三天了,起步也快,还带烟灰缸,后排空间也不小,宝宝座椅也放得下。我说,什么宝宝座椅?她说,我们准备领养个。我说,我听明白了。牛排上来,我没吃,没有胃口。李翠红餐巾别在领口,拿刀叉姿势优雅,把牛排分切成小块,用刀尖扎起来,往嘴里送。我说,别用刀扎着吃,太粗。她愣着看我,眼镜又掉下来,手背往上推推,换成叉子,显得有些局促,说,我还不太适应。又聊了些有的没的,距离感觉远了,桌子变得很长,话听不清楚,我就说了说我妈,觉得她可怜,也不知道是白天上的冻,还是晚上。还有乐乐,很像我那天在派出所见到的警察。李翠红把嘴里的牛肉嚼干净后说,你也该考虑一下了。我说,考虑什么。她说,人总要向前看,我有点理解赵英。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她说,时间长了,你挺没劲的。
我把牛排吃了个精光,胃里难受,想吐,这东西半生不熟,盐粒儿撒在面上,黏嗓子,喝了一杯红酒冲冲,没什么用。李翠红的车大红色,阳光下光彩夺目,耀人眼。我和她握了手,她往回抽,上了车。我弯腰透过车后玻璃往里看,车身太矮,啥也看不见,想必她也不会回头。掏出手机,把聊天记录删了,好友也删了。删完就后悔,再想加回来,微信号不记得了。
我妈的葬礼还是张罗了一下,来的人不多,赵英是其中之一,带着乐乐。她穿一身黑,表示抱歉,电话里没听太清。乐乐不懂事,在花圈那转来转去,老问我奶奶在哪,我说在后头,他翻过花圈往后找,一遍又一遍。我挨个谢过厂里的领导,也能听出药厂的情况,不再多问。赵英站在我身边,没什么话,但也算好,好歹有个人陪。我说,乐乐胖了不少。赵英没说话。我接着说,枪少给他摸,万一哪天梭子没卸,伤了自己。她说,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说,和那警察挺长时间了吧。她说,你管得有点多了。我说,没什么,就问问,我说乐乐怎么不像我。赵英转过身来站定,一巴掌打到我脸上,我没站稳,一个趔趄,扶着墙起来,眼里模糊,看着乐乐被赵英拉走了。没有答案,谁也给不了答案,这事就真的至于吗?
周六上午,我网购的手枪到了,快递封得严实,透明胶糊了三四层,硬是手撕,手指都红了,打开,黑色的手枪躺在里头,叫不出名字,和警察别腰里的一样,摸上去凉,凑近了还有金属味。弹匣自带子弹,保险扣紧得要命,我没仔细检查,拿出来放进兜里,准备给乐乐带去。下午在商场门口等了半天,时间将近三点,乐乐没来。我给赵英打电话,她不接。过会儿回复我信息,准备给乐乐改名。我有点急,连着打了三回,她接了,我问她啥意思。她说,你真不要脸。这话我听着熟悉,一阵哆嗦。我说,我给乐乐买了把枪,和乐乐说的一样,你过来给他拿着。她挂了电话。
不知道站了多久,天暗下来,商场门口的路灯满了飞蛾,一片一片的,仔细看看是雪,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人行道一层白,马路上有车,轧出一道道水辙。人们都赶着回家,裹着厚实的衣服,从商场往外出。我从怀里掏出手枪,没捂热乎,金属冰冰凉凉,黑漆漆的枪口,里面和有子弹似的,我对着瞧,扳机扣不动,保险还上着呢。人们绕着我走,不知道情况,我被躲出来一个圆,站在中间,雪好像也闪了出来,周围地上干净得不像话,没人踩,没人靠近。
雪花一会儿就铺满了,不知道这次要下多久,我从怀里掏出根烟,点上,又灭了,打火机火苗弱得不行,费了会劲,勉强着起来,吸了一口,往天上吐。远处有人叫警察过来,径直往我这走,快到了又绕到一边。我掂了掂这手枪,是这么回事,就是不知道和真的放一块,经不经打。雪几分钟就变个样,随着风摇摇晃晃,像块破布。其中一个警察藏在了冬青后头,说,放下手枪。我心想,如果大雪不停,兴许我妈这会走到沈阳了,可惜路有尽头,天会晴,晴也不见得是个好事。具体站了多久,不清楚,马路上有车开过,红色,和个虫似的。我把手枪举起来,瞄准那辆甲壳虫,它跑得飞快,枪口跟不上。我站在原地,就那么一直抬着胳膊,等着雪落,等着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