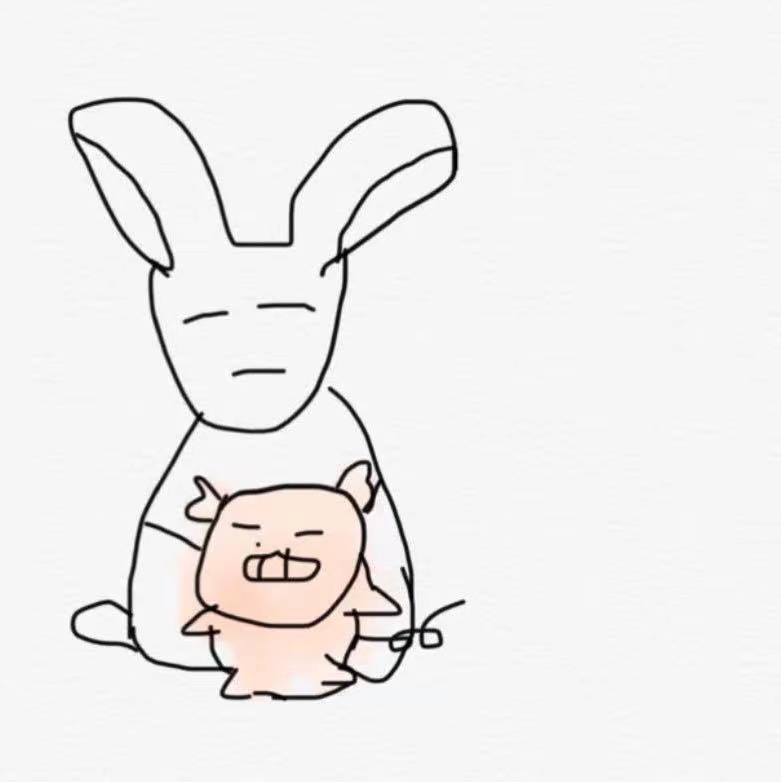离婚,生病,责任,义务,每个人都被牵扯,又都在做一只,把脑袋背过去的猫头鹰。
祖父变成猫头鹰后,曾经回过一次江城。
那天是除夕,全家人都在,天已经黑透,但鞭炮声还没响起来,大概是春晚第三或者第四个节目演出时,小豆从阳台跑进客厅,说外面有一只猫头鹰,我和父亲对视一眼,撂了筷子就往阳台挤。外面果真有一只猫头鹰,就停在窗外那株有五十岁年纪的楝树树杈子上,圆滚滚的,羽毛丰满,爪子稳稳捏着树干,歪着脑袋,两只眸子反着路灯灯光。它看到我们一家出来后,转了几下脑袋,翅膀一扬,飞走了。
“错不了。”父亲说,“是你爷爷。”
我说不一定,可能就是猫头鹰。父亲把我和小豆一搂,我们回到客厅继续看春晚。午夜,我带小豆出去放鞭炮,盯着那根猫头鹰待过的树枝瞅了半天,隐约看见两丛爪印,前三后一,刻在杈子上,卷着白边,我想可能真是祖父,祖父在厂里当了三十年钳工,力气奇大,别的猫头鹰抓不出这种印子。
我很容易想起我们最后几次见面,都在病房里,祖父那时已经开始绝食。第一次去住院部看望他时,他平躺着,闭着眼睛,嘴巴微张,鼻孔里插着氧气管,胸口贴了三处电极,心跳划出的线像一串阴晴不定的山峦,这是间双人病房,另一张床还没病人入住,被子被护士叠成一条扁平洞穴,匍匐在摇起来了的、前高后低的床铺上,窗外有一株五球悬铃木,上了年纪,宏伟而衰败,毛絮在阳光里飘着,我咳嗽起来。我安静地坐在窗边整一刻钟,突然意识到祖父正在装睡。我轻拍祖父的手背,他缓慢睁开眼睛,看向我。
彼时我刚办完离婚手续,带着小豆回到江城,尚未计划下一步。我们俩搬进五金厂家属院,祖父家,一间明亮的小房子,60平米,有手打的木头柜子和茶几,原本朱红色的漆斑驳褪到棕色,在祖母曾经的卧室里,我贴着墙,拉出沙发床。小豆睡在大床上,枕头旁堆有几只玩偶,海獭、狐獴、一只曾经会唱歌但现在沉默的无尾熊。
我和父亲换班照顾祖父,我值夜班,父亲值白班。住院部的晚上是一种有规律的安静,仪器的声音,窗外的声音,偶尔,走廊上有稠密的脚步和轮滑动,最初让人惊慌,习惯后就容易忽略,祖父有时半夜起来,剧烈咳嗽,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不知道该怎么帮他。某夜,火警铃突然响起来,我走出病房,看见手术室门口有两个老人正在跟值班医生吵架,地上有一个陶瓷盆,里面有正在燃烧的黄纸,烟往上爬,撞到天花板然后散开,我回到病房,看见祖父醒了,睁着眼睛,望着窗外。
“你和华玉散了?”他问。
我说没散,就是离婚了,以后过日子有什么肯定也互相照应着,你别担心。他问那小豆呢,我说我照顾着呢。祖父把脑袋扭回正面,闭上眼睛,睡着了,我走到窗边,想开条缝透透气,祖父突然又蹦出来一句,问之后什么打算?我说歇一歇去湖南,有几个关系好的老同学一直在那边发展,叫我过去,看看机会。祖父再没回话。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向小豆解释华玉和我们的分离,但小豆没问我这个问题。她用一个21寸的拉杆书包,装好自己的书和玩具,和她的妈妈告别,牵着我的手和我回到了江城。
小豆刚上小学的时候,有朋友送过我们一只金毛,刚断奶,跟拖鞋一样大,全身毛色很淡,唯独耳朵是深棕色。小豆给它取名叫安静。我们叫:“安静!”,安静就安静蹲坐在地板上,像是听懂了名字的含义,我给小豆看了很多成年金毛的视频和照片,小豆不相信安静也能有如此威风的体型,三个月的时候,安静长到了近一米长,站起来能扒住窗台,它时常跟着小豆,模仿她的动作,跑、跳、躺在地毯上,三个半月的时候,安静突然死了,没人知道安静的死因。那天是周末,小豆去上钢琴课,我和华玉去看了场电影,回到家,发现安静趴在阳台上一动不动,我去摸它,发现它已经失去了温度,肢体僵硬,被死亡固定在那里。华玉留在家里,我把安静的尸体放进一个纸箱子,开车至郊区,找到片树林,把纸箱子埋在一株松树下,覆盖一层薄土。晚上,小豆回到家,找了一圈没看到安静,问我们安静去哪了?华玉在洗澡,我把手搭在小豆双肩上,直视她的眼睛,说安静回家去了,安静的家人也想它了,小豆问安静是不是死了,我回头看向卫生间,灯亮着,水声透过玻璃门传到客厅像是隔了一层鼓皮,有种雾里看花的怅然,我说是。我突然想到,原本可以在埋葬安静的地方插一根树枝,或者只是一根狗尾巴草,但我忘了这么做,可能已经没法再找到墓了。
祖父的心脏不好,晚上经常停跳,最开始几天让我紧张,叫了很多次医生,后来也渐渐习以为常,我看着心脏检测跳出警报,“心跳漏搏”,心里默数一二三,警报声就消失,屡试不爽。
某个夜晚,我去换班,隔壁病床来了新病人,和祖父差不多年纪,全身不少管子,持续呢喃着。父亲坐在窗边,告诉我华玉今天来过。我说挺好,爷爷开心吗,父亲说不知道,你爷爷一直在睡觉,华玉坐了两小时,剥出一个橘子,吃了两瓣就走了。我说她最近累坏了,创业阶段,提着一口气在拼呢。我抻好行军床,铺好褥子,父亲还坐在病床边,摸着祖父的手,跟拖把杆一样粗细,皮肤薄薄一层,绷在上面,留置针显得突兀。他说出去透透气,你爷爷这会儿没事。
我俩绕着住院部楼下小花园走,刚入秋,冬青依然翠郁,还没开始褪色,今夜无星,风持续不断,但没到渗人的地步。父亲点了根烟,站在漫步机上晃着身子,他说你爷爷要是愿意好好吃饭,病早好了,现在光靠营养针。我说要不换种药?换种不反胃的,父亲说都换三种了。我一时语塞,父亲抬起右手又猛吸一口,烟头火星剧烈明亮又迅速衰微,夜色的窟窿缓慢愈合,他说:
“我不了解你爷爷。”
我站在扭腰器上,双手握着固定在正中的轮把,能听见医院外的麦田里田鸡此起彼伏的叫声,穿过麦田后,有一条运行时间长久的火车轨道,我七八岁时,曾坐上一列双层火车驶过这条轨道,趴在玻璃上看向窗外,一切都很新奇。我说,怎么样算了解?父亲把烟头扔到脚边,踩灭。说,度这个东西,很难把握。过了半天,他又扔出来一句,华玉是很不错的人,但不怪你,缘分尽了就没辙。
今年,小豆暑假时,我和华玉为她报了附近山里一家野生动物园的短期夏令营,我陪同参加。我们住在一片名为小熊猫庄园的森林里,几栋木屋别墅,有八角型尖顶子和船木老料打造的家具,坐在阳台上就能看到抱着树干的小熊猫,表情憨厚,这里氧含量较高,每一觉都能睡得很熟。小豆每天参与动物园提供的各项活动:举着水枪给犀牛洗澡,坐在湖边观看鱼鹰抓鱼,喂喂猕猴,丛林穿梭和滑草,还有吃过晚饭后用灯诱捕捉螳螂,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戴眼镜男人给他们讲解螳螂的种类,一个月时间,每天安排得满满当当。
最初几天我都跟着,时间久了就有点盯不住,精力跟不上,脑袋晕,睡觉也缓不过来,我就让小豆自己跟着带队老师玩,别乱跑,自己在别墅里歇着,偶尔出去散散步,和其他家长们聊聊天。在动物园西南角,有一个微型湿地,周长百米余,河岸边有接近腐朽的木制栏杆,芦苇横生,穿透木板搭构出的行路,那里生活着一种全身通黑唯头白的鸟类,像小野鸭,飞起来露出纯白底羽,像水墨画,我查了资料,得知这种鸟学名叫白骨顶鸡,按说是冬候鸟,不应该能在南方的夏天看见。
我开始观察白骨顶鸡的生活,偶尔用手机拍拍照,它们很喜欢浮在水面上游弋,喜欢穿梭在稀疏的芦苇丛间,不时晃动身子、不住地点头,有时离我近了,我大叫一声,会把它们吓得一股脑全潜进水里,只在水面上留下大大小小的波纹。有一个女孩也是这片湿地的常客,年轻人,喜欢戴亮色棒球帽,头发卷曲但有光泽,只到脖颈长度,眼睛极其有神,能一眼看到湿地对面草丛里的蜥蜴,盯得我心里发慌。一来二去,我们很快熟起来,她叫周亮,是北方某工科大学学生,暑假过来当义工,会比我们更深入接触到黑熊等猛兽,每天下午没事了,就过来用一台老相机拍鸟。后来我抽了一天时间,坐车到市里也买了一台数码相机。周亮邀请我,和她比赛,看看谁能拍到最美的白骨顶鸡,我说这太主观了,谁来评判呢?她说让孩子来。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我和周亮每天拍摄白骨顶鸡,不停推翻昨天的自己,周亮每天只按一次快门,通常是在刚到湿地或者即将离开湿地时,她说要把相机当画笔,只画最好的那一幅。我有时恍惚,觉得自己能跟白骨顶鸡通感,拥有它们的翅,拥有它们雪白的喙,拥有它们细长的腿、趾,也拥有它们终将迁徙的习性。我也拍了很多张周亮,大多是眼睛,她不躲避镜头,眼神比湖泊更加坦然,我拍下她卷曲的头发,拍下她手臂上泛着柔光的汗毛,拍下她略微驼背的身躯和细长脖颈,拍下她一直挂在脖子上的动物园工作证,其侧面有几处开裂,周亮用两条印有兔子的纸胶带细心地在头尾各缠了一圈,现在比磐石还坚固。
夏令营进入尾声,我和周亮把各自引以为傲的白骨顶鸡照片洗出来,邀请夏令营的孩子们前来评判,我们票数相差不多,几乎所有孩子都做了选择,唯独小豆看着我和周亮拍出的两张照片,别开脑袋,说什么也不投票。
凌晨四点,我再次被医院楼下救护车的铃声吵醒。祖父睡得正熟,侧着身子,窗帘缝隙流出来的月光隐约能勾勒出藏在被子里的枯槁。隔壁病床的病人不再呻吟,我转过脑袋,看见他仰躺着,弓起右腿,被子掉在地上,一丝不挂地睡着,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详细地观察到一具被衰老侵蚀的躯体,他的胸前肋骨硬撑起血肉,乳头带领双胸的皮肤堆积到肚脐之上,会阴部的毛发灰白且稀疏,阴茎和睾丸蜷缩在一起,垂坠着,双腿青紫遍布,脚踝处血管明显,在皮肤下像山脉中夹杂的河流一样攀附其中。他的心电图像我们写字时会画出的波浪线,但更平缓。我起身去叫护士。他很快被推进抢救室。
天亮后,祖父依然不吃饭,小豆早上跟着父亲过来,我偷偷嘱咐她,劝劝太爷爷,她拍拍我的手,说包在她身上。我回家睡觉,闭上眼睛却总能想到那具垂危之人的胴体,淡蓝色的,像条被拍在干燥病床上的鱼,似乎先生命离开之前就已停滞,我睡得不安稳。小豆中午吃过饭回来,告诉我太爷爷中午喝了半碗稀饭,还告诉了他一个秘密,我说既然是秘密,那就不能往外说,小豆嘴快,直接说出口:
“太爷爷能变成猫头鹰。”
我问是哪种猫头鹰,她说没讲那么细,就趁中午爷爷去打饭时告诉我的,我说那你相信了吗,她说最开始没有,但太爷爷有证据,我问是什么证据,小豆伸出手,对着太阳光弯曲食指、中指、无名指和拇指,比出一个鹰爪的形状,我点点头,说,明白了。你不能再告诉其他人哦,这是你跟太爷爷两人的秘密。下午饭后,小豆邀请我去一个地方,秘密场所,她偶然间发现的,我欣然接受。她牵住我的手腕,我们走回医院,到东南角,一栋荒废的三层小楼旁边,这里曾经是隔离住院部,非典时兴建,我小时候得水痘时住过这里。小豆带着我绕过住院部,踏在杂草上往楼后走,我们路过一些塑料垃圾、一些并不惧怕人的鸽子,这里的杂草坪尚未被人踩出道路。我们走到荒废住院部楼后,这里有一座花园,狭长形状,夹在住院楼与围墙之间,很微型,小豆凑上来,问怎么样,我努力搜寻记忆,始终没找出这座花园的存在,可能是我的病房在另一侧,又或者我囿于传染病与被困禁的苦闷,竟忽视掉了它。我说我说不上来,小豆,这里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花园中间立着一座假山,上面有两串红漆写出的书法字,褪光颜色,走近才看清上句——得山水清气,下面一句藏在草里,我害怕惊到毒虫或草蛇,就没探开,假山旁有一方水泥浇成的小潭,池水早干透,黑绿色的青苔在水泥中间点下,也干枯,生命枯萎成一抹浓墨。小豆站在假山旁,突然不走了,她说,爸爸先走,我要歇一下。我说好,离草远点。我绕过假山,看到假山后藏着两套石桌石凳,然后就是尽头围墙,此时落日,余晖从围墙上切出隐约边界,两套石桌都被分进了阴影里。我先看到了远处那套石桌,空无一人,然后又看到贴着假山的那套,有人坐在上面,我停下脚步,假山挡在我们中间,我看到一双手,修长白皙,指甲修得整齐,十指交叉相叠,摆在石桌上,我看到一双运动鞋,并拢在一起,白色长袜,大部分都被藏进牛仔裤里。我走出假山,华玉没看我,正盯着远方花园尽头的墙壁,她假装没注意到我此刻正在这里站着,等待我出声,搅散漂浮在这座被遗忘花园里的静默,我停步,回头看向小豆,她也看向我,我张开嘴,始终没能说出什么,我们三个曾经是一家人,只是现在分离了,是否我现在走过去牵起华玉和小豆的手,我们就能返回那间现在已经属于华玉一个人的房子里继续去过幸福的日子呢?我如同回到了被关在旁边这栋传染住院楼里的时刻,失去了探索答案的勇气,或许是因为答案不存在于这个时空里。
我转过身,牵起小豆的手,离开这座隐匿花园。
傍晚,福利区开始下雨,最初细碎,挟着雾一起流在身周,几声雷后就变得粗暴,我打着雨伞往医院走,雨滴把伞布撞得砰砰直响,水洼鳞次栉比诞生,飞溅水花,打湿了我的两个裤脚。我到病房里的时候,祖父醒着,穿戴整齐,头上戴了顶棉帽,驻着拐杖,站在窗边看着雨水被风吹得乱飘,砸到他面前的玻璃上,他说华玉刚走,我说这么急啊,正下暴雨呢,祖父头也没转,说,因为我告诉她你快来了。
我把伞靠在门边,开始撑行军床,祖父拄着拐杖走过来,在床尾坐下,俯视着我,他说: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抬头,看见祖父的两只手都撑在拐杖柄上,骨节粗大,血管突出,祖父咳嗽两声,说:
“我害死过两个人。”
我停下动作,站起身,祖父的目光毫不躲闪,没有表情,盯得我心里发毛。病房里的钟表和仪器在嘀嗒响,雾化器挂在墙上,和氧气管绑在一起,祖父过于干瘦,衬衫领口空荡,很容易就能看见他胸口上方因为贴电极片而形成的淤痕。他今天刚做过CT,肺部炎症已经消了,拔了留置针,住院观察几天就能回家,但仍然拒绝吃饭,靠营养针度日。医生说是心理问题,我和父亲决定先让他出院,或许离开医院后心态会有所转变。我在祖父身边坐下,问是当兵时候的事吗?他摇摇头,说是这几十年的事情,当时刚让你爸接班进厂,没事干,就每天去南山捕野鸡,带到马路上卖,那时常跟我同去的是我的徒弟,叫小四,东北人,刚三十出头,我俩骑着他新买的弯梁摩托往山林里钻,后车架上挂着饵料和网兜,我包里有把气枪,防野猪用。一天黄昏,我们蹲在设好的陷阱旁边等野鸡上钩,突然看到一只黑色的鸟正往树冠上冲,燕子大小,但双翅展得直,嘴是弯钩,一看就是猛禽,树冠上有个巢,里面有一只老鸟,圆滚滚,看不清品种。
我说黑鸟可能是隼,咱们这边总能见到。
祖父说不清楚,后来就想不起来具体啥样了。黑鸟和老鸟打半天,老鸟从空中掉下来,摔在石头上,晃悠两下脑袋就不动了,我掏出气枪,瞄着黑鸟打了一枪,应该是擦到点边,把黑鸟吓跑了,小四爬到树冠上,掏回两只绣鸟,黄头黑背白肚皮,拇指大小,我们各带一只回家养着。
我记得那只绣鸟,记得其音色清亮的叫声,但不记得它死亡的时间了,童年的记忆成年后就缠在一起,只隐约留下一幅画面,冬夜,祖父坐在阳台上听收音机,暖气包上放着橘皮,一只木制鸟笼挂在窗台上缘,里面卡着两个小盅,被灰尘填满。
祖父接着讲,后来你奶奶去世,你爸辞职,跑到北方,有一天我去阳台,看见鸟笼门开着,绣鸟不见了。我端着气枪在家属区里绕了几圈,没找到,我去小四家,小四刚钓鱼回来,媳妇正在炖汤,留我吃饭,我坐在客厅,模糊听见绣鸟叫声,像是两种,我走到他家阳台,看见笼子里有两只绣鸟,正是我俩八年前从山上摸下来那两只。吃完饭,我让他开了瓶酒,喝到位后,我问他我的绣鸟怎么跑他这了?他还惊讶起来,说师父开玩笑呢,咱俩的绣鸟不是两年前同一天死的吗,这两只是我带着茵茵去花鸟市场买的,才一岁不到。我当时就拍了桌子,没控制力度,陶瓷盘子都震起来,碎了满地,我说你别装蒜,当着家人面,我不收拾你,你想清楚了来我家找我,小四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师父,你的鸟早死了。
我把手搭到祖父手腕上,他颤抖着,腕关节突出像一把锁,正濒临被打开前的悸动。我说不说了,爷爷,以前的事了。
祖父摇头,说这事不能带走。当晚我从小四家出来,回家待阳台上,自己又喝掉半斤白酒,越琢磨越委屈,半夜,我拿着气枪出去,跑到小四家楼下,照着阳台,两只绣鸟鸟笼的位置上开了一枪,玻璃碎,灯很快亮起来,我酒醒了大半,在路边抽了两根烟,回家把气枪锁起来,气枪子弹埋到楼后槐树下。第二天,听说小四瞎了一只眼,窗户被打烂的时候他正巧坐在阳台上抽烟,玻璃渣子掉进了眼眶里。我凑到五万块钱,去厂医院看他,他脑袋上缠了几圈纱布,让我坐,我把钱掏出来,他没接,问是我打的吗,我没敢认,说不是,他说他信我,我是师父。这钱他不能收。后来出院后小四和老婆离了婚,办了病退,钱不够花,就跑到他女儿学校门口推个车卖早饭,初中时候,班里几个女生因为小四独眼笑话茵茵,干了几架,茵茵没干过,就一直受着欺负,初二刚开学第一个礼拜就从教学楼跳下来,没摔死,脊椎骨折,瘫痪了,那年除夕,小四在家打开煤气,俩人一起走了。
祖父哭起来,腰背弯得像一块失去内容物的蜗壳,颤抖着,没有声音,幅度很小,不时抬手用手背抹掉眼泪和鼻涕。我伸手替他取掉帽子,轻拍他的肩膀,我说你糊涂了,爷爷,四叔每年都来给你拜年的。他眼睛没瞎,身体好得很,就是头顶秃了。他前年调度岗退了,干部待遇,在省城买的房带个院子,养赛鸽呢。茵茵上完大学又去国外读了个研究生,现在留新西兰了,我俩现在还加着微信,逢年过节都有联系。
祖父看向我,沉默半天才开口,说他可能真糊涂了。我说记岔劈了,回头让四叔给你搞俩鸽子,你再养养,比绣鸟有意思。他点点头,脱光衣服躺进被子里,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窗外的雨到后半夜才停,我出去转了圈,发现冬青树被淋掉不少叶子,摞在树坑里,几百米外的稻田,再也听不见青蛙叫,此时雨停,秋天正式到来。
我回到病房,看见祖父变成了一只猫头鹰。
他蹬掉了自己的被子,蜷缩在床上,侧躺着,头部宽圆,眼周羽毛向外辐射,左眼睁着右眼闭紧,双翅收拢在身旁,尾羽看起来十分坚韧,双爪摊在床单上,强锐内弯,但此时松懈着,毫无力量感。
从动物园回来时,华玉还在外地出差。一个下午,小豆去隔壁小区的同学家打游戏机,我送过去后一个人回家睡觉,醒来时天已半黑,卧室没开灯,蓝色像帷幕一般包裹住整个房间,我坐在床上,想到湿地已经和我分离,恍惚了好几分钟。我光着脚走到客厅,看见华玉已经回来,正坐在沙发上翻看我新买的相机相册,脸上有笑意。我没出声,小心翼翼地把身子靠到沙发上,在她后面看着,华玉看到小豆的照片,看到动物园里的那些动物,看到那片湿地,看到白骨顶鸡,看到周亮,看到周亮的棒球帽和被晒成褐色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沾染泥巴的徒步鞋,华玉不再笑了。她把相机相册划到最前面,重新又看一遍,我站在沙发后面,把身体藏在沙发旁那顶暖色立灯照射不到的黑暗里,双脚踩在羊毛地毯上,痒从脚心传来。华玉看了三遍,把相机放回包里,小心翼翼地拉上拉链。我慢慢退回卧室,盯着表,等待五分钟后重新走进客厅。华玉冲我笑,说等小豆回来,晚上我们去吃西餐吧。
我说华玉,我出轨了。
华玉的眼神落向地板,我们刚搬家时一同选定的橡木地板,上面保留了一些天然的树疤。她说你别乱开玩笑,我说相机里的那个女孩,我喜欢上她了,我不能瞒你。她蹲下来,无声无息地落泪,她说没看到什么相机,没看到什么女孩。
天亮后,祖父变回人类。
他穿戴整齐,拄好拐杖,跟我一起去医院食堂吃早饭,步伐矫健,精神抖擞,我们一落座祖父就开始点菜,待我把餐食全买回来后,祖父却不见了,只留拐杖靠在椅背上,我在食堂外跑了一圈,终于在人造湖中的石亭里找到他,他靠在亭柱上,盯着天空看,我安下心,喘着粗气走到亭廊下,我问在看什么?爷爷。祖父扬起下巴,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向远方,高积云凝固在空中,太阳被挡在其后,光射出来,一队白骨顶鸡,正从北方某处湿地迁徙而来。我问祖父认不认识这种鸟,祖父点头,说是候鸟,统称没有家的鸟。我看到云逐渐散去,白骨顶鸡雪白的喙和纤细的足肢快速飘动着,我说爷爷,我犯了错。祖父在亭椅上坐下,水面安静地漾着波纹,反射出光斑,撞着我的眼睛,我说夏天时候,我带小豆去动物园参加夏令营,认识了一个女生,相处些时间。离开前,我约她去林子里走走,散散步,到安静的地方去,半山深处,只有蝉鸣鸟叫,我问她要不要和我一起走,她问去哪里,我说很多选择,国外、北方、温暖的地方、冷的地方,她问那我女儿和妻子呢,我站在几株近百年树龄的参天巨木里想了几分钟,我说我都可以不要,只有我,和你。
祖父低垂着脑袋,呼吸声沉重,我把手掌贴上他的脊背,他的脊椎像明灭交替的海浪,因为饥饿而松垮的血肉翻涌出褶皱,他睡着了,但睡得汹涌。我抱起他轻薄的肉体,像抱起一朵水花,我们回到病房,他再次沉没进病床上。
正午时候,父亲带着小豆一起来了,祖父依然没醒,我和小豆去食堂带午饭,回来后,祖父睁大眼睛望着窗外,父亲坐在床尾边的塑料凳上,正在叠祖父脱下来的裤子。祖父看见我们回来,一脸严肃地开口:
“把窗户打开吧,我得走了。”
窗外起风了,这是秋天的风,五球悬铃木的毛絮充斥在半空中,我没看父亲和小豆的表情,我想,或许我们三个都知道祖父在说什么。父亲的手僵在空中,片刻后缓和,继续叠起衣服来,祖父伸出食指,指向我和小豆,说我们不能在这儿,用不上我们,小豆走上去抓祖父的被角,祖父把脑袋别过去,说快点的吧,一会儿就错过这场大风了。父亲站起身,打开窗户,我牵着小豆走出病房,走到楼下花园的长椅上,小豆扭头,一直盯着祖父病房的窗口看。梧桐树的树根扎进湿润的、褐色的土壤,分界并不明显,在树根与水泥台中点处的树坑里,插有根粗壮的狗尾巴草,正因风摆动,我稍微探头,看见狗尾巴草根部,挨着一块圆形的淡黄色鹅卵石,唯独石心处有一抹深褐色。有扇翅的声音传来,我回过头,看见一只猫头鹰从祖父病房的窗户里飞了出来。
“爸爸。”小豆说,“如果你有什么秘密,绝对不要告诉我。”
猫头鹰飞过我俩脑袋上方,我转过头,看见祖父的身影飞向南方,很快就从视野边缘的地平线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