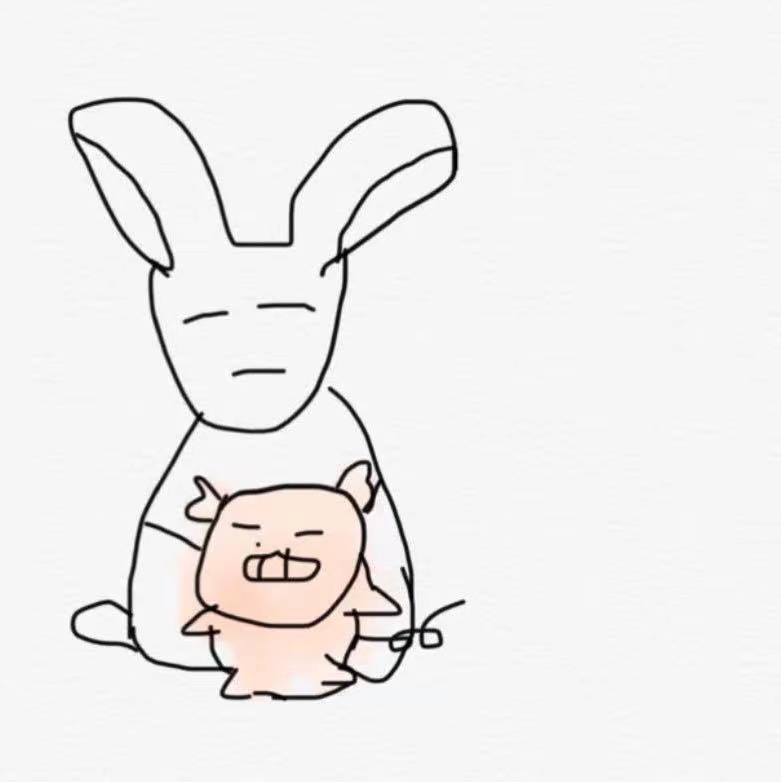为了拍出想要的纪录片,我谎称自己后天失明,开始与盲女一起生活,光明正大地偷拍素材,并与她产生“爱情”。
在湖城的那几年,冬季总有暴雪,昼夜不停,吴佳有时坐在阳台上,说看过一篇武侠小说,盲剑客,练成一门绝技,能通过听物体碰撞的声音判断出物体的形状、重量、大小和加速度,包括雪花,我问那你可以吗?她说不行,咱家是双层玻璃,有回声,循环往复地,把清晰搅成模糊了。
临近过年,吴佳放了长假,我们开车去三十公里外的冰瀑谷,闻梅花开放时的气味,半路上撞了车,路面结冰打滑,我没估算好刹车距离,撞上护栏,气囊弹出来,前保险杠耷拉着。等待拖车的时候,雪又落下来,我俩站在公路外的一株松树下,不住地跺脚,泥泞被雪压紧,吴佳钻进我怀里,我按住她的肩膀,她颤抖着。
四年前,我刚从学校毕业,每天都闲着。彼时有同系的学弟准备拍一部讲述老年人黄昏恋的纪录片,我觉得有意思就一起跟着,我俩当了半年婚恋中介,攒下不少素材。出乎意料地,片子得了奖,国内国外的。那段时间酒局不断,他的导师也宴请我们几次,带着醉意说我们有天赋,趁着年轻,应该多拍拍,说不定真能把纪录片这条路走下去。
学弟当时就热泪盈眶,说:
“不死不休。”
那之后的一年,我们又拍了几部,题材乱七八糟的,有流浪猫,有快递师傅,始终没翻起什么波澜,一直到冬天,学弟家人和女友一直施压,他泄了气。某晚,我们约定重返母校,最后再吃一次食堂就散伙,走出校门,学弟终于还是哭了,他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
学弟退出,留给我所有设备。我又独自摸索了半年时间,毫无头绪,直到另一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吴佳。我们一起出来喝了几次东西。吴佳个子不高,头发短到耳后,脸和肩都很小,笑起来爱露牙龈,总穿连衣裙,戴圆框墨镜,墨镜后的眼睛只能隐约看见几团黑影,所有事物的边缘都混淆一团,什么都无法分辨。
我让朋友谎称我刚得了神经系统罕见病,后天失明,只能看见轮廓,想寻找一位老前辈能教我过盲人过的生活,因此想认识吴佳,吴佳一口答应。
我开始偷偷拍摄吴佳的生活细节,这相当容易,她是被留在更低维度的人,只能指望我们这群双目健全之人保持善意来拥有自己的隐私。我从未如此明目张胆地偷拍过一位女性,为此才会对人类肢体能有如此多细节表现感到诧异。吴佳的动作都很“微”,平时我们能一步做好的动作她需要四五步才能完成,比如用杯子喝水,我们会把杯子端到嘴边,吴佳会缓慢地握紧杯壁,平稳垂直地让杯子分几次上升到她嘴唇的高度,之后再向嘴唇平移,直到二者相遇,才倾斜杯壁。这些动作让她像一只架在炉子上的茶壶,被沸水拨动,轻微、不停歇地保持颤抖。
吴佳有近30岁,长相普通,她是大四时失明,距今只有七八年,所以能跟我聊到一起去。我们聊到一些老电影时,吴佳总能说出些我没能看到的细节来,最开始我以为是她原本就有足够强的记忆力,后来当我们住到一起后,我才发现谜底是吴佳会反复地听曾经看过的那些电影的解说,每一位解说都不放过。有一天,我问她为什么一直听以前看过的电影,她说怕忘掉。我们相处了大概半年时间就住到了一起,在这之前也谈了三个月恋爱,追到她相当容易,她的情感很好把握,多关心几句,多做点事,尽管她自认为有所保留,但其实早已被失明开膛破肚。一次约会,我特意迟到半小时,架好相机记录下吴佳从从容到焦急的全过程,她站在原地,不停地用手机听时间,给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未接通后,她离开我们约定的地方,只走了几米,又走回来,低着头,继续站着。那时候我在想,假如有人需要对吴佳来一场最恶劣的复仇,那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成为她最好的朋友。可是吴佳没有朋友。她独居,做着很少接触外人的文字工作,爱好是听电影解说,这让我觉得素材有些单薄,于是才有了更加深入接触她的计划。
吴佳的家里墙壁上贴满触感不一的胶带,用来提醒她所处的位置,我在几个角度安装好隐藏摄影机,得以记录下那些更加私密的时刻,偶尔我会过来住,我们睡在一起,灯很少开,因为吴佳能感觉到灯泡的温度。和我想象中不同,这间屋子并不让我压抑,吴佳把它塞得尽量狭窄、拥挤,借此明确自己的空间。
我们也会外出约会,散步,去咖啡店喝点东西,她曾经拥有过一只萨摩耶,找人帮忙训练成了导盲犬,四岁的时候生病死去,之后她就只依靠盲杖和记忆在这座小城里行走。
一天,我们走到斑马线中间的中岛上等待下次绿灯时,吴佳突然开口问我:
“你能看见多少?”
我有点心虚,就把眼睛眯起来,说:“很粗略的像素,一根一根的,撞在一起。”
吴佳点点头,把左手伸给我,说那跟着她走就好。
我们第一次做爱也是在吴佳的卧室里。我们喝了点葡萄酒,然后亲吻,来到床上,我剥掉吴佳的衣服,她躺得很直,双臂贴紧两侧,双眼分开瞪着,她有些酒精过敏,脸颊有红晕,微张嘴,轻轻呵出滚烫的气,我用食指在她的皮肤上滑动,像鱼鳍破开水面,吴佳颤抖如海啸,肉随着浪潮涌动。吴佳很瘦,但小腹和屁股上有赘肉,我插入的时候,能感觉到极其猛烈地收紧,压缩着视线所能及的全部,直到归于一线为止。吴佳总会哭。
事后我检查了摄影机,发现其中一台有透过卧室门角度录下床尾的画面,吴佳的两只脚不知所措地摆动着,在某些体位时,像两根被风吹动的树杈。这是不错的镜头,很有可能是能获得大奖的因素之一。我始终没把它剪进片子里,后来就删除掉了。
吴佳可以通过手机的无障碍模式打字,但更多是发语音。她的声音很好听,或者是她知道自己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比较好听。我睁着眼睛听一遍,再闭上眼睛听一遍,听不出区别。我买了几个眼罩,独自在家的时候,我就把它们同时戴上,层层叠叠,模拟失明,房间不会变得未知,只是会让人不安和惊讶,我能在脑海里构建出家具的布局与位置,但真的伸出手,却总扑空。我很缓慢地行动,耳朵变得敏感,但分辨不出什么,我最多坚持过十几分钟,后十分钟只是坐在沙发上,等待钟表秒针一下一下转动,哪怕我知道只要摘下眼罩就能重回光明,也仍旧没能习惯黑暗。
介绍我和吴佳认识的朋友又和我吃过几次饭,问我片子拍得怎么样了,我说说不好,他说怎么,我说就是普普通通的。我给他看了几段视频素材,合上电脑,他也沉思起来。
“有点没劲。”他说,“缺少冲突。”
我说这就是吴佳的日子,平平淡淡的,他说你得当坏人,你得让她有点情绪波动,不管是生气还是伤心。吴佳的妈妈你知道吗?我说只听过几次,好像不亲近,他说里面肯定有戏,去找找看。
吴佳洗澡的时候,我用她的手机翻了翻她妈妈的朋友圈,退休了,每天上午在新城广场练太极剑,今年自驾游去了甘南,拍了戈壁滩上挥舞披肩的视频,还有一家三口的合照,在她儿子的初中毕业典礼上。后来我去了新城广场,蹲了几天点,认清楚了吴妈妈,头发黑亮,束在脑后,身材保持得不错,穿着太极服,动作十分有力,我在树林里用相机录下一段。练完剑,吴妈妈总会在太极服外穿上一件毛织外套,跟两三个老太太结伴去菜市场买菜。有一天,我悄悄跟着,听到她们在说寒假和补习班的事,她们往北走,分开,我跟着吴妈妈一直到机关厂家属院,在单元楼口,吴妈妈突然停住,转身,瞪住我,问我是干嘛的,我放下相机,我想了想,没想出该怎么回答。吴妈妈手里的买菜筐是竹编的,很老式的那种,她把排骨肉放在最里面,上面是芹菜和菠菜,最上面还有包蛋卷,散着热气,给塑料袋镀出一层雾,楼上有炒菜的香味飘下来,吴妈妈看着我,突然解开了眉头,她瞪大眼睛,张开嘴,又缓缓闭上,视线轻轻地飘下去,直至砸在地面上。竹编买菜筐轻轻地摇晃着。
我举起相机,说,阿姨,让我拍张照片吧。
吴妈妈点点头,但眼睛始终没抬起来。我把眼睛凑近取景框,吴妈妈站在单元门外,她的家就在楼上,她的第二任丈夫和第二个孩子正在等她,她想回家,却被我困在咫尺外。我按下快门,感到一种报复的快感,但很快又觉得可笑,她按照法律完成了义务,然后去追寻自己应得的一切,错在哪呢?被我这样的人趁虚而入,抱着目的去接近利用欺骗了吴佳,不是因为吴妈妈的不管不顾,只是因为我是人渣。
我放下相机,吴妈妈几次张嘴,可最终也什么都没问出口。
后来我把这张照片打出来,找了个框,就立在吴佳家鞋柜上,吴佳摸到过,来回摩挲,没问我是什么。我端详过吴妈妈的照片,她额角有还没来得及染的,花白的头发长出来,左边手腕贴了块肉色膏药,藏在袖子的阴影里,和皮肤混着,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吴佳的父亲在南方某沿海城市,据说也已成家,经商,过得比较富裕,在得知吴佳失明后曾打电话来过,问她要地址和银行账户,吴佳没给,总觉得是对母亲的背叛,她再没有别的要好的亲戚,血脉联系只是浅浅系在脚腕上,时间推移,路越走越远,就慢慢干枯断裂。我问她,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就是那种想要和恋人一起去完成的事,吴佳想了一整天,然后郑重地请求我,和她一起去找一个寺。
我问是什么样的寺。她说是一间小寺,不知道在城内还是城外,小时候一家三口坐大巴车去过,一殿一院,院子里有株巨大的树,香火味道很奇怪,混杂着别的,和一般的寺都不一样,后来她一个人去找过几个,都不是。我说信息有点少,可能会找很久,她说没关系,她找了很多年都没找到过,湖城这十年大兴基建,有可能早就拆掉了。
我在网上查了些资料,也实地跑了几趟,始终没找到符合吴佳描述的寺庙,湖城不大,但四周临山,县城很多,野寺更是数不过来,一些老的在手机地图上都没法找到,吴佳作为亲历者,那么长的时间都找空,没理由就能让我碰上。我失去了信心,想着这事就算了,找点别的事当素材拍,日子过久,吴佳总能忘掉。有一天,吴佳叫我去家里,递给我一本厚重的本子,我接过,看见里面记满了日期、寺庙的位置和名字,甚至有几个是在省外,我问这是什么,她说是以前找过的寺庙的名字,都不是。说完,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补充,当时大学时有过一个男朋友,他也帮着找,就都写下来,以免重复。我翻到本子最后,看见最后一次记录的日期是八年前。我把本子合上,说知道了。半夜,将睡未睡之际,又聊到那座小寺,我说要不然去问问你爸爸或者妈妈,吴佳不说话,只有呼吸声轻轻漂浮着。
后来我知道,去那座寺时吴佳刚经历完一场手术,入院前,吴妈妈去庙里许了愿,出院后,一家三口就一起去还愿。坐上大巴,他们三个人挤在两个座位上,吴爸爸给吴佳披上自己的工装夹克,以免她受凉,吴佳被两个人牢牢夹住,心里安心,很快就睡过去,再醒来,就已经到寺院门口了。还完愿后,他们在院中等待返程的大巴车到来,吴佳坐在院子里一张木制摇椅上,父亲轻轻摇着她,她太过瘦小的身体没能坐满整张椅子,不停上下滑动。母亲在跟院子里一个穿着运动服扫叶子的女人聊天,院中那棵大树把阳光滤成丝状,蝉鸣不断,她问父亲是不是不用再回医院了,父亲把手放在她肩膀上,说他做主,不回了。后来大巴车回来,一家三口回到家里,三年后,父母离婚,父亲去了南方,母亲留在本地,再次结婚,她跟着祖父祖母一起生活,大四那年,她再次因头痛住进医院,出来后,神经畸变已经夺走了她的视力。
我决心找到这座寺。
问了几个朋友,有人提了醒,这么多年,寺院不一定能保留下来,但那么大一棵树,很可能是古树,去网上发发帖子,湖城树木爱好者很多的。我发了帖子,编出一个更加值得同情的故事:祖父曾在此寺庙当过很长年岁的义工,如今确诊老年痴呆,希望能找到此庙,唤回理智。
底下回帖不断,大多贴有照片,我记在笔记本上,挨个找过去,但都落空,要么是近十年重修的,要么就是格局不对,门口也从来没有过大巴线路。最后,一个网友突然说搞不好不是寺庙,是金台观,供的是张三丰,当年坐1路车就能到,院子里有一株巨大的银杏,秋天白果成熟,会有墨香味。
我一下子激动起来,是啊,吴佳和她前男友跑了本市一百来座寺庙都一无所获,越发执着,反而忽视了一开始那里就不是寺庙的可能,吴佳的记忆过于遥远,且多次回忆,侧重点都在于如今已经荡然无存的亲情上,当然会出错,找东西往往就是这样,有执念,就会走上歧路。我拎着摄像机到金台观,道观应该已经重修过几次,里面宽阔无比,铺满水磨石,主要建筑按中轴线排列,大殿也是标准仿古建筑,有翻飞的檐角和斗拱,没见到树。我逛了半圈,在院中门廊墙上看见金台观以前的照片,一座小院,大门正对着一株巨大的银杏树,树后就是平房样式的主殿,和吴佳描述的一模一样。我抓到一个路过的道士问树呢,道士问哪颗,我指指照片,道士说树早死了,千禧年前后好像就死了,但一直立在那,树身不腐,叶片不落,只是不再结果,所以大家都没发现,后来10年重修时候,几个师傅轻轻一推,树就倒下,摔在地上,里面早就空了。我说那怎么可能?道士笑了笑,行了个拱手礼,走掉了。
我回到家,吴佳正在阳台上坐着,外放着电影解说的视频,闭着眼睛,不知是否陷入沉睡,夜幕将至,天际线酝酿蓝色,落在脸上,有暗淡的反光。我瞒下金台观的秘密,所有亲历者都已离去,时间总是这样一去不复返,回忆到最后,会把一切化为齑粉。吴佳突然睁开眼,问我还记不记得正在解说的这部电影,我说大差不差,谍战片,打打杀杀的,剧情比较简单,她说,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里面有些画面,她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坐在沙发里,身体塌下去,终于,夜晚完全来临,房间里只留下模糊的影子,我说,吴佳,你小时候去过的那个寺,我找到了。
我曾经想过,或许失明对吴佳是一种解脱,视角的缺失,让她得以不去直面那些砸到她头上的一切,碰撞解不干净的谜团,但相处时间越久,这种念头就越发可笑。我渐渐明白,失明不是拿走了吴佳的现实,只是冷静地给予她一个更加窘迫的疆界,任何人不得入内,她闭上眼睛,可世界不会就此熄灭,她不是失去了看的能力,而只是什么都看不见了,两者的区别像一根肉刺,扎在她脚心,以至于她永远没法停下来,获得安宁。
除金台观外,湖城也有不少老银杏,我对比过,其中最老的种在党校里,枝叶茂密,被单独围出一片空地。我带着吴佳坐上公交车,她戴着墨镜,车一开,世界就摇晃起来,两根导盲杖偶尔碰撞,我扶着座椅前方的把手,吴佳的手叠在我手上。
可能是周末的缘故,党校没什么人,银杏就圈在那里,散发着馥郁气味。我说那座寺庙拆掉了,树迁了过来,是银杏树,等到秋天,叶片就会变得金黄,落下来层层叠叠,能堆出一片沙滩。吴佳攥紧我的手,说,她能想象到。吴佳走过去,我偷偷掏出摄像机,对准她,我看见吴佳松开了导盲杖,让它就这么垂落,她伸出一只手贴在树皮上,然后弯曲膝盖,缓慢地跪了下去。我关掉摄像机,转过身,以免余光仍能看见她的身影。我知道再诚恳的愿望也没办法阻止谎言的繁殖,因为那是它唯一的生存法则,我闭上眼睛,像曾经几百次模拟过的盲人生活那样,敲响导盲杖,在地面泛起涟漪,一直荡到吴佳所在的树旁,她流下泪,轻轻一滴,还没到达地面就被风吹散,但声音还是清晰地钻进我耳朵里来。
我从没相信过神明的存在,但至此一刻,我希望有什么至高存在能够消灭我的痛苦,甚至不用宽恕我的罪恶,只是把虚无的引力降到最低,或者单纯吞没。让我能砸烂摄影机,走上去,牵起吴佳的手,也能让我就这么离开,从此再不出现在她的世界里。可事情没有这么容易。我睁开眼睛,一切都还存在,草地,石头,嘈杂摇晃着,亮光汹涌袭来,抓不住什么东西做信标的人只能跟随时间一同腐朽。我回头,吴佳已经站起身,她拍拍膝盖,杵着导盲杖走向我,我把摄影机揣进包里。
返程公交上,吴佳心情很不错,小声哼起歌来,我问怎么样,想起那时候的事了吗?她摇摇头,开心地说:
“这下就能全忘咯。”
我们回到家,吴佳说要给我露一手,她钻去厨房,做微波炉菜,一根筷子来回碰撞,叮咚作响。我知道吴佳很久之前就在用微波炉做饭,前两月还特意听过教学,练习过,但大多时候,她的胆怯总会在这间不开灯的屋子里来回回荡,碰撞,她怕抓得太紧就会任由事物从手中流走,让命中注定的分离来得更加迅速。当晚,我在吴佳家留宿,睡在一起的时候,吴佳拉开我的胳膊,把脑袋枕在上面。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把我置于和吴佳相同的境地,我会怎么生活,是否能有足够的勇气举起那根手杖,接着走下去?或许人在极痛苦极绝望的时刻,才会把握生命的可贵,吴佳一定经历过这种时刻,才能到达现在。可对于我来说,如何到达之后的日子呢?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即使我完成了这部拍摄,获了奖,也不会改变我只有伤害生活才能被存在感找到的本质,我可以不停思辨,不停回望,驻足不前,但生活轮播向前,时间会抛下一切迷惘的人,自顾自地到达未来。
我小心翼翼地抽出手,光脚走到客厅,把之前架设过的摄像机都拆下来,里面的储存卡聚集在一起,扔进垃圾桶里,我回到床上,吴佳已经醒了,但仍在装睡。我坐在床边,只拉着一层纱帘的窗户透着月光,轻松地划出明暗分割线,我伸出手,旋转,看到肤色不断变换,没留下触感。我闭上眼睛,吴佳的呼吸声很轻,持续且柔软,我睁开眼睛,看见我刚才睡过的枕头仍没恢复凹陷。
那么,吴佳又是真的爱我吗,还是为了对抗熄灭一切的夜幕需要抓住漂流至身边的温度,我们无从得知,二者交杂着,细究带不来好结果。
我说,吴佳,我能看得见。从一开始,我就在撒谎,我接近你只是为了偷拍你的生活,尝试做一部视障人士的纪录片,拿去冲奖,我偷窃你的感情,也只是为了你在镜头里能有更多的情绪波动。对于这些,我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也不会恬不知耻地要求你的原谅。
吴佳没说话,没睁开眼睛,呼吸也没有变得急促。
我继续说,我曾经试着闭上眼睛,模仿你的生活,但我相信我得不到你的感受。吴佳,有时我会觉得,我爱着你,但总没有勇气去深究和承认这一点。幻想我们抛开一切枷锁,毫无顾忌地去表达爱的那些日子到来,总让我恐惧,那是一条无比漫长、艰险的道路,很有可能会在半路坍塌,葬送过往的一切。我们无法理解对方的喜乐,更无法触碰对方的痛苦,只有渺茫的火光能给予指引,等待自愈,爱会很单薄,因此需要超越自我的信任感,这对彼此来说都会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吴佳,我很难相信我能做得到。我们有更简单的未来,明天天亮,我会离开,那些摄影储存卡我已经销毁了,你可以报警,我也会倾尽全力去给你经济上的赔偿,然后我这个人就会从你的生活里彻底消失掉。你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总能走出来,我知道的,你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坚强。
吴佳的侧脸下一半被笼罩在月光下,她的脖颈很细,喉咙随着呼吸起伏,那些真正睡着的时刻,她不会把嘴完全闭合。她总是蜷缩着身体睡觉,像胎儿在子宫中的姿势,我站起身,吴佳伸出手,抓住我的手腕,十分用力,快要把我握断,我看过去,看到她睁开眼,眼睛在阴影中闪着光。
“选难的那条。”她说,“我们选更麻烦的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