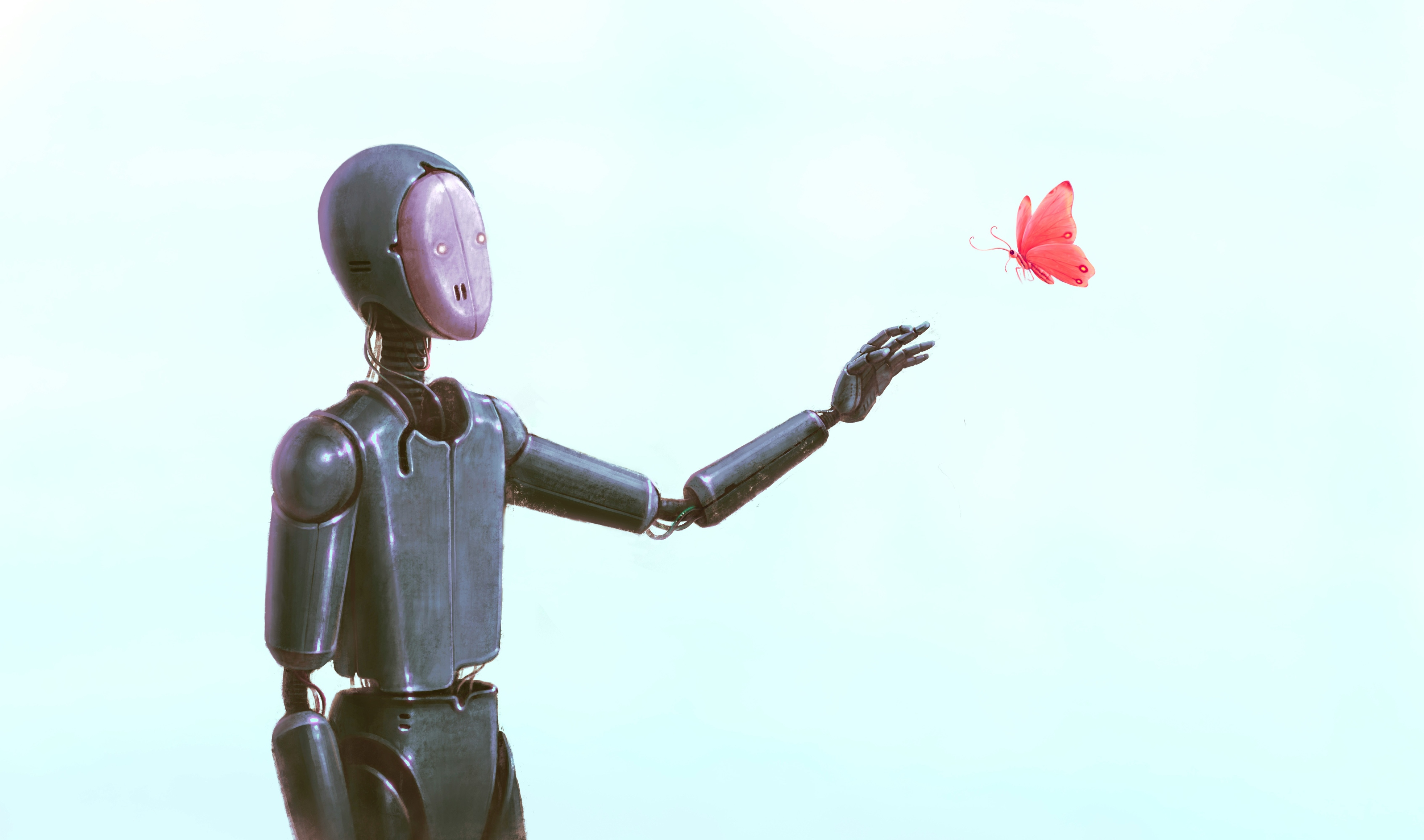
环境污染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动植物体内淤积大量毒素。因此,科学家将人工食品做出两类,元食与末食。前者由筛选出的无毒食材制作,后者则是将含毒的食材,进行祛毒处理后,再加工。但与此同时,带来更显著的阶级隔阂,想吃元食的普通孩子,究竟要怎样才能尝到公平的味道?
1.
傍晚的教室里,只剩下两个人,谭文雅和班主任。文雅是个胖丫头,浑身上下,全是肉,手臂像是一截藕。但这种胖,在高高瘦瘦的班主任眼里,是浮肿,是虚胖,是穷人相,是从小喂末食,喂出来的结果。她踩着低跟皮鞋,往讲台前一站,清瘦的身形就在黑板的映衬下,瞬间有了班主任的力道与威严。黑板上方,贴着六个正楷红字,公平,公正,公开。前门,偶尔有风穿过,将红字吹出横扫落叶的沙沙声。
“凭什么......别人都有的吃,就我没有!”谭文雅攥着未拆封的奶酪棒,舔着唇峰上的死皮,缩在门边,等爸爸来接。平时他不一定会来,但今天一定会,因为班主任打过电话了。
“不要老和别人比,”班主任清了清嗓,重拾教书育人的口吻,“比,是两把匕首,一把刺向他人,一把刺向自己。”
“匕首?”谭文雅举起手中的奶酪棒,看了看。
“奶酪棒,是元食,不在学校午餐里,是同学们额外订的点心。”说完,见谭文雅翘起肉乎乎的下巴,索性吼了一嗓子,“想吃,就让你爸交钱。”
“那班长也没订呀!”
“他,是表现好,我才奖励了一个。”
“这不......不对的。”谭文雅想说“这不公平”,但脑子里一时搜不出“公平”这个词,只好直抒胸臆,“要么大家都有的吃,要么大家都不吃。”说完,她才看到班主任头顶上的六个大字,伸手指了指。
班主任转身,扫了黑板上方一眼,“你觉得老师不公正?”
“班长是你家亲戚!”谭文雅扯起嗓门,“所以你才给他奶酪棒。”
“胡扯!”班主任说完,赶忙冲去关门,可力使大了,压出一阵风,将“公开”二字,吹卷了边。
“我没胡扯!你是他......”文雅皱起眼皮,使劲想着这层关系,往外蹦词儿,“你——他妈!”
此时,合上的门,被一只手推开。是文雅的爸爸,谭天。
“你他妈。”谭文雅急坏了——你!他后妈!你是他后妈!就这么简简单单几个字,愣是说不明白。刚入学那会儿,同学就笑她结巴。但班主任说,这是从小吃末食的结果。末食,没营养,吃多了,影响大脑发育,所以嘴笨。可她知道,这不算啥毛病,她和爸爸一样,一着急,舌头就打结,心里想得再明白,嘴里也讲不清。
“谭文雅,你可一点也不文雅啊!”班主任迅速占领道德高地,“你说说,这学期,都偷了多少回了!”说完,见文雅爸爸皱眉闷头,站在一边,比女儿更像一名现行犯,随即调转枪头,“小小年纪,就爱攀比,别人有的吃,她就也想吃,吃不着,就偷。”班主任的话,叫谭文雅奇怪,偷就是偷,怎么还成攀比了。
“比什么不好,比吃的。”谭天见女儿一脸倔强,眉心的川字纹,更深了,“要比,就比成绩!”
班主任听了这话,又笑起来,“其实身为老师,也理解,自从食物危机以来,别说,学校了,社会上这种攀比,也不少。诶,文雅爸爸,你听说没,为了防止攀比,城里办了一所食验学校,离我们县不算远。坐车,半小时就到。”说着,瞥了文雅一眼,“封闭式管理!”吓唬完她,又扭头继续,“听人讲,那里不吃元食,也不吃末食。”
“那吃什么?”谭文雅够着脖子。
“营养片。一日三餐,都吃营养片,人人都一样,谁也不多,谁也不少,绝对公平,杜绝了攀比的可能。而且听说,那儿的孩子,很不一样,特有教养,张口就是诗词,谚语。”班主任一皱鼻子,眼镜瞬间顶起,“脏话,可是一句都不会讲。”
谭文雅闷下头,快速地翻了个白眼。
“不过那学校,是私立的,不像我们这儿,学费全免,只有订元食点心,才收钱。”
谭文雅隐隐感觉到,此刻被欺负的不是自己,而是爸爸。班主任揉揉太阳穴,继续说道,“学费嘛,是贵了点,但,贵有贵的道理,毕竟那营养片,是最新的研究成果,不仅味道美,营养价值更是元食的好几倍!总之,胖的进去,变瘦。瘦的进去,长肉。”谭文雅不用看,都知道爸爸的眉头,皱成了啥样。他的川字纹里,藏着一根线,一听到跟钱有关的事儿,立马抽紧。而“贵”这个字,就是线头上的针。
“转去那儿,对孩子好,”班主任又轻幽幽吐一句,“不然,为个饭后点心,就偷鸡摸狗,大了怎么得了!”
谭天一听这话,像被上了发条似的,醒过来。一掌打掉女儿手中的奶酪棒,又俯身拾起,恭恭敬敬地摆到讲台桌上,班主任一扶眼镜,“现在还过来,人家还能要吗?”
“不要了?”谭天盯着那根他总也舍不得买的元食。
“你没看见上面的牙印啊?”班主任瞪向谭文雅。
谭天这才留意到塑料外壳上那一排浅浅的凹痕。
“我看,还是早点转学吧。”说完,班主任就趿拉着皮鞋,走出教室。
2.
谭天愣在那儿好久,似乎只要不离开,一切就还有回旋的余地。可文雅才不管那么多。潇洒地走上讲台,抓起桌上的奶酪棒,往书包里一丢,就推着谭天往家走。谭天知道不该拿,但也没阻拦,只是嘴巴还不依不饶。
“你怎么能偷呢!”
“我不偷,你会买给我吗?”
一听这话,谭天就哑了。下岗半年,到处找活儿,但干来干去,都是些短工。后来,听前工友忽悠,叉车挣钱。就买了车,考了证。可去几家厂子一问,得到的回复都是——机器干得比人利索。
“昨天是我生日。”谭文雅说着,举起那只被她咬出牙印的奶酪棒,在空中拧动,塑料外壳随着转动的角度,漾出彩虹的色泽,“你说,妈妈爱吃元食吗?”谭文雅边说,边剥开外壳,“肯定爱吃,因为我也爱吃。”她一口含住奶酪棒,唇齿不动,眼里透出一股馋疯了的狠劲。
早在她出生前,环境污染就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老天总是灰着脸,河流也浑浊一片。但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继续下去会导致大批动植物的死亡,食物危机一触即发。直到一个冬天,科学家在部分存活下来的动植物体内,发现了大量毒素,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民众不懂那么多,只听说,小到米面粮油,大到鸡鸭鱼肉,通通有毒。没多久,各国就先后颁布法令——为避免民众误食毒源,禁止各类生鲜流入市场,所有人必须购买加工好的熟食。可大批动植物的死亡,毕竟造成了严重的食物短缺。因此,将有毒的动植物,进行祛毒处理,再供人食用,成了没办法的办法。
至此,天底下的食物被分成两类,元食与末食。前者由筛选出的无毒食材制作,后者则是将含毒的食材,进行祛毒处理后,再加工。元食,健康,营养,美味,但价格昂贵。末食,便宜,却因深度加工,导致营养流失,只能果腹。不过,末食最为人诟病的,还不是没营养,而是没味道。国际卫生组织担心,长期大量食用末食,对人体有害。于是,禁止末食在加工过程中使用香精,并严格控制调味料的用量。这导致市面上大多数末食都味同嚼蜡。
那时,谭天认为,企业之所以把末食做得那么难吃,就是为了逼民众花高价,买元食。因此,他总是将买回来的末食,重新回锅调味。白肉,做成卤肉。白饭,做成炒饭。厂里的仓管大姐总劝他,也别太省,元食,贵是贵了点,但,贵有贵的道理!道理,他明白。可如今这时代,贵的东西,属于有钱人,属于年轻人,属于相信自己未来会有钱的年轻人。就是不属于努力生活的人,更不属于需要努力,才能生活下去的人。
妻子怀孕后,他更是配齐了油盐酱醋,将末食变着花样做给妻子吃。可结果呢,妻子顿顿吃得很饱,却因营养不良,难产死了。从此以后,调味料在他眼里,就成了害死妻子的毒药。他至今都记得,妻子临盆前说,想吃根元食奶酪棒。他说,那是小孩子吃的东西。妻子说,可能就是孩子想吃吧。说完,就被推进手术室。而那份鼓胀的食欲,逐渐被生产的疼痛,挤压成了心脏监控器上的一道横线。
当晚,谭天就发誓,以后女儿每年生日,都要买一大袋奶酪棒,给她吃。可谭天从没做到过,元食真的太贵了,而且随着人们的抢购,越来越贵。班主任有句话,说得没错,不仅仅是学校,社会上也攀比成风——吃不起元食的,天天想着,如何吃到元食。吃得起元食的,就想着,如何吃到更贵的元食,仿佛他们不是在吃东西,而是在吃更高贵的自己。总之,为了口吃的,世界已经完全走了样。谭天就这样,被卡在了走样的世界里,无法抽身,挤得生疼。而钱,是唯一的润滑剂。
此时,手机响了。文雅一边咬着奶酪棒,一边够着脖子听。
“谭师傅吧,叉车还开吗?”是老厂的仓管大姐,“明天厂里,要来一车货。”谭天捂着话筒,连声答应,不仅满脸堆笑,还点头哈腰,在电话这头,做足了礼。谭文雅不忍再听,拔出奶酪棒,死咬下唇。咬多狠,都不疼,只觉得自己的心,像手里的奶酪棒一样,被什么怪东西啃出了牙印。
“有啥好高兴的,”谭文雅说,“机器干得比你快多了。”
“机器能干,为啥请我去!”谭天难得挺起胸膛。
“能为啥?”谭文雅横起奶酪棒,吃出刷牙的架势,“因为你便宜。”
女儿说得不错。在货不多的情况下,他确实比机器便宜。想到这儿,谭天攥紧手机,像攥着一根大号奶酪棒。谭文雅见状,岔开话题,“这奶酪棒,也没有多好吃嘛。”光秃秃的塑料棒上挤满了她的牙印。
“奶酪棒本来就不好吃。”谭天有点赌气。
“那什么才好吃?”文雅鼓着嘴问。
“营养片,食验学校的营养片。”谭天动了转学的念头。
“那是什么味道?”文雅追问。
谭天沉默了一路,也没回答。直到夜里,梦见妻子,梦见她挺着肚子,吃着末食,一个声音才在心里响起,“那大概是,公平的味道。”
3.
隔天,谭天开着叉车,边跟仓管大姐打听食验学校的情况,边在一桶桶油漆和一张张托盘码成的迷宫里穿行。仓管大姐手往哪儿指,他就往哪儿搬。车前的货叉,犹如两条铁臂,往托盘的缝隙里一戳,油漆桶就尽在掌握。货叉微抬,门架后倾,木头托盘瞬间抬起,任他调遣。
突然,厂门口一阵轰鸣,扭头一看,一辆黑色轿车,顶着油门,黑豹一般,直冲过来。谭天急打方向,转昏了头,才侥幸避开。好在托盘上的油漆桶,军心稳定,老老实实地落在了仓管大姐的指定地点。谭天定了定神,刚要骂,就见仓管大姐弓腰上前,拉开车门。一老一少,前后脚从车里下来。老的说:“以后不许开这么快,差点撞到……”他瞥了眼谭天,“叉车。”小的说:“我开得不快,是叉车开得太慢。”谭天的手,在方向盘上握了握,仿佛确定了自己就是辆叉车。
“别愣着,好好干,老领导来视察了。”仓管大姐凑过来小声提醒,“总厂的。”
“老的那个,是老领导?”谭天问完,仓管大姐点点头。
“那小的呢?”谭天盯向那个看上去才刚成年的小伙儿。
“小的是他儿子,”仓管大姐挤挤眼睛,“小领导!”
谭天咂咂嘴,领导可真是个好职业,还能继承。这时,小领导走上前,冲谭天一挥手:“你下来,我试试。”仓管大姐见老领导在后头,不做声,便拽货似的,把谭天拽下车。小领导摇头晃脑地往叉车里一坐,老领导才发话:“该怎么搬,就怎么搬,千万别客气,让他多体验体验,才知道生活的苦。”话没说完,小领导就揉着方向盘,玩儿了起来。货叉在托盘里进进出出,好似冲着一个不会还手的人,反复捅刀。也不知怎么回事,那些垒起的托盘,在谭天眼中,突然变成了自己的肋骨。
“开叉车是要考证的。”谭天闷头,盯着自己的脚尖。
“考证是为了接活儿,他又不接活儿。”仓管大姐挠挠鼻子。
“接不接活,都得考证,”谭天说着,瞟了眼暂时失宠的黑色轿车,嘟囔道,“开什么车,都得考证。”
“人和人,不一样,”仓管大姐说完,见谭天要反驳,轻声解释道,“有钱人,做什么,都是体验生活。没钱的,做什么,都是为了生活。懂吗?”
谭天还没琢磨完这话的意思,就看见小领导在货叉捅到底之前,便抬起了托盘,随即连盘带桶,翻了个底朝天。油漆桶像保龄球瓶似的,滚落一地,好几桶都砸开了口,吐出一片鲜红。谭天抬起双手,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蠢样,但眼睛却追着红油漆的流向,由远及近,一路看。看着看着,眼就花了,神就散了,最后,连脚也软了,一口气没喘上来,晕了过去。还好晕得及时,否则,他将亲眼见证,自己的右脚被砸成烂番茄的惨状。
当谭天再次睁开眼,只看到白茫茫一片。稍稍抬头,仓管大姐就皱着一张脸,送上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好消息是,手术费和住院费,老领导已经付完。坏消息是,右脚脚面,被截去大半。谭天皱起眉头,在麻醉剂的余威里,尽力分辨着两个消息的分量,没等他掂量清楚,老领导就挺着肚腩,走了进来。
“醒了?”老领导说完,冲后头一招手,小领导就提着两个礼盒,走上前。谭天盯着那精致的丝带拉花,只看了一眼,就知道,准是元食。小领导上贡似的,将礼盒搁上床头,“元食蒸蛋,补补身子。”说完,就退到了老领导身后。“有什么需求,尽管提。”老领导说着,一跺脚,肚腩跟着翻起肉浪。谭天没接话,仓管大姐倒会顺杆爬:“谭师傅,你不是想把女儿转去食验学校嘛!”老领导满意地看了仓管大姐一眼,“食验好,寄宿学校,省心!”说着,坐到床边,一脸慈祥,“但作为一所开创性的学校,名额,确实有限,想进去,不容易,”见谭天仍不接话,只好继续说道,“为什么想转去食验?为了营养片?”
谭天这才点点头。
“明白的,在当今这个环境下,做家长的,都希望孩子吃好一点。可送进去了,学费也不便宜啊。”老领导的话,比叉车还能转。“不过也巧,我手上刚好,有个名额,要是特殊家庭,还能免学费。”
“什么是特殊家庭?”谭天看到了希望。
“就是残疾人!”小领导上前一步说道,“要么孩子残疾,要么父母没有劳动能力。”
“我残疾。”谭天坐起身,争做残疾人。
“谭师傅哪里残疾了!”老领导扭头瞪了一眼,小领导立马吓退回去。这下,谭天才回过味儿来。评残疾,就得定工伤,工伤一定,就坐实了小领导的违规操作,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能残疾。
“你看,这样行不行,”老领导俯下身,粗壮的手指在惨白的被面上,来回画圈,“上回啊,有个朋友,托我把他儿子送进去,我说,不是特殊家庭不行啊,他倒想了个好办法,让儿子装哑巴。现在想想,这办法,真不错。”
“聋哑人还怎么上课?”谭天问。
“聋人多哑巴,但哑巴未必聋嘛。”老领导摸了摸自己肥大的耳垂。
“所以,我女儿,以后就不能出声了?”谭天问。
“有时候,沉默也是一种声音。”老领导掸了掸被子,似乎很满意自己的哲思。
那被迫的沉默,也是一种声音吗?谭天想完,抬头又问,“也不能一直不说话吧!”
“就装两天,”老领导搓搓手,“混过入学检查就行。”讲完,见谭天仍一脸疑虑,补充道,“就是量身高,称体重,测维生素含量。学校会通过这些数据,计算出最合适您女儿的营养配比。最后,量身定制营养片。”
谭天想了想,似是而非地点了头。
老领导顿时松了口气,嘴角扬起笑意。
谭天又说:“那工伤?”
老领导闻风而动,站起身,做好了二次战斗的准备。
“工伤,我不定了,但工伤的钱,能私下给我吗?”
“穷人总是想要更多。”小领导刚说完,就吃了老领导一耳光。谭天眼眶抽紧,直愣愣地盯向那只被纱布缠粗的右脚,“不是想要更多,是不想失去更多。”说完,他突然觉得此刻的右脚,像极了一根巨型奶酪棒。随后,叹了口气,“我是想,给女儿多买点元食。”
“理解!理解!”老领导双手合十,“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说着又恨了儿子一眼,小领导这才会意,上前一步,鞠躬致歉,九十度的弯腰,叫他重新披上了一层“小领导”的体面。这番情景,谭天还能说什么呢,只好客套两句,不用不用。老领导见状,趁势上前,与谭天握手,告别。“俩领导”前脚一走,谭天后脚就闹着出院。仓管大姐连忙将他摁下。
“钱都付了,不住白不住。”
“我得回去,女儿一个人在家。”
“我已经叫人把她接过来了。”
“那正好,跟她说说转学的事儿。”
“你还当真了!”
“领导还能讲假的?”
“领导讲的不假,但你女儿能一直装哑巴?”
“不是说,混过入学检查就行吗?”
仓管大姐看着谭天吊在床尾的那只脚,多少有点不落忍,嚅嚅嘴,交了实底。
“话是这么讲,之前,也有人托领导,办这事儿。礼送了一堆,最后也是装哑巴入学,结果呢,那孩子连一天都没忍住,第二天就被劝退。一退学,领导手上的名额,又回来了,下次还能用,礼也不用退。”
“这不公平!”谭天瞪仇人似的,瞪着自己的右脚。
“什么公平不公平的,自家孩子,开口说话,漏了陷,还能怪到领导头上吗?”仓管大姐皱着一张脸,委屈得像在讲自家的事。
4.
此时,谭文雅呼哧带喘地冲进门。一撞见吊在床尾的右脚,又像只受惊的小鹿,退了两步。仓管大姐走上前,抚了抚她的背。这只小鹿才稍稍定神。每隔一会儿,往床上瞟一眼。
“想去食验上学吗?”谭天问。
文雅咬了咬唇峰的死皮,没说话。
“去,就不能说话。”谭天抛出条件。
“为啥?”文雅撅起嘴。
“因为你是个哑巴!”
“我不是哑巴!”
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儿解释。二年级,才八岁,说懂事,有点懂事了,但八岁懂的事,是课本里的事,课本外的世界,往往是用另一套逻辑运行的。
“什么算哑巴?”谭文雅问。
“不能张口说话!”谭天说。
“那我不去了。”
“为啥?”
“不张口,怎么吃东西!”
谭天意识到女儿在逗他,笑笑说,“张口,但不能出声。”
文雅翘起下巴,赌气道,“那也不去!”但看着爸爸的脚,又不知在和谁赌气。
“你不想吃营养片吗?”谭天引诱道。
“那是什么味道?”文雅问。
谭天想了会儿,“是奶酪棒的味道!”
“真的吗?”谭文雅动了心。
“去了就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会被赶出去。”为把规矩夯实,谭天又补一句,“被赶出去,就再也没有奶酪棒吃了!”
谭文雅低着头,翻着眼,望向爸爸的右脚,“营养片,有奶酪棒那么甜吗?”
“比奶酪棒还甜。”谭天说完,就望着吊在床尾的那只大号“奶酪棒”祈祷,祈祷营养片的味道别太差。仓管大姐见状,立马帮腔,“吃过的孩子都说,那是世上最好的味道。”
谭文雅听到这句,嘴角立马漾出甜甜的笑意,像含住了奶酪棒那么甜。这份甜,叫谭天头疼,仿佛后脑勺有两根筋扭成了一股。他怀疑,是麻醉剂的药劲儿,还没彻底褪去。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无比清醒,望着眼前一脸憧憬的女儿,他模模糊糊感觉到,人这玩意儿,有时要的不是甜头,而是对甜的盼头。
5.
谭文雅入学那天,操场上积了层厚厚的雪。环境污染让这种极端天气愈发常见。即使六月飞雪,也谈不上冤。但雪积得再厚,孩子们也不玩儿,毕竟它散发着难闻的臭味。此时,一台无人铲雪车,因超时运作,屁股正冒着黑烟,收麦子似的,在操场边,来回绕圈。谁也说不清,是雪的味道大,还是车的味道大。
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走,时不时回头看一眼,身后留下的一长串脚印。越看,越觉得像她曾经留在奶酪棒上的牙印!她笑了笑,决定再也不回头了,她要一口气,跑进对面的教学楼。但跑着跑着,又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落在了后头。
此刻,她踏入的教学楼,像一座巨大的石笼。每条走廊都拉起了铁丝网。突然,一只白鸽飞来,两脚一碰到密密麻麻的铁丝,就噗的一声,挥翅,掉头,像是一只被规则击飞的羽毛球。谭文雅还没回过神,就被一条胳膊揽进了教室,抬头一看,是个年轻的女老师。
城里的老师就是漂亮,她正想着,女老师就抚着她的后背,引她入座。右手边,是个男生,头发很短,稍稍一低,就露出青亮的头皮。没有一根更长,也没有一根更短。仿佛上一秒,才修剪过,得体得不像个孩子。“我叫何里,你呢?”他眨眨眼。
谭文雅张开嘴,又闭上。这个叫何里的家伙,挑起眉毛,意味深长地一笑。女老师回到讲台,点亮智能黑板,准备上课。何里立马举手:“新同学,还没做自我介绍呢!”话音刚落,其他同学,也跟着起哄!吓得谭文雅霍地起身,膝盖窝砰一声,顶开凳子,凳脚随即在地面摩擦出刺耳的声音。同学们一阵哄笑,女老师抬手往下压了压:“新同学,有点特殊,是个聋哑人。”
“不,她听得见,老师!”何里抢话。
“对,她只是,”女老师顿了顿,“声带发育不良,导致沟通上有一些障碍。”
谭文雅使劲儿点头,像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可。曾经她说话一慢,别人就笑她结巴,但在这里,她扮演哑巴,老师也只是说她发育不良。多好听啊,不良,又不是坏,只是沟通有障碍。她从未见过这么讲理的地方。
随后,女老师便带领同学翻开课本,轻声细语地上起了课。谭文雅盯着黑板,看了会儿,也跟上了节奏。这里用的教材与县里的一模一样,可教课的内容,却完全不同。眼前的女老师会把一个小问题,无限延伸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讲明讲透。而曾经的班主任,就只是单纯地瞄准题目,进行填空式的教学,空填满了,课就完了。对比出这些不同,谭文雅多少有点得意,仿佛来到了好学校,自己也跟着聪明起来,可一想到,现在的自己,是个哑巴,没法将心得大谈特谈,又感到一阵失落。
上午的课一结束,她的胃袋,就像冬夜里冷掉的炉子一样,等着一堆柴来填。此时,又一位女老师,就走到教室门口。她的五官,比教课的女老师还精致,额前的每根刘海,都透露出一种正确的美。身后有台圆柱形的送餐机器人,她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她的脚步一停,机器人的腰间,就弹出一截抽屉。女老师随即弯腰,从中取出一粒带着泡罩包装的营养片,摆上课桌。与此同时,机器人的脑袋,又像头盔面罩似的,缓缓掀开,顶出一排一次性纸杯,供人挑选。女老师取出一只,放入抽屉,几秒后,就端出一杯清水,摆到距离营养片四指宽的位置。整个过程,在谭文雅的眼中,繁复得像是一场多余的表演,恨不得自己上前,取餐。可当机器人即将走到跟前时,她又怯了场。好在女老师先停在了何里身边。
只见他静等服务员上菜似的,将身子往后让了让,待“上餐”完毕,还文质彬彬地说了声,谢谢。谭文雅打算有样学样,可又不能开口,于是灵机一动,起身,鞠了一躬。女老师毫无反应,后排的同学倒笑出了声。
何里挑眉一笑:“不用这样,她是个机器人。”
谭文雅愣住,指了指女老师。
何里点点头:“这里除了教课的,其他都是机器人。”
受了捉弄的谭文雅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但此刻的她,已无须为说话苦恼了。
当全班同学都分配到“午餐”后,送餐机器人的脑袋上,亮起一行红色数字,11:30。随即,一段轻柔的铃声响起,同学们纷纷剥开包装,将营养片丢到杯底。下一秒,水就咕噜噜地翻滚,起泡,一杯清水顿时变成了奶白色。眼看同学们举杯,闭眼,牛饮起来,谭文雅也迫不及待,闭眼干了。刹那间,舌头边,牙床间,涌出一股浓浓的奶香,香味里透出一股浑然的甜。爸爸没骗人,真是奶酪棒的味道,不仅仅是味道,她甚至感觉到,自己正在啃一块比拳头还大的奶酪。嚼得腮帮子都酸了,也舍不得停下来。最后,还是自己的一声饱嗝,打破了这幸福的盛宴。她缓缓睁开眼,看向机器人的脑袋——11:31,居然才过了一分钟。她揉揉脸,酸胀的腮帮,竟轻松如常,刚刚那顿漫长的奶酪盛宴,似乎从未发生。
这下,她完全没了上课的心思,唇边的死皮被她咬秃了,胃口也只涨不消。直到晚餐的营养片,再次被她投入杯中,连喝带灌地冲进肚里,馋意才稍稍冷却。夜里,她闷着头,跟着同学们,往宿舍的方向走。突然,一阵风穿过走廊的铁丝网,吹凉她的脖颈,她随即扭身,从一根根铁丝的间隙里,看出去。夜空里,悬着一颗很亮很亮的星。自从她记事起,天上的星星就愈发微弱,像今晚这样的亮度,更是极其少有。
“夜空里有一颗星,你就看到了那颗星。夜空里没有星,你就看到了整片天空。”她转过头,看向同样在仰望夜空的何里,“是个谚语,老师教的。”何里说完,笑了笑,跟上了前方的大部队。谭文雅咬了咬唇峰,看来,班主任没说假话,这里的人,确实不一样。
那一夜,她舔着唇角,躺进梦乡,丝毫没有想家的念头,只觉得来对了地方。从小到大,她的嘴巴,从未被如此善待过。浓郁的奶香,持久的回甘,让她感觉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但年幼的她,不会想到,没有任何一种幸福会持久,一切美好感受,一旦重复必将回归平淡,甚至倍感厌恶。
6.
仅仅五天,她就腻了,腻得恨不能把舌头都吐出来。一天三顿,顿顿都是营养片,每一粒都是奶酪棒的味道。这么个吃法,就是和尚也受不了,她边在心里抱怨,边环顾四周,难道城里的孩子都不贪吃吗?即使每天吃同一种味道,也不会腻吗?她想问,又碍于自己是个哑巴,不能开口。
此时,何里卷起草稿本,戳了戳问前排的同学:“你早上吃的什么?”前排说:“牛排,战斧牛排,黑胡椒汁,美味极了,你呢?”何里说:“鱼子酱。”前排说:“鱼子酱,听着就吃不饱。”何里说:“吃,只是动物的动作。品尝,才是人类的行为。”
谭文雅无心去听他们的雅论,只觉得奇怪,营养片不是奶酪棒的味道吗?怎么会是牛排,怎么会是鱼子酱?难道每个人得到的营养片,根本就是不同味道。想到这儿,她偷心又起,准确来说,这回,不是偷,而是换。她准备在午餐时,故意碰掉何里桌上的草稿本,待何里弯腰去捡,她就快速调包两人的营养片。反正女老师也是机器人,根本不会在乎她做了什么。
但实际情况是,草稿本落地,何里根本无动于衷,甚至嫌脏似的,抬脚将本子踢远了些。她还不死心,表面正襟危坐,叠起胳膊,实则用叠在下方的手,一点点靠近目标。刚要得手,何里就一把掐住她的腕子。谭文雅的脸,顿时火烧火燎,可下一秒,何里又松了手:“想吃,就吃吧。”说罢,就剥开自己的营养片,投入谭文雅的杯里,气泡随即涌起。谭文雅顾不上脸面,举起杯子,一饮而尽,正当她等着享用鱼子酱的美味时,一股浓郁的奶酪味,再次糊满口腔。怎么......还是......奶酪棒的味道。她的心,竟也结巴起来。
“我的营养片,味道不错吧。”何里说完,谭文雅的胃袋就一阵翻涌,小嘴噘成一朵欲放的花。“怎么?很难吃吗?难吃得你都要开口说话了?”她赶忙捂住嘴巴,咬紧牙关,咽下干呕的欲望。什么牛排,鱼子酱,都是吹牛的,明明就是奶酪棒的味道!谭文雅意识到自己又受了捉弄,翘起下巴,想要骂人,但一想到爸爸,还是忍住了。今天是周六,下午爸爸就会来接她回家。至少今晚,她不用再忍受奶酪棒的味道了。
7.
放学时,谭天拄着双拐,站在门口。同学们井然有序地排队出门,只有谭文雅驮着书包,拨开人群,逃难似的,飞奔出来。刚到跟前,谭天就发觉,女儿瘦了。随即递上提前买好的奶酪棒,想给她一个惊喜。可文雅只看了一眼,就干呕起来,声音尖得刺耳。谭天赶忙将女儿搂进怀里,叫车回家。
一到家,谭天就指着桌上还未拆封的末食大餐,介绍起来——清蒸鲈鱼,小炒牛肉,香菇青菜,青椒土豆。他边说,边撕开包装,倒入餐盘,送进微波炉里加热。谭文雅只吃了两口,就停了筷。末食这东西,加热前,还像模像样,加热后,管他什么鸡鸭鱼肉,一入口,统统淡而无味,好似泥水。
“我要吃元食!”女儿说完,谭天才想起,家里还存着老领导送的蒸蛋呢!那可是女儿从没尝过的元食。他赶紧取出一盒,撕开包装,倒扣入碗。还没来得及加热,女儿就凑上来,扒饭似的,把稀得像水的蛋块,往嘴里划拉,吃到最后,甚至发出几声轻微的猪叫。
“下次回家,我还要吃蒸蛋。”
“不吃奶酪棒了?”
“吃腻了。”
谭天的眉心,皱起川字,一脸疑惑地望向女儿。
“去了学校,天天有的吃。”谭文雅咬着筷头,吮吸最后一点鲜美,“反正营养片都是奶酪棒的味道。”
这下,谭天的川字纹更深了,营养片竟然真是奶酪棒的味道?他搓了搓手,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可当他望着女儿瘦尖的下巴,透亮的脸颊时,眉心又松了绑。管他呢,有营养就行。随即翻着眼皮,估了下元食蒸蛋的价格,心里突然又没了底。
8.
周末一过,谭文雅梗着脖子,重返学校。一到午餐时间,便喉头发紧,胃袋反拧。她皱着眉头,把营养片丢进水杯,当气泡涌起,立马捏住鼻子,一口灌下。可刚咽一口,一股鲜美,就淌过舌头,直冲脑门——是蒸蛋的味道。刹那间,谭文雅空了表情,直愣愣地看着空气中的某一点——奶酪棒怎么变成蒸蛋了?
“味道变了,对不对?”何里问。
谭文雅瞪大双眼,望向何里。
“周末回家,吃什么好吃的了?”
她刚要开口,何里就捂住她的嘴,在耳边轻声道:“别出声。之前就有个‘哑巴’说话,被退了学。”说完,将桌上崭新的草稿本推过去,手指在封面上敲密码似的,轻点几下:“写下来。”谭文雅盯着崭新的草稿本,舍不得下手。
何里随手掀开一页:“快。”
谭文雅抿抿嘴,写下“蒸蛋”二字。
何里扫了一眼:“所以,你吃到的,是蒸蛋的味道。”
谭文雅使劲儿点头。何里笑了笑,不置可否。
此时,后排的几个同学围成一圈,聊了起来。
“你吃的什么?”
“螺蛳粉。”
“臭死了。”
“这你就不懂了。”
“我懂,闻着臭,吃着香嘛!”
“臭,之所以好吃,是因为它的味道会拐弯。因为拐弯,所以勾人。闻着臭,吃着香,就是它拐弯的过程。你想想臭豆腐,想想臭鳜鱼。”
“我还是喜欢清淡的。”
“那火锅呢?”
“那还是麻辣的好吃。”
“其实都好吃,只是各有千秋罢了。清淡的味道像绽放,麻辣的味道像爆炸,它们对味蕾来说,一个是花,一个是烟花。不分高下!”
一瞬间,谭文雅觉得周遭的所有人,都骄傲得像是同一个人。不是五官,而是五官下的神态。这种相似,叫她害怕。他们都顶着一张从没被欺负过的脸,任何小事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而作为哑巴的她,只能干巴巴看着,等待合适的时机,附和一笑,避免尴尬。是的,连笑,都要等待时机,等待是穷人的必修课。谭文雅被自己感想,吓了一跳,扭头扯过何里的草稿本,就写:“你吃的是什么?”
“和牛。”何里说。
“能不能,换着吃。”谭文雅写道。
“你吃过和牛吗?”何里说。
“没有。”谭文雅写。
“那换也没用,”何里眨眨眼,“就像上次一样。”
“为什么?”谭文雅写。
何里笑了笑:“你能想象龙肉的味道吗?不能吧,因为你没吃过。营养片,本质上是一种健康无害的致幻剂。一方面,它能满足每个人的营养所需,另一方面,它也能刺激大脑,制造出美味的体验,但这样体验是有上限的。”说完,见谭文雅一脸茫然,又继续解释:“简单来说就是,你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那营养片就是什么!”
谭文雅的字迹潦草起来:“所以我们的营养片,从来就不一样!”
何里耸耸肩,“营养片,是一样的。但我们的体验,不一样。该怎么形容呢,就像同一件衣服,胖子穿和瘦子穿,效果就是不一样。”
“这不公平!”谭文雅动了唇,没出声,但何里还是看出了大概。
“没什么不公平的,生活里的一切,都是这样。有时,大家看似获得了一样的东西,但因为各自的成长环境与生活经验的不同,最后,每个人也必然获得截然不同的体验。”
何里的表达叫她瞪大了双眼,像是婴儿头回看见电视机里的人。但她惊讶的,不仅仅是何里对于营养片的解释,更是他的这一套逻辑连贯的说辞,在何里面前,自己就算不装哑巴,也像个哑巴。她再次看向草稿本,眼前的每个字,顿时变成了乞怜的小丑。她伸手遮住,又攥起拳头,那一页,瞬间皱起,被她攥在拳心。何里见到自己崭新的草稿本被如此蹂躏,毫不在意,小声说道:“没关系的,等周末,叫你爸妈,多给你买点好吃的就行了。”
“他不会买给我的。”谭文雅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叫。何里也没继续问下去,只是轻轻点点头,随即淡淡一笑:“元食对一部分人来说,确实挺贵的。”说完,挪开谭文雅的手,将草稿本团成球,“总之,你希望它是什么味道,它就是什么味道。你吃过的好味道越多,那营养片的味道就越多,如果你只吃过一两样好吃的,那么你就只能吃到腻。”说着,做了个投篮的姿势,把草稿本丢进了后门的垃圾桶,“之前有个同学,天天吃同一种口味的泡面,学期还没结束,就跳了楼。从那之后,走廊就拉起了铁丝网。”
“跳楼?”谭文雅张口无声。
“听起来,似乎不可能。但后来老师在课上讲过,食物能让人完整,食欲能把人掏空。”何里说着,扭过头,望向走廊,“人想吃,不仅是因为饿,更是因为馋。而馋,也不仅是因为某样东西有多好吃,更多的是因为吃不着。吃不着,所以更想吃。当你知道,别人都吃的到,只有自己吃不到的时候,心就彻底乱掉了。”
谭文雅顺着何里的目光,看出去,想起了那晚的谚语。“夜空里有一颗星,你就看到了那颗星。夜空里没有星,你就看到了整片天空。”她的那颗星,就是奶酪棒,就是蒸蛋,她看不到整片天空。因为只有眼里没有星星的人,才能看到整片天空。吃东西,也是一样,只有吃过见过的人,什么美味都不放在眼里的人,才能吃到真正的好味道。
9.
何里的这番话,让谭文雅的这一周,比上一周更难熬了。因为她得到了营养片的真相,也彻底丢掉了对奶酪棒的盼头。周六夜里回到家,一看见桌上的蒸蛋,她的嘴里就泛出浓浓的鸡屎味。
“我不要吃蒸蛋!”谭文雅甩下书包。
“不是你要吃蒸蛋的吗?”谭天弯腰,拎起书包,掸了掸。
“我要吃和牛,吃鱼子酱!”说完,整个人漏气似的,蜷缩在地上。
谭天看着此刻的女儿,像是看见了当年索要奶酪棒的妻子一样,无能为力。
“凭什么别人都有的吃,就我没有。”
“谁有的吃?”
“同学就有的吃,他们天天在学校吃,这不公平!”
“胡说,食验学校,人人都吃营养片,还不公平?”
谭文雅很想像何里一样,有条有理地把关于营养片的真相,一口气说个明白。但此刻的她,连复述一遍的能力都没有。她很着急,她太着急了,急得大口喘气,急得拳头攥紧,急得攥紧的拳心,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其中穿行。急得眼睛,像口井,有亮晃晃的东西,在闪。但身为父亲的谭天却认为,是这口井,太浅,所以才会遇到一点亮,就闪。
“得到一样的东西,就叫公平吗?”
10.
女儿的这句话,叫谭天一夜没合眼。他不确定是女儿没说明白,还是自己没听明白。他甚至担心,是女儿装哑巴,装久了,连话都不会说了。他爬起身,坐在床边,看了看自己仅剩的右脚跟,踩了踩幻想中的油门,这才想起,叉车还在厂里头停着呢。
事故发生到现在,厂里一个电话也没打来过,看来大概率是不会再用他了,毕竟哪个正规的厂,敢用缺了半只脚的人,更何况他的事故,还不能放在明面上。但不管怎样,叉车总得开回来。
天一亮,他就拄起双拐,站在镜子前,照了照,左看右看,总觉得不体面,于是甩下一根,一摇一晃地出了门。刚到厂门口,就望见小领导,正开着他的叉车,在厂房前打转。仓管大姐一边看着小领导,一边对着托盘点货,稍一抬眼,就瞅见了谭天:“呦,你咋来了?”
谭天双手撑拐,半走半跳地上前:“想看看有没有活儿。”
仓管大姐伸手点了点货,没接话。
谭天望向正摆弄叉车的小领导,说:“没活儿,就把叉车开回去。”
仓管大姐看了眼谭天的拐杖,拍了拍他的肩膀:“要不,把车卖了吧。”
谭天咂咂嘴:“二手的,不值几个钱。”
仓管大姐下巴一抬:“那得看卖谁了!”说完,朝叉车的方向,挤了挤眼。
谭天一眯眼:“他要?”
仓管大姐说:“过了新鲜劲儿,可就说不好了。”
此时,叉车以一种跑车的气势,急刹在他面前:“谭师傅,这车,我会开了。”说着,一揉方向盘,得意地原地转圈。也许是老领导不在,此刻的他,像只脱缰的小兽,恨不能把叉车驾驭成战马。
仓管大姐说:“谭师傅想卖了它,你要吗?”
小领导眼都没抬:“要。”口吻像是在预订一款廉价的玩具。
谭天猛然想起女儿昨晚的话——得到一样的东西,就叫公平吗?他开叉车和小领导开叉车,是一回事吗?他似乎琢磨出一点什么,却又说不清。那种感觉像是一粒盐落在嘴里,总感觉有点什么,但刚要回味,又荡然无存。
这时,厂房前卷起一阵狂风,落脚的空地,突然变成了一台风做的滚筒洗衣机,用力地撕扯着谭天的身体。他昂起头,努力站稳仅剩的脚跟。可下一秒,就看到一颗硕大的星,明目张胆地亮在大白天里。他就这么直愣愣地看着,直到撑拐的腋窝开始发疼,才意识到——今天,应该拄两根拐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