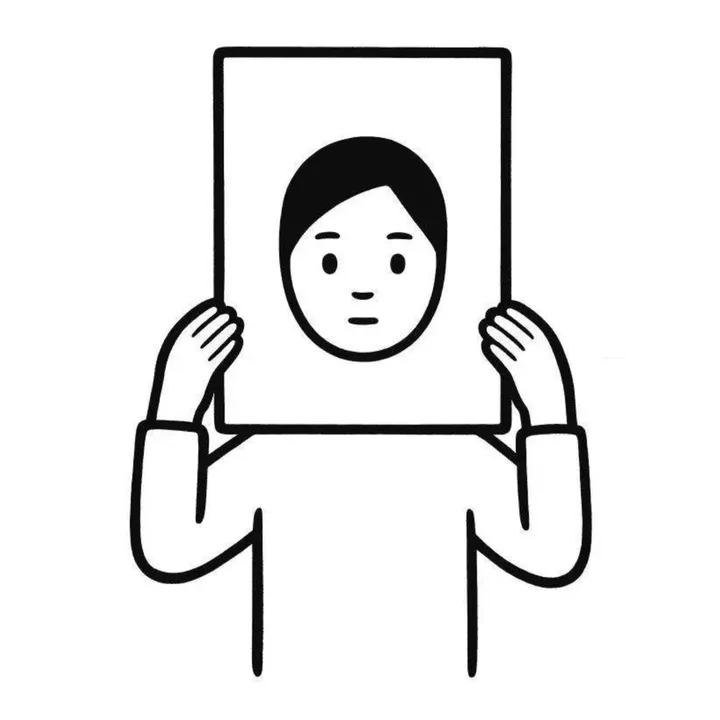莫名其妙收的礼,班里调皮的孩子,不公平的投诉,连续而不明的失眠,在迷离边缘,我加入了神秘的失眠互助小组……
1
中午接到的投诉,大概一点,校长电话把我叫醒,我急忙去了他那儿。内容我大概能够猜到,依然感觉很困,也不知道自己刚才到底睡着了没有。失眠有一个多月了,半夜总是翻来覆去,动作尽量小,怕打扰魏如清的休息。有时候能做上几个梦,但梦里总是有个吊灯,帆布灯罩,天花板有个细长身的壁虎,从一个角落爬到另一个角落,像在用身体测量面积。直到有个白天,我在墙角发现了这只丑陋的壁虎,才明白过来,夜里那些梦都是假的,我只是撑着眼皮,似扫描仪般转动眼珠。工作日的中午有一个半小时的午餐时间,我不去食堂,下课铃一响,便踱回办公室,背靠座椅,脖颈绕一圈U形枕,强迫自己闭眼,试图把夜里的睡眠补回来,论分钟算也是好的。
校长开门见山,问我是不是收礼了。办公室格外气派,宽敞明亮,大玻璃窗很是晃眼,我不常来,也跟领导没什么交道可打,容纳四十五个学生的教室,那是我的常驻地。我感觉头晕,眼里看到长条沙发,便挪过去坐下,按住扶手。我问,什么礼?红七条是入职必学的,是底层必要条件,谁也不敢在其中出什么幺蛾子。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李健生除了学习差,还参与了派出所的几场打架,因未成年不予处罚,但家长还是赔了一笔钱,他本人不知悔改,连续挑衅其他同学,因此我向上汇报并拟定了相关处分,等待审核开除学籍。这个时候冒出来一个其他部门老师,多次找我说情,并且让我回忆回忆两周前他拿到我办公室的两篮子鸡蛋和一桶油。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我继续问,什么礼?校长转了话锋,说,你最近状态好像不太好,吃午饭了吗,对面咬得死,也有人,对你很不利,不过既然我出面了,这个事儿先停一停,你不用管了。我又问,什么事?他不再作声。窗口的光暗了下去,我走到窗边,抬头往上看,一大朵阴云像辆渣土车,轰隆隆开了过来。校长说,最近有连续暴雨,跟学生提个醒。
下午上着课,雨就来了。天刹那间黑了,滚滚的雷声敲打着教室的窗。我盯着坐在最后一排的李健生,恍惚中他好像高大了,我好像在盯着一个成年人,他长出了一副金丝边的眼镜,头发变得稀少,我好像在盯着校长。恍惚被一道闪电拉回教室,我招呼靠窗的同学抓紧关窗,尽量在雷雨声中把课堂继续。
我没带伞,下班后又在办公室待了一个多小时,想等雨停。最后还是给魏如清打了电话,等她下班,顺路把我接上。这期间,我又尝试睡觉,同事都走后,我干脆躺在地上,抱起胳膊睡,硬睡,还是未果。我胡乱刷着手机,在社交媒体看失眠的各种信息,雨越下越大,最后想着那两篮子鸡蛋和油,但是记不清,什么时候,谁给的,我拿了没拿。这么下去,学生也总会看出问题,我的状态确实如校长所说越来越差,对事物的感知变钝了,脑子不如以前灵活,一道简单的几何题,我也会在黑板前愣上几秒,卡壳一般。
魏如清把车开到教学楼下,我淌了一段水坐上去。一上车,我便问她,记不记得两篮子鸡蛋和一桶油。她把雨刷开到最大,雨线被扫净重又覆盖。她说,什么鸡蛋什么油。我说,我来开吧。她驾龄不到一年,这个雨搞得路都看不见。我们在车内费劲地换好位置。我把车开出学校,路灯也亮了起来,路面都是水,我打开双闪,缓慢踩着油门。我告诉她我被投诉了,说是我收了礼,犯了红七条。魏如清说,鸡蛋和油?我继续说,有没有这个事儿?她说,我怎么知道,我也经常被投诉,打针打鼓了,配药搞错了,都是概率问题,你还当真。我点点头,说,现在不让我管了。她说,是个好事,少操心吧。我们不再说话。小轿车机盖有水漫过,我降了速,歪头看魏如清,她竟然睡着了。睡着了好,睡着了好,我自言自语。
2
压力过大,神经紧张,大脑无法放松,始终处于紧绷状态。过于焦虑,对事物过分关注,对还未发生事件的影响怀有悲观的预见性。输入手机号码,在一款APP上进行自检自查,逐条看过,觉得也无法对号入座。等魏如清睡着了,我便蹑脚起来,到客厅沙发上坐一会,打开窗户抽烟,脑子里也没什么好想的。有时候就这么不间断地抽烟,一盒烟都燃尽了,再到卫生间漱口刷牙。等回到卧室再躺下,时间才过去半个小时。漫长的黑夜如野兽般撕咬着我的全身,我能听到齿与齿的碰撞,下意识躲离翻身的魏如清,生怕这猛兽袭击她。
与她是哪年结的婚,婚后过了几年?相亲的地点在华丰大酒店,一楼大厅有十几个卡座,我与她坐下便聊,职业,薪资水平,年终奖,房与车,家庭背景,是否有奇葩亲戚坐过牢。基本信息确认好后,才开始上菜,一人一筷子夹,过去聊完了,聊未来,晋升计划,度假旅游,婚房购置,老人赡养等。观念上并无差别,一拍即合,婚期定在了相亲两个月后,性生活也和谐,互相都懂得忍让,毕恭毕敬。想来,结婚有两年了,孩子还未打算,生活和工作都顺利。失眠就这么来了。想不通,我便重新坐起身,走向客厅,围着墙边转圈。记得和魏如清去动物园,我看一只金钱豹,有吃有喝的,活鸡乱跑,它也是如此,围着玻璃笼,一圈圈转。她告诉我,那叫抑郁症。金钱豹不是在消化食物,它在消解自己的生命,一步步往死亡走。有意思,我一边转圈,一边想。
半夜的雨小了很多,客厅的窗户都打开了。手机是这个时候弹出的消息。一条邀请,号码未知。上面写,知道你没睡,知道你很久没睡,西郊水厂,等你。我看了看时间,凌晨一点半。我没认识什么外人,也没有什么私藏的秘密,手机几乎透明,这号码我不认识,怀疑是不是登录了APP的事儿。第一时间想跟魏如清解释。我看了一眼卧室,她正睡着。我继续在客厅转圈,又走了五圈后,我回卧室换了衣服,拿起手机和车钥匙,轻声关门,下了楼。
西郊水厂建于八十年代,地势低,有二十几个储水罐,但早就废弃了,储水罐都被搬走,留下了个红砖房。学校组织参观的蒙牛奶制品加工厂就在那片山上,那次参观结束等车,我往下看,对废旧建筑有莫名的好感,也想着哪天去看看。这次就算去看看,我给自己这么一个理由。
路面的水没存住,少了很多,零星的小雨用不上自动雨刷,水珠密了,就手动扫一下。梅雨季节的夜里很凉,穿着短袖感觉很冷,我连打了几个喷嚏,也许是熬夜太久,免疫力也不在线了。我编辑了一条信息发给魏如清,但又觉得天亮之前准能回去,便作罢。没多久雨就停了,一路向西开,半小时后,车子拐下一个土坡,就到了西郊。这里原来工厂密集,现在大都转型,留下空置的房屋,几乎成了流浪汉的专属场所。把车停在较远的马路边,我下来,慢慢往水厂走。这才重新对陌生号码感到奇怪,还有一丝害怕,感受不止慢了半拍,但来都来了,就索性继续往前。水厂的门还在,金属铁架在上空框了一个半圆,上面挂着仅剩的两个字牌,水和厂,前面大概还有四个或五个字,记不清叫什么了。一进去,一股腐败刺鼻的味道扑冲过来,几个坑洼都盛满了水,还有一些堆叠在砖墙边湿透了的垃圾。砖墙足够高,铁皮棚顶还在,从下面看,映着露出的光,也能瞧见上面锈迹斑斑。厂房的门被撤掉了,里面挺亮,还有一溪水缓缓流出来。和想象的废旧建筑差不多,为了确认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我狠狠踩了踩脚下的水坑,发出扑哧一声,溅出一摊水花。似乎被什么人听到了,门里面的光在说话,你来了,进来吧。
3
我领了面具,被安排到一张蓝色的塑料凳子上。大概有七八个人,和我同样戴着白色的面具,猛一看有点吓人,但也看不太清。我们呈环形围坐,中间是一盏从铁皮棚顶垂掉下来的圆盘灯,发着煞白的光,因为彼此间隔距离较远,也仅仅能照亮每个人的腿,加上面具,都足够好地保护了每个人的隐私。
你是最后一个来的,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声音也不知道是谁发出来的,面具上只有两个眼洞和鼻洞,每个人的动作几乎都一致,偶尔有几个跷着二郎腿。在我确认了最后一个是我,于是我说,我收到了短信,也确实没睡着,就来看看,我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我继续如实说,说实话,这种气氛,我并不太喜欢,虚伪和面具本身就令我作呕,秘密之下,注定还有秘密。
有人笑了起来,说,他在提议我们摘掉面具。另外的人说,不要,谁也不要坏了规矩,我们可以踢出他,这件事不是以人数取胜的。又有人说,自由,规矩也无非是自由的托盘,我是组织者,你可以叫我A,是我给你发的短信,我们每晚只给十个登录者发短信,你是这一周来的唯一一个,欢迎你。
有人说,那还不是因为没人会相信这个,尤其是在半夜里。A的声音我听出来了,他说,我们需要信任他人,也需要被他人相信,上周你不就来了。那人闭了嘴。A继续说,别在意,我们都睡不着,睡不着的人火气大,失眠,痛苦地熬夜,眼睁睁感受时间划割自己的皮肤。这里面的人也尝试了各种办法,中药,西药,按摩,甚至气功,都无济于事,因此我想到了这个,做了一款软件,召集大家,语言和故事像一根绳子,也像一条船,把我们牢牢绑住,漂浮在失眠的海,起码我们可以一起抵消黑夜的凝重,你说是吧?
我说,你是个诗人。他大笑。根据声音的方位,我判断出组织者在我的右上方,在整个圆的一点钟位置。我把这个奇怪的排列组合想成了一个圆,每个人像小时针安静地立在圆弧上。模糊中听到不知道哪里传来的切割声,摩擦声,像一把小锯子。我继续说,我没什么故事,就单纯睡不着,我也不擅长讲故事,我是一名数学老师,也是班主任,刚刚接到了12345的投诉。A接话,说,你是因为接到了12345的投诉,所以睡不着。我说,不是,我就是单纯睡不着,大概有近两个月了,等妻先睡了,我就再爬起来,在客厅转上几圈,再回去躺下,看天花板,直到天亮。有人说,你打孩子了,所以接到了投诉,打得厉害吗?住院了吗?你活该睡不着。我说,没有,不是。又有人说,那你惦记着什么,所以睡不着,是比赛吗?市里的优质课评比,我也参加了,没得奖,我们是同行,你是因为这个吗?我又说,不是,没有。又有人说,你在撒谎吗?A说,好了,明白了,我们正常进行吧,你的基本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了,你是一个睡不着的老师,接到了不公平的投诉,不爱撒谎。我打断他,说,不是不公平的投诉,电话里说我收了礼,两篮子鸡蛋和一桶油,也许鸡蛋做成了鸡蛋饼,油也拿来吃了,但是我不记得了。A说,没关系,长期失眠的症状之一就是忘事,老B还因此忘了自己的汽车停在了哪里。
老B开始说话了,听声音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嗓子有痰,估计和我一样,没少抽烟。他说,这事儿我再唠唠。上个月我开车去剧院,我是一个演员,不知名,这不重要。我把车停在门口,进去演戏,演一个疯子,因为儿子夭折而疯掉的男人,几乎是本色演出,这不是说我儿子死了,我儿子在美国上学,好好的。只是那个精神状态,很适合我,我在舞台上怒吼,口水都流进了领子里,脑子里一直在想我为什么睡不着的事儿,跟你一样,新来的,我也搞不懂。等我演完出来,打车回家,突然发现楼下停车位上没有车,那是一辆奔驰越野车,花了五十万买的,我的车丢了,但是钥匙还在裤腰上别着。我一直找,很失望,我失眠的所有原因几乎变成了这辆越野车,我至今没有找到这辆越野车。
我说,这车不是就在剧院门口吗,你自己说的。老B接着说,我怎么没想到!我明天一定要去看看。掌声响了起来。A说,我说什么来着,故事是唯一的答案,能够帮你找到车,也能帮你找到自己。我下意识跟着鼓掌,又听到什么窸窸窣窣的声音,很轻。
4
面具可以带走,上了车我才摘下,把它放在副驾驶,又拿过来藏进了驾驶座底下。凌晨三点半,天仍黑着。聚会挺有意思,后面有个女人哭哭啼啼讲了很多,她像是玻璃做的,哭声清脆极了。她男人打她,但也道歉,每次打都跟着道歉,女人总是在愤怒和接纳之间摇摆,她睡不着,一方面担心自己再次挨打,一方面又开始期待对方再一次卑躬屈膝地道歉。或大或小的身份体验,跟着那盏白炽吊灯明明灭灭的。最后A安慰了她,告诉她,接受每一次被动的锤炼,同时拥抱每一次真诚的亏欠。组织者是有风范的,说话也很动听,总在试图宽慰他人。但我理解不了,搞不懂为什么女人不离开,或许她讲的故事也是假的,仅仅是为了消耗掉黑夜的时长。但失眠是真的,她已然在崩溃的边缘了,几乎每个人都是,包括我。
天晴了两天。我上课时差点昏倒,总觉得讲台下所有的学生都变成了李健生。他胖乎乎的,平头,脸上布满了青春痘,右侧门牙隔壁有一颗金牙,每次他总是咧开嘴,露那颗金牙笑,手腕有一串粗粒佛珠,偏穿瘦腿裤,豆豆鞋。他坐在最后一排,他坐在每一排,咧嘴冲我笑,他说,他们说,你吃了我的鸡蛋,喝了我的油,你想把我怎么样,能把我怎么样?他站起来,从前排走到中间,把数学书卷成个筒状,甩到了一个女孩子的后颈,然后笑着跑回了座位。同学们吵闹着,我看着这一幕,头脑发懵,觉得虚假。窗外再次有阴云掠过,雨好像又要来了。
我向上汇报。校长室聚满了人,七嘴八舌开始说话。管理不到位。小孩子打闹,有什么要紧。女孩子也不能事先骂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看这老师很有问题。我家孩子长得壮就要担责任吗。我继续听,觉得吵。看到校长瞪我一眼,于是我退了一步,出了校长室。雨下紧了,我到教室关窗,看到女孩站到课桌上。我喊,嘿,下来。她扭头看我一眼,没有动。我先去关窗子,雨飘进来,很快就会湿了靠窗书桌的作业本。她仍然站在自己的书桌上,脚下踩着数学课本,看着窗外的雨。我说,你课间骂他了吗?女孩说,骂谁?我又问,那他为什么打你?女孩又说,需要理由才可以对吗?我不作声了。她跳下课桌,对我说,你也没办法,不是吗?说完,从桌洞里抽出了一把透明的雨伞,像扛一把剑般走出了教室。
校长又找我谈话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女孩那句你也没办法不是吗,一直在我脑子里转。白天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还没讲题,便想起了上周的那场聚会,白色的面具还在车座底下。我似乎也有了什么秘密。
我跟魏如清说了,大概有两个月没有睡过觉。她很惊讶,先是仔细看了看我的脑袋,然后翻看了我的眼底,甚至是舌苔。她说,不可能,你状态看着还可以的,要不明天请个假跟我去医院抽个血。她怪我这么久了才跟她说,又觉得我好像在逗她玩。我们躺在床上,开着灯,我看见那只丑陋的壁虎又爬了出来,顺着灯线,迅速躲进了灯罩里。我说,没什么,也可能我睡着了,感觉和没睡着一样。魏如清说,你别说,还真有这样的神经官能症,总觉得自己在醒着,拿24小时监控一录,就能看出来,其实早迷糊着了,打呼噜的时间也真不少。再说,你有什么烦心事,朝九晚五的。我说,说到底也跟我没关系,班里那个坏孩子又打人了,我也没什么办法。魏如清说,不是校长管这个事了吗?我说,因为鸡蛋和油吧。她又问,什么鸡蛋和油?我说,没什么,对了,你觉得失眠的人多吗?魏如清说,我睡眠挺好的,天天累得要死,你想表达什么?我说,有人因为失眠聚到一块,聊聊天,你觉得会管用吗?魏如清问,收费吗?别弄那玩意。我说,嗯,不弄。
5
我数清了,一共八个人。
A说,今晚要下暴雨,你们来得都很准时,上次我们聊得很快乐,尽管有人哭了,但回去一定也睡了个好觉,对不对?女人回答,没有,回去也没睡着。大家一起笑。我也跟着笑。我说,老B车找到了对吗?老B咳嗽了几声,说,没有,还是丢着,找不到。我纳闷,接着说,剧院门口不是吗?老B说,是,但是不能找到,你明白吧?老A插话说,我们都懂,寻找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灯线目测有三米长,从房梁上垂下来,灯盘在晃,今晚有风,从破漏的窗洞和正门吹进来的。光圈跟着一起晃,从我们六个人身上依次切过,我们确实像在海上,随海浪起伏,摇曳着。
我又听到吱吱的声音,像老鼠又不像,金属质感,有些刺耳。又有一位女性说话了。她说,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不想睡觉,但有时候会困,每天晚上都喝很多杯咖啡,强迫自己不能入睡。睡眠对我来说,是很恐怖的,我不知道你们做不做梦,我讨厌梦,梦是难以逃脱的。A说,梦是假的,是休息的一种。她继续说,我不喜欢,做梦醒来会感觉恶心,我需要真实,有时候也很抗拒这个面具。老B说,关于面具的问题,新朋友来的时候我们讨论过了。她又说,好,我听你们的,请让我保持清醒。
我说,下雨了。正门有雨飞进来,窗洞里也是,灯闪了几下,灭掉了,几秒后重又亮起。有人开始骚动,从塑料凳子上站起来,随即凳子被风吹出去半米。A说,在凳子上坐好。我们都照做,看来暴雨要来了。我说,你们让我感受到了秘密。A说,接着往下说。我说,我把面具藏在了车座底下,车一直是妻在开,她没有发现,我本来想跟她说说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疯子。老B说,你答对了。有人问,那你说了吗?我说,没有,我没有告诉她,我在参加,这个叫什么,我们这个?A说,失眠症候群组,就叫这个吧,自救与他救,或者单纯像那位女士一样,试图摆脱枯燥的日常,时刻保持清醒。我说,清醒也没那么容易,不是吗?我又接到了投诉。大家笑起来,我也跟着笑。我说,失眠的好处还是有的,培养了巨大的钝感,对一切丧失反应能力。A说,为新朋友鼓掌。于是,大家鼓掌,我也照做。
雨水开始积成小河,从大门流进来。我的皮鞋底浸在水里,袜子也湿了,脚趾感觉到了冷。人们还在聊。我抬起了双脚,踩在凳子稍高的横条上。A说,睡不着也许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特殊的权利,可以让我们活得久一点,共同反刍痛苦,兴许可以咀嚼出点甜味。有人说,我不在乎什么甜味,生活本身就是巨大的苦楚。又有人说,你的悲观令人可怜。我说,水进来了。
暴雨如注,倾泻在铁棚顶上,发出巨大的响声,像颗颗石头砸了下来。涌进厂房的水已经及脚踝处,有人盘腿在塑料凳子上。我又听到那金属摩擦声,丝丝微微地响着。有人说,看来我们这艘船要翻了。众人又笑了。直到有人停在外面的汽车开始发出呜呜的报警声,人们才开始真的慌乱起来。有人撂下凳子,挽起裤腿就往外跑,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说句再见。我也站在水里,水深已经到了膝盖。
6
我一把扯掉面具,赶紧往外走。西郊水厂地势太低,水积得极快,附近的排水系统也被垃圾堆满,完全不起作用。很快,人们都踱到了马路对面,我也庆幸自己把车依旧停在了远点的高处。站在大门口,还是听到了摩擦声,我回头看厂房。有个女人还在塑料凳子上坐着,因水流移位,女人就在吊灯的正下方,一袭白裙,在水里泡了一半。我掉头回去。水已经到我的大腿,我一步步艰难地淌过去。
她抬头看我,两只眼睛从面具的窟窿里闪着光。我说,你是个学生?她没有回答,双手垂在涨起来的水里。显然穿着大号的裙子,胳臂和身子都细长,坐在凳子上像折断的筷子。我说,你怎么还不走,看不见这水涨得有多快吗!我拉住她的手腕。她的手这才从水里探出来。手里握着一把美工刀。我下意识松开。她又伸出另一只手,给我看她的胳膊。她说,怎么样,漂亮吗?吊灯在头顶又开始摇晃,打圈。光像是在交叉。我看到她的小臂上有一朵花,但看不清,我掏出手机,打开闪光灯,照着看,上面暗红色和鲜红色的花瓣交叠着,有血滴进了水里。我灭了灯,说,你疯了吗,你多大?她说,我的磨刀石丢了,我就在地上蹭,越锋利,刻出来的花越好看,你不觉得吗?吊灯闪烁着,彻底灭掉了。外面应该是跳闸了,水已经涨到了腰,塑料凳子开始一个个漂浮起来。一片漆黑,只能勉强从厂房门口瞥见对面还在亮着微光的路灯。她说,这下才像在海上。她指着那些塑料凳子说,那是一个个集装箱,它们从船上意外掉落下来,船是不会回来打捞它们的,它们永远被遗弃了。她站在水里,白色裙子在水里展开像上浮的水母。我拽起她的手往外走,她甩开。黑暗中我又上前去拽她的面具。她拿起美工刀对着我,刀面反着室外的微光,她的身子已经开始在水里摇晃。她说,别靠近我。我说,我不是坏人,我是一个数学老师,在县中教书,坐公交车118路,终点站,你就可以找到我,我们得出去。她说,我知道你是谁,你们没什么区别,我在无数个夜晚都看得到你们,你们伤害了我,还用道德的裹尸布给自己开脱,一群疯子,我嘲笑你们的聚会,嘲笑你们所有人的秘密。懦夫,胆小鬼,可怜虫。我觉得她说得很对,也不知道怎么反驳。看着她歇斯底里的模样,又有点羡慕。我说,我不想知道你到底发生过什么,眼下,我们得出去。她重又戴紧了面具,说,你不认识我,也没必要认识我,我的经历对你来说毫无意义,我仍在海上,永远在海上。
双脚离地,我浮起来。暴雨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厂房成了巨大的游泳池,我摆动双臂,才能保持胸部露出水面。水同样也是漆黑的,凝滞的果冻状,包裹着我和她。棚顶开始松散,发出咯吱的声响。我抬头看,铁皮已经开始向两侧倾斜,露出巨大的窟窿。雨从那里钻进来,像一颗颗子弹射到我的脸上,射进水里。我抹了把脸,看到女孩真的如白色水母,向后游走,我抓不到她。她回头,好像在说,你看,你也没办法不是吗?
水已经到达脖颈,我向厂房出口游去,憋了口气,潜进水里。
7
暴雨连续下了两天。课全停了,整个县城泡在水里。魏如清当晚值夜班,被困在了医院。她在电话里和我抱怨,地库的车准也淹了,说早知道买条船。我说,船也会翻。她说,这个时候你别贫嘴了。我们等着雨停。一天后,雨渐弱,但水位还是很高,消防已经坐着汽艇救人了,有的狗上了屋顶,树杈上能看到猫。我把失眠小组聚会的事电话里给魏如清说了。她表示很诧异,我是如何在她睡着了以后,偷偷溜出去的,还认识了这些奇怪的人。我表示忏悔,秘密没什么意思,悲欢也并不相通。我又强调了一遍,我确实睡不着觉,感觉身子轻飘飘的,没有支点,那些人也许一样,理由总要有的,编一个,也总要有的,大家吵吵闹闹的,漫长的黑夜才变得可视起来。她这回当真了,说水退了就带我去看病,失眠也是可以治疗的,她们医院还有一套针灸疗法,也许关键还是心病,是我不够在乎你吗?我听着笑了,连忙回没有,我们很好,各方面都很好。魏如清说,听着不像很好,没想到你亚健康了这么久。我附和着,挂了电话。亚健康这个名词瞬间跳进脑子里,我也许很早就已经是个病人了。
水完全退了,小区楼下涌出一堆泥沙。公共交通还没开,我只能步行,后来用跑的。等我赶到西郊水厂,却找不到西郊水厂。那一片仍旧在水里,像一片存在了多年的湖。湖面上漂浮着杂七杂八的垃圾,我分辨出几个塑料凳子,像是那天我们坐过的。水面异常平静,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相信,女孩在我之后也游了出去,水母不会溺死自己的。为了求证,我联系了A,想和他要一下女孩的联系方式。A说,你忘了,我们都戴着面具,我们谁也不认识谁,包括你,包括我,我们也不认识,你的电话也许打错了,同志,你再看看。我挂了电话,失眠像一场梦游,聚会也形同虚设,我点点头。
复课后,李健生最后一个到校,把书包甩过头顶,似直升机的螺旋桨,闯进教室,走到最后一排。我停下粉笔,站在讲台看他。他把书包扔在课桌上,一脚踩着凳子看我。我放下课本。其他同学好像都屏住了呼吸,教室一片阒寂,大概过了五分钟,他把脚从凳子上放下来,这才坐下。我继续讲课。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和一条竖线,又一条竖线,又一条竖线。围坐的失眠的人,和密集的雨线,涨满的水,水里的船,麻绳,人,嬉笑,讽刺,哭闹。你干吗!我回头,有女学生站起来喊。李健生搬起凳子挪到一个女孩的身后拽起了她的辫子。我走上前去,他立刻也站起来,挺着肚子看我。我拽住他的胳膊,狠狠地使劲。他大喊,哎哟我去,老师打人了,老师打人了。其他学生都站起来闪开。我想我不会再放手了,我继续使劲,捏住他的腕骨,哪怕暴雨再来,水涨得再高,我都不会放手。李健生的另一只手上前掐住我的脖子,我咳嗽了几声,仍旧拽住他的手腕。我们就这么僵持着,直到他疼得哭起来,同学们都笑了。我跟着笑起来,看到穿着白裙子的女孩站在最后一排,不知道是谁,不知道是哪个班级的,一起跟着笑起来。
毫无意外,我又被投诉了,学校停了我的课。魏如清说,无所谓,正好带你去看看。我们拿了一堆药,她买了口砂锅,一下班就开始熬。她说,失眠不是病,人也不用睡那么久,记得哪里说,名人一晚上才睡三个小时,对不对,不要有压力。我说,我没压力。她说,那你打人家小孩。我想了想说,总归是有办法的。她说,对,总归是有办法的。
晚上喝了药,躺在床上。还是魏如清先睡着的。我闭着眼,不知道闭了多久,起来,去客厅转圈。三五圈后,窗外又开始下雨,但不大,打开窗,空气泛凉。手机又响起来。我打开看,上面写,我知道你没睡着,玻璃厂,等你。我删掉短信,回去床上。魏如清打起轻鼾。我想起那天的鸡蛋和油,它们就一直放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无人认领,窗帘及地,它们就在那背后,一直躲躲掩掩。也许那就是我所有失眠的起点,也是我失眠的终点,有些事尽管我处理不了,关于课堂里的愤怒和校长室大义凛然的言谈。但我起码还是个数学老师,最擅长的就是数数,我闭上眼,努力回忆被风吹掀起来的窗帘一角,后面的篮子有盆子那么大,摆在里面的鸡蛋一共有: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六颗…
水母奋力向上游着,海底也能看到光,在水面上闪烁着。手臂上的花是自然生长雕刻,向阳盛开的。人们夜里聚在一起,按顺时针发言,失眠只是借口,秘密越垒越高,需要额外的无穷的黑夜,一层层将其覆茧,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