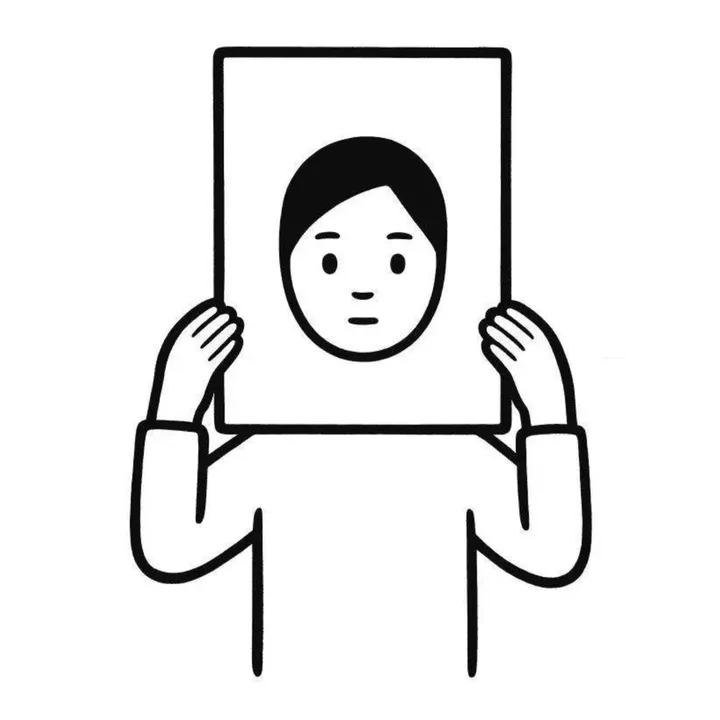一场分不清蓄意还是意外的海难,一帮各自“自私”的人,或许这是如今社会的一种微观。
杰克与罗丝
船是昨天傍晚离的港口,说是港,其实就是一处木栈,一条麻绳拴在栈桩上,另一头系着船头。船也是木头的,标准大小,长三米,宽一米半,两人坐船头船尾,中间隔板还能当个茶几。当然他们不是在谁的客厅喝茶的,出来没带什么东西,他只有一个背包,她连个背包都没有,手机攒着一个不透明的玻璃瓶子,似乎是毫无打算。算私奔吗?她有点冷,男人把外套脱下来给她披上后她问。他说,别这么俗,那两字我不喜欢。她点点头,又问,算失踪吗?男人看了看手机,后半夜的海面颇为平静,如果没有月亮从他们背面的太阳那儿借来的这丁点的光,他们确实都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在哪儿。木船没有一丝一毫的晃动。这让女人想起了一幅画。远处月亮巨大地沉在海面的那条直线上,一半上一半下,她觉得那像个细细的锯,画面的波动是画家想象后的执笔,她觉得月亮早晚被割断,一半像气球一样飞上天,一半如巨石沉入凝黑的海底。海面是没有颜色的,画也是骗人的,只是为了营造意境而营造意境。
此刻对面的男人正在掏包,随后摆在所谓的茶几上的是这么几样东西:一包桃李面包,一盒煊赫门,一包洽洽瓜子,炫迈橙子味口香糖,清风纸巾,一把瑞士六合一军刀,一副蓝牙耳机和一包未拆封的杜蕾斯避孕套。看上去是准备了,又像即兴。她伸手随意挑选,手指摁在避孕套上,说,你认真的?男人说,我想会用得上。女人笑着站起来,外套从肩头滑落,男人俯身去捡。女人突觉骤冷,抱起胳膊,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答应他。男人看起来很蠢,不值得托付。木船是上周二他们发现的,偏僻的海边过于萧瑟,浅滩没有开发,也无人打理,堆满浪冲来的垃圾,她仔细数过,像她那一堆糟心的生活。发现后,她说,你出过海吗?男人一愣,用什么出海。她指指这艘船,用这个。男人说,浅滩的垃圾有的会往回漂,再回到海里,这,就是工人用来捞垃圾的。女人说,我知道,我想把自己放走。男人把外套又给女人披上,这一点是让她一直暖心的,也大概是这一点,她觉得和他在一艘船上,并没有太难接受。他说,我想好了,也查过了,我们顺着海,会一直漂,大概明天中午,会漂到那座岛上。女人顺着他的手指看,确实有一处更黑的黑。她说,去那儿干什么?男人说,不是去那儿吗?漫无目的去那儿,不做打算去那儿,假装流浪,那里也有渡船和铁索,我查了。她说,我没有假装。男人不明白。她继续说,我想要一个海难,突如其来那种,一下掀翻我们的船,你跳进海里,费力抽出那块木板,把我捞在上面,还拉着我的手。男人说,怎么这么熟悉。她说,我叫你的名字,杰克,你要永远爱我,好吗?男人说,杰克是谁?女人看到了远处的灯塔。上面一束强光打了过来,在海面上留下一处不大不小正好圈住他们的圆形光斑。他们被发现了,灯塔上亮起三长两短的另一束射光,他们听到游艇的声音,嘟嘟嘟,从远处来了一艘白白的船,马上就近了。男人开始敛起隔板上的东西。女人说,最后杰克死在了海里,冻成了冰,永远在漂,罗丝趴在木板上,苟活着,她背叛了爱,背叛了一场灾难的神圣和不可抵抗。男人收好背包,开始向游艇挥手,随即听到一声扑通,他看到船身一侧的水花,还没有意识到,那将会是他这一辈子看到过的最浪漫的水花。
快艇
魏明磊一个人在塔顶值班,却摆了两把椅子,中间台子上是一副象棋,他从抖音上看来的死局,一人分饰两角,一会儿这边坐一会儿对面坐,研究互相破局。一耗一个晚上,天亮下班,往往下班前也研究不出答案,也不乐意看谜题的最终解,耗本身就是一种能量,博弈状态下的魏明磊是清醒的,他需要清醒,时不时从窗口摆弄一下探照灯,抓着两侧把手,横射整个海面。这片区域静得出奇,是陆地的拐口,往往漂来的都是南面的一些垃圾,有时候需要夜里判断一下,大部分时候不用管,垃圾落到岸上,每个月都有人处理。他不喜欢搞那些,坐条小船,沿平静的海岸线溜上半圈,捞捞矿泉水瓶,船摇得他心慌。这里清静得多,就是只有夜班,射灯的作用也只是防止有船触礁搁浅,大型货轮他见过几艘,没几个会犯傻,海上导航他也见过,这里就是导航的禁区,象棋玩累了,海上寻宝,那束光柱就是另外的乐趣。魏明磊幻想过,光圈里出现的一切不可能。座头鲸,巨型乌贼,水怪和海底生长出的类亚特兰蒂斯文明。
木船的出现,他完全没有料到。象棋的死局意外破解,像某种征兆,魏明磊站起来抱住探照灯直射大海,光圈掠过一条极小的线段,初判是块浮木,光打回来,他发现线段上方两个圆点,一高一矮,像是一站一坐。光圈锁住,聚焦。平静的海面像手机屏幕的截图,中心是一艘木船,和两个人。他们手里没有任何工具,就杵在那里。魏明磊心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是遇难。他以前当过兵,在南海,跟一艘小军舰,甲板上待了半年,又调回陆上,海上的事儿他算是门清,一艘这样的木船,不出意外,天亮前决定命运,顺着看着平静的洋流,渡过拐口,直接入深海,没有十天半个月看不到任何地平线。他年轻时在中央六台看过一个纪录片,科学家带着十几个人坐木筏漂大西洋,充足的食物和水,三个月才到岸。他不觉得那艘小木船能藏下多少食物,他眯起眼继续望,笃定他们是意外漂荡于此,也应该庆幸能偶然间被这束魏明磊的光刺到。自我感动之际,他拿出另一部手电,向远处发出三长两短的光信号,对方没有任何反应,魏明磊迅速攀下铁梯,拿起一层墙上挂的钥匙,那是一艘早就成为应急管理预案摆设一部分的快艇,跳上它时他仍旧在怀疑这是否还能够正常启动,也将远处未知的命运与这艘快艇挂了钩,如果钥匙插进去,拧上半圈,船尾的发动机冒出声响,他将义无反顾冲去那束光锁死的圆圈,否则,他将会重新回到塔顶,再摆上一副死局,使探照灯挪位,木船于是再次隐入光的边缘,被黑暗拽走。魏明磊穿上橙色的救生衣,轰隆一声巨响,船尾的海面被割开,波浪像座朝两侧倾倒的小山。快艇在加速,他一手扶着船舷,一手紧握发动机的摇杆,越向后拨,船越像一枚炮弹,他的脸上已经被飞溅的浪花打湿,额头的发丝迅速结了绺。
速度正向光冲刺,在魏明磊的脑子里,二人正要被海怪吞噬,一切能想到的词汇均已过了一遍,迫在眉睫,千钧一发,近在咫尺,危难之中,刻不容缓,求救,呐喊,无助,绝望,等等,焦躁的他像是摸寻到死局的唯一解。他从救生衣里掏出金属铜镀的口哨,大力吹了起来,海浪似乎盖过了哨声,但在他心里,正好相反。
死亡
女人是什么时候捞起来的,张建德站在浅滩问,脚下还有个雪碧的绿色塑料瓶子,他用皮鞋踩着,前后搓动,没一会儿,塑料瓶就卡进了湿润的沙子里。没等回答,他看了看手表,凌晨三点十五,梦里有一辆车,大型SUV,副驾驶坐着他的妻子,喋喋不休,不知疲倦地说,内容他记不清,方向盘不在自己手里,可他坐在驾驶室,奇怪地透过前挡玻璃往外看,外面是起风了的海面,他行驶在海中,他扎进海里,他打开雨刮器,海蟹与鱼从玻璃一层层划过,又一层层重新覆盖。女人躺在沙滩上,肚子鼓得肿胀,喝了太多海水。张建德怀疑人工呼吸是否做过,意义不大,但他还是蹲下,探了探鼻息。又试着按压了一下女人的胸腔,有流水从嘴角溢出。像睡着了,张建德自言自语。但确实死了,他见过太多,推测时间不出两个小时,两个男人站在他对面,都穿着救生衣,女人没有,女人只有一件单薄的毛衣,下身藏蓝色牛仔裤,裤腰的扣带被胀大的肚皮挤掉,看上去像隔夜死的。实在太能喝了,他得出判断。直到这一系列的猜测停下,他才又问了一遍,什么时候捞的?他看向魏明磊。魏明磊这才说话,也是吓得不轻,手在打哆嗦,他没有如此接近过尸体,况且是返回去重新捞的。快艇到时,只有男人一个站在木船里。他还纳闷明明看到两个人头。男人上前握手,并没有再多说任何情况,意外走入困境,仅此而已,于是从木船踩进快艇。魏明磊掉头转回灯塔,见男人老是回头,光圈是死的,木船已经漂走,不知道他看向哪里,再问。魏明磊掌掴自己。索性再次掉头,强光手电照射一圈,女人的辫子浮出水面,发箍缓慢松散,头发如液体般融扩,遮了小范围的海。捞上来时,快艇停浮,魏明磊将其平放,快速按压胸腔,让男人对其吹气。男人摸索背包,半天不上前来。魏明磊自己操作了十几分钟,女人的面庞娇嫩,偏白,一次次地贴近嘴巴,牙齿磕在嘴唇上,他脑子里已然是女人的脸忽大忽小,忽近忽远的喋喋重复。他站直身子,回答张建德,大概一个半小时前,我打电话报的警,抢救了也有二十分钟吧。张建德把执法仪按开,挤了挤左眼,还有点迷糊,说,怎么没的?你看见了吗?谁认识她?魏明磊搓了搓手,把救生衣卸下来,扔回搁浅的快艇。男人提紧背包,身上救生衣的水还在往下滴,一下下落在沙滩上,砸出一个个凹坑,他听得格外分明,瑟缩起来。
光来自快艇前端的一盏小灯,只能打出横着的一道,照在男人的大腿和张建德错开的膝盖上。张建德一米八五,人高,粗壮,视觉对比,男人矮小,像做错事的孩子般蜷缩着。张建德不耐烦地吼了声,你赶紧说说,死人了知道吧,不交代?男人终于开口,说,她跳进去的,从船上,往下跳,没跟我打招呼。这几个字也是有间隔的,男人唯唯诺诺,好像一下子小了三十几岁。张建德继续问,往哪跳?男人说,海,海里捞的。张建德把执法仪从胸袋取下来,对准男人的脸,再问,你们什么关系?男人答不上来。起了雾,也就一阵儿风的事,张建德眯起眼越过男人头顶往后看,白雾蒙蒙,像凭空降下的云,猛地盖在海上。魏明磊重又走来,站定后像个背景,盯着两人。张建德看他,又看男人,又看他,说,还有你什么事吗?魏明磊说,120也是我打的,还没来。张建德知道他是守塔人,两人半年前打过照面,海上捞出了一枚鱼雷,魏明磊退伍前见过军用的,第一时间汇报,用木排车拉进了派出所。当时张建德就挺看不惯这人,总琢磨着这枚仍旧光滑锃亮的鱼雷会突然爆炸,整个派出所两层将被夷为平地。他回头看看堤坝,车顶的红蓝灯交错,按理说出警必须两人,搭伙的没来,这块地儿没有什么事是真的需要两人及以上警力处理的。他现在依然坚信这一点,没必要再问两句,他还要回去继续睡,把先前的梦续上。尸体先交给急救车,担架和裹尸袋他们也都有,纠结什么关系干什么,张建德不再发问。
罗丝
她重温这部电影时他在酣睡,酒店的床头射灯坏了一枚,只剩了一枚,她在全屋唯一的光下蜷起双腿,平板立在膝盖上,保护壳卡通,戴着粉色硅胶兔耳,是他女儿的。但不是她女儿。她执意要男人把女儿的平板带出来,她在一次两人视频中偶然看到,想把它据为己有,男人说你想要我可以给你买,但最终还是带了出来。她也不会真的要走,像是入侵他生活的一次证明,平板拿在手里,想象自己是他的女儿,是他的什么都行,只要是他的。她用爱奇艺看泰坦尼克号,船沉下去时,声音从画面里出来,罗丝,罗丝。甲板倾斜,海是黑色的爪子,攀住所有的铁皮,人极其渺小,船舱入水,数万人喝下了数万吨水,她感觉自己也隔着屏幕喝下了巨量的水,咽喉处疼痛,似有铁球膨胀卡在其中。罗丝,她就是罗丝。她侧头看着一旁的男人,杰克,那是她要的杰克。一个微微打着鼾声,有着两个固定女性的男人,加上她,就是三个固定的女性,男人的欲望终归是无限延展的,她想笑,但船彻底沉了。她把一条紧挨他的腿伸平,脚背勾住被子里的他的小腿。杰克,她说。救我,她说。
他们每周都会在学校见面,但约会并不频繁,一个月最多一次,有时候过夜,有时候不过。罗丝没有什么太大的需求,男人将近四十,却格外温柔,有时候也像个孩子。她不知道孩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她不喜欢孩子,那种没有看过世界的幼稚让她反胃。男人更多时候像个父亲,她觉得她渴望的是一个父亲,他从海上回来时会带一些贝壳,颜色各异,形状不一,说是哪个海滩专门捡的,后来才知道是小义务批发市场成麻袋购买的,倒出藏于船舱内床下的一方木箱里,专门为了哄她的,聪明的父亲,那些贝壳就像那块带着兔耳的平板。父亲与船一同失踪时,她才六岁,总觉得他能回来,又总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过什么父亲。男人那天走上讲台时,她盯着他看,觉得他凌乱的头发和碎破的胡茬可能是种巧合,或者天意,她全然接受,只管让血液里某种奇怪的东西流动下去,直到他爬上她的身体,进入,倾泻。她仍旧孤独,被道德感深深绑架,好似自己被父亲压在身下,喘息声格外遥远,突破大气层,坠入黑洞。她推开他时在哭,汗液湿透了彼此,那时她已经感觉像在溺水,但还并未知晓自己就是罗丝,船仍旧在航行,汽笛声划破黑色的夜空。男人紧紧抱住她,说了永远两个字。她脑子里是漆黑而平静的海面,父亲单手攀在桅杆,另一只手举起长筒望远镜看向远处,多笨的父亲,远处除了黑,什么也没有,她感觉不是海在流动,是船在流动,是自己在流动。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钻入,她清楚地看到男人裸露的后背上,靠近脖颈儿的位置,有一左一右两颗黑痣。她用指甲去扣,直到笑出声来。
心肺复苏
人工呼吸当场就做,两个急救人员一左一右,很是专业。女人起伏的胸口落满沙子,是海雾里卷来的,细腻,绵软,他们都尝到了。男人也脱下了救生衣,跪在一旁,背包置在沙子上。他伸出手去,握住她的手,那手已经微微僵硬,冰冷,不像是再能够有血液穿过。张建德背身过去掏烟,魏明磊也小步过来,两人走出几米远,围手圈,点火。张建德说,有你,准没好事。魏明磊接过烟,吸了两口,说,鱼雷那事,还惦记呢。张建德白他一眼,说,你就真不怕它爆炸,往派出所大厅一撂,得亏认识你,要不谁知道你是不是来炸所的。张建德真见识过,一个老头用破布裹着一长条杆子,进所里就晾出来两把猎枪,吓得他往台后一蹲,右手已经扶住了腰间的枪托。也好歹是有躲和还的机会,不像鱼雷。魏明磊说,这回你怎么看?张建德咳了几声,说,什么怎么看?殉情自杀,一人得逞一人未遂。魏明磊又问,不再查查了?张建德想起了自己还没做完的梦,车子从大海中飞起来,海生动物从两侧门板掉落,他侧头看,妻子变成了巨型乌贼,正用触手绑住自己,操作方向盘。他浑身一冷,说,你有高见?
魏明磊说,男人胆怯,做了亏心事,约女人上船,借顺势海流,漂至远处,夜里推其下水,如果我没有发现,也许就没人发现了。张建德不太认可,又问如果真没发现会如何。魏明磊说,两人不管谁推谁,最后都得死在海上,不可能出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张建德吐口烟,摆摆头,说,还真是那么回事,就是说,这场海难只发生了一半,你的参与是救了一个也害了一个。魏明磊说,这什么意思?张建德说,你看,你快艇赶到,接一个捞一个,一死一活,如果你当没看见,你可以当他们死了,但也可以当他们活着,正拉着手在船上赏月,这事,本跟你我都没关,我正做着梦呢,他妈的。魏明磊不吱声,又开口道,我看见了就是看见了,假装不了,话我说到这里,事实我看不透彻,只是好奇,定夺还得你们。张建德点点头,说,热心市民。魏明磊转身往回走,路过心肺复苏时停下看了几秒,才俯下身子推船,快艇重新入水,他跳上去,再次穿好救生衣,往海的黎明开去。
晨曦被雾阻隔,落在救护车上的光斑零零散散。后门左右对敞着,四个轮子陷在沙里,在等女人安稳上车。张建德看天,晨雾不浓不薄,觉是睡不了了,太阳再高,雾就会散,又扭头看救护车,里面仪器齐全,氧气瓶,输液器,电子监护仪,除颤器。为什么不用除颤器呢,他看着两人忙活,额头出了汗,实在够卖力的。再点支烟,听救护人员问跪着的男人,还救吗?肋骨都快压断了。男人松开握着女人的手,手背捋了捋女人的一侧鬓角,心想,压断了和死掉了,哪个更接近,哪个更真实。他推开救护的两人,自己上手,掌心叠掌心,放在胸口猛压。还是有水,女人像是把大海都吸了进去,在这个黑夜是无法清空的,紧接着的白昼和下一个黑夜,他想试试。急救人员站起身,拍了拍腿上的沙粒,站在一旁等,注意到张建德,于是走了过去。张建德给两人递了根烟,他们一高一矮,都接了过来,分别抹去额头的汗,聊起天。
张建德问,一晚上几趟了?高个说,一个喝多的,车祸,把树撞断了,人也是当场没的。矮个说,倒不像这么麻烦,身子碎得彻底,你来干啥?刑事案件?张建德看着眼前这一幕,男人手掌不停地按压女人的身子,越加卖力,近乎歇斯底里,竟生出了一丝恐惧。他说,那个灯塔的,打了报警电话。两人哦了一声。张建德接上另一句,自杀,男的没拦住,也不会水,看着淹死的。
杰克
他不会水,从小都不会。学生时代最避讳游泳,也不是怕,就是学不会,显得尴尬。单位组织教职工游泳比赛,他请了假,别人问,他说,如果不是发了低烧,他准能在游泳馆里拿第一名。骗子。从来都是,只会吹牛,反正没有任何可以求证的机会。女儿小学三年级,游泳课,他站在池子边上看,女老师,穿着连体游衣,像条泥鳅,从水中滑上滑下。要不是那名女老师,他也不会去陪着,对水有些恐惧。
海边的船是她先看见的,他开始以为是块废木板,更不会想到她还要坐上漂出去,漂哪去?漫无目的,他一点也不喜欢,自己和她不一样,年龄差了将近二十岁,思维模式也不一样,他不太喜欢冒险,总是按部就班,但贪财好色,算是个俗人,头脑一昏,当即也就答应了。据他网上搜索来的信息,海岸线有股冷暖流的交界,不到十公里,会到乳峰山。那是一座刚开发的小岛,山像卧姿的美女,两座山峰像乳房,图他看了,觉得更像坐下身子的骆驼,但叫驼峰山,不够吸引人,他懂里面的套路。景区有完备的设施,轮渡与铁索都有,选择如何回程也都不麻烦。不过没跟她讲过,算是精心为她打造一场漂流式的流浪,玩玩而已,这是他想的,也好像是他历来的初衷。女人掉入海里时,他脑子一下就蒙了,被快艇的光射得晃眼,再回过神瞧船沿的海水,女人好像身上坠着石头,一下往深处落,水花合拢后,大海恢复如初。他连惊讶都没喊一下,连女人的名字都没有叫出声。魏明磊招呼他上来时,他真想就这么走了,就当自己完全没来过。他对她到底有多深的感情,她对他到底又意味着什么。海的黑是比橡皮还要残忍的抹除程序。他们今天的见面没人知道,他在解开木船的缰绳时,就知道自己一定是再次安全的,船在海上,四下阒寂,他什么都可以干,他们什么都可以干。于是他才想到往背包里塞进了一盒路上药店临时买的避孕套,死,他没想过,从来都没有,他自己的,包括她的。
他听到清脆的一声。肋骨断掉了。他停下双手,看着躺在沙子上的这个陌生的女人,散乱的头发遮了一半的脸,毛衣被刚才的急救人员剪开,双乳露出来,乳头立挺,像个玩具。她从广州订的,一个乳房模样的假乳房,质地极其柔软,高级硅胶,按照她的左胸,就是他正盯着的这个,一比一定制的,她送的生日礼物,他一直放在书柜最下方的纸盒子里,仅仅把玩过几次,觉得很怪异。此刻也是,他站起身,往后退了几步,倒吸一口凉气。阳光从散开的雾中穿过,打在他的背上,后脖颈的两颗痣像在发光,当他把背包再次背到身上后重又被掩住。他似乎接受了这个情况,算是意外还是赴死,他搞不清楚,也许跟他也无关,配合调查,有什么说什么,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供出一切。这一切是指:我们只是在木船偶遇,海浪风大,女人脚下打滑,跌入水中。我从岸边看到木船有人,随即跳入水中,游出千米,爬上木船之际,女人纵身入海,还没来得及说上半句。我随守塔人往回走时看到海里漂浮人形,协助打捞,看清后发现是一女人,人工呼吸做了,我没上手,我毕竟跟她不熟。
他还能想到更多情况,他天生就是个骗子。但他停下,冷静多了,关系不是死的,突然就可以被撇开,先前抖动而拉紧背包系带的手松弛了。两名救护人员把女人抬上担架,盖了块白布,站在急救车上看他。他看张建德。张建德烟抽完了,再掏,已经没有了,说,人都没了,就这么着吧。
不会再有其他额外问题。回去路上,他把背包直接扔进了垃圾桶,敲响初晨的家门,开门的是妻子和上小学的女儿,锅里煮着牛奶,盘子里有几片涂了巧克力的吐司,鸡蛋切成了心形,两半橙子去了皮用卡通牙签扎着。这里没有任何海难发生,他躺回卧室的床上,想到了小时候学游泳的自己,被祖父拎起脖颈扔进河里,喝水,喝水,喝水,喝水,他被恐惧钳住,锁死在一米八的床上。
乳峰山
景区开发进展顺利,加上几个民俗文化和原始洞穴的噱头,旅游的人极多,原来的灯塔拆了,魏明磊无地儿可去,也跑到了乳峰山,在海边管轮渡。还是椅子,只有一把,他坐上去,和排队的游客闲聊。鱼雷知道吧,就那片浅滩捞的,直接弄到派出所,立三等功。甲午中日战争的,别看表面光滑,那都是让鱼食去了锈,要是突然炸了,大海都得翻天。人们多数不听。他有时也讲自己在塔上,但那些大多只有自己懂,讲出来没趣,解了半辈子象棋,才搞清楚死局从来都是自己,枉费徒劳。轮渡到岸,魏明磊站起来,解开小铁栅栏,看游客回程,又看新一轮游客登岸。其中有一人眼熟,像是在哪儿见过,他牵着孩子,背后跟着一个女人。穿过铁栏时,魏明磊还瞪着他看,但就是想不起来,自从换个工作,哪里都不顺心,看谁又像战友又像仇人,他低下头,在最后一名游客走远后锁上了栅栏。
男人继续往前走,按照指示牌,他们将会向右拐,脚下有些生石,未经打磨,好像故意留有些许意味。男人把女儿扛在肩头,妻子搀着他的胳膊。民宿他做过功课,提前查好了,每次出行都是如此,她们也在网上提前看过,顺着路走就好,五百米后,下榻,吃点东西再出来,四处逛逛,拿山峰的形状互相侃侃,夜就到了。
海滩果然有民俗活动,篝火支在距海不到十米的岸边,有个巨大的火盆,四周用木条支撑,插在湿润后的沙里。太阳落山后,乳峰山岛像被黑色围裹,往海看,波浪缓缓起伏,像岛在晃,往山看,坡下建筑层林叠置,灯光从窗口照出。铁索从坡下直通山顶,挂有彩灯,像条蹬直的彩虹。轮渡还有最后一班,排队回去的人并不多,大部分都安顿下来,正如男人携家眷,在一平坦处铺盖了防潮垫,盘腿坐着,等一个狂欢。人群逐渐聚集,男人看到铁栅栏那儿还坐有一人,跷着二郎腿,左右腿不停变换姿势,等着轮渡再下班。女儿坐不住,一会儿就站起来疯跑,对海格外感兴趣,他则和妻子闲聊。他说,这里怎么样?妻子把包拽到身前,打开,取出几包零食,矿泉水,一本书,又把书放回去,拿出防蚊手环,湿巾,蓝牙音箱,一面小镜子。然后她说,挺好的,有意思。他继续问,哪里有意思?她说,什么?男人闭了嘴,对话大多这样,孩子在就是孩子,孩子不在,就是两个互相交错的问句,他索性躺下,想睡一觉。妻子说,给你这个,去给女儿戴上。他撑起身子,接过手环,往海边去。目光扫了一圈,没见女儿。她一米四,个子不高,还在迅猛生长发育,是世界好奇的守卫者。于是他侧向人群聚集的篝火,往人少的方向看,寻到半蹲的女儿,走近后,她猛地起身,吓他一跳。
你猜我找到了啥?女儿边说边摇着他的胳膊。男人没理,先掏来她的小手,把防蚊手环扩进碗节。一个瓶子,带个塞,女儿说,我打开了。男人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女儿说,你真老土,漂流瓶,来自大洋彼岸,有字。男人说,真时髦,写的什么?女儿抖了抖纸条,看了看不远处的篝火,映着光,说,我渴望……有人爆裂地……爱。男人抢过来,说,我看看。他把纸条贴近面庞,看清了上面的一行字:我渴望有人暴烈地爱我至死不渝,明白爱和死一样强大,并永远站在我身边,我渴望有人毁灭我并被我毁灭。落款,罗丝。他觉得笔迹熟悉,但又纳闷,翻回背面,纸条写着另几个字,致我永远的杰克。
女儿吵着要看,他把纸条拿高。篝火处发生了争执,两群人吵起来,有个大高个从更远处跑过来,扶着头顶的帽檐,吼着,吵,吵,吵,继续吵。那人,他好像也从哪里见过。时钟被拨回某个时刻,有一艘木船,她清澈的眼睛望着他,有声音从某地传来,像是某种呼唤,杰克,杰克。女儿跳起来够,男人没拿稳,纸条顺着风飘出去,直到落入光的背面,不见了踪影。他似乎也知道,它也终会落入大海,重演一次海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