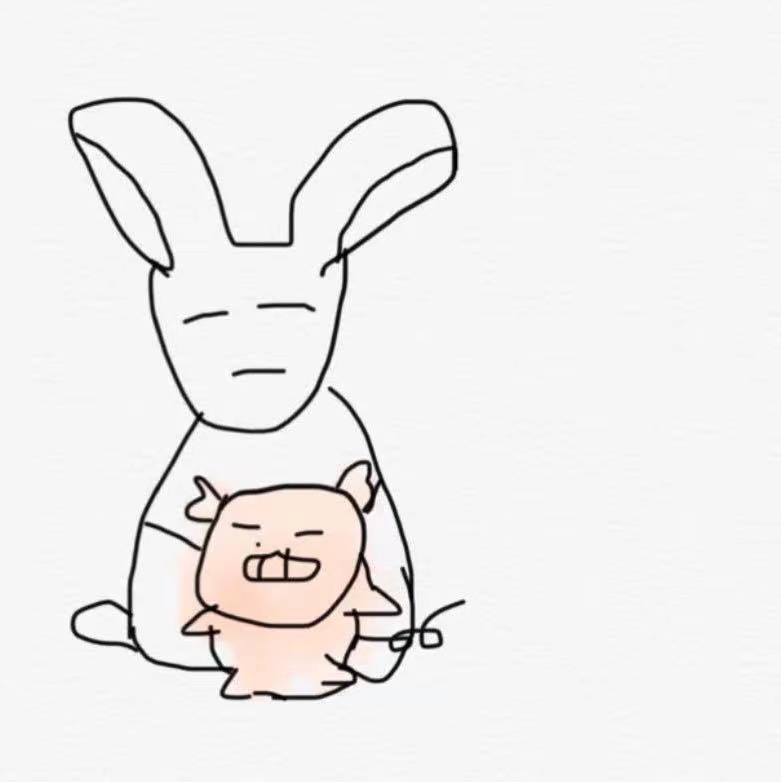我游进记忆深处,找到那些不愿重临的痛苦瞬间。
冰窖巷拐角有片空地,我每天花三个小时待在那里。
空地有半个足球场大,原本是家露天咖啡馆,2021年因疫情倒闭,拆除后,只剩下些从地面破土而出的钢架和堆摞在角落的塑料板材,外面围了圈半人高的围挡,但拦不住我。上个月,我从学校翻墙出来,想去吃个冰淇淋,路过空地,看到他们正在施工,两个戴着安全帽的工人用一柄巨大铁锤猛砸咖啡馆的墙壁,涂鸦破碎,混凝土轰然倒塌,灰末缠绕住剩余的废墟,工人直起腰,又砸开另一面墙来,我在空地边驻足观看了一整个下午。快结束时,工人们用手推车把废渣运出空地,我凑上去,问我能不能帮忙运一车。
没人理我,一名年纪大的人冲我摆摆手,我凑过去,他一脸疲惫地说:
“躲远点。”
第二天,我又来到空地,这里已经变得跟其他空地并无二致了。但我见证过它的辉煌与毁灭,也知道它的今天如何诞生,这里便成为了只属于我一人的秘密花园。我在空地上四处乱转,尘土随着皮鞋起落肆意弥漫,我从空地角落拿下来一张椅子,坐在上面,看着空地外的人来来往往。
初中这两年来,我痴迷游戏,最开始是一些角色扮演类的网游,游戏背景复杂、充满史诗感,我要不是某个门派仅存的全部希望,背负血海深仇,要不就是不世出的天才,被命运选中,开启一段冒险,我逃课来到昏暗的黑网吧,在二手烟和谩骂声中打开久经沙场的电脑,经常有身在江湖的错觉。
这类网游总有暴风骤雨般的新鲜感,层出不穷的装备和BOSS,无尽征途,我们马不停蹄地四处征战,没人知道究竟哪里是终点,也没人在乎。深夜,网吧跳闸,所有光都熄灭,有人愤怒地敲打桌子,有人叹气,几百张嘴的呼吸声清晰可闻,借着身后打火机的火光,我看见屏幕里映照出一张油腻,沧桑,额头有三颗痘,上唇裂开向上翻出两瓣的脸,我的脸,它丝毫算不上光鲜亮丽,我转头,看见身边坐满了这样的人,于是我起身离开这间网吧,之后再也没有回去。
离开网吧后,我换过很多阵地,24h快餐店、公园小亭子、废弃铁轨满铺的尽头等等,这些地方收留我,却并不能缓解我的不知所措,我能在那里一直坐下去,坐到太阳升起,坐到风雪来临,它们也只能帮我到此了,迷雾依然。我没放弃,所以不停寻觅,终于,树叶变黄时,我在离家4个路口的胡同里找到一家游戏机店。店有两层,一层放满一排上时代的游戏机主机和32寸液晶显示屏,二层是店主的卧室,有一台高配电脑以及两台最新的次世代主机,在我们熟络起来后,我常上来玩。店主是个留着长发的男人,看不出年纪,没有顾客的时候,他会让我免费玩单机游戏。我通关了不少,这类游戏总有一段完整的,发人深思的旅程,故事中感受到的情绪会在结束之后仍然粘稠,难以脱身,他从不问我为什么不上学之类的话,我也没问他有没有结婚,彼此交流止于游戏,他能精准说出某个游戏让人心潮汹涌的地方,还能拿上手柄,轻松击败某个我望而生畏的BOSS。我每天都去店里。放假前夕,我的课桌被肥龙用美工刀在表面上刻下一只巨大的兔子,到了下午,我问店主,我们究竟是来这里做什么的?
“来玩游戏的。”店主说。
“不是,”我摇头,“我是说来这个世界上。”
店主转过来,直视着我的眼睛,他伸出手,第一次拍了拍我的头。
“是来玩游戏的。”他接着说,“下次教你作弊的方法。”
过完年回来,游戏机店的卷闸门紧闭,又过半月,这里变成一家面馆。我再次失去据点。新学期,我每天下午翻出学校,在市里乱转,直到深夜才回家,我把探索当做一种游戏内容,城市是沙盒,每到一处没去过的地方我就能升级,每做一件没做过的事,就能离通关更近一步,一直到我拥有了空地的今天,这座城市已经被我通关了一半。
我是空地的国王,我把所有桌椅都支起来,按照我的喜好摆放,我把透明塑料篷布罩上钢架,想在下雨时也能有容身之地,我把我喜欢的游戏海报贴到墙壁上。台风天到来,所有努力全部功亏一篑。我花一整天把残骸清理干净,土地泥泞,翻涌不平,只有我的杂乱脚印。我坐在仅剩的椅子上,暴雨的余波仍有几点砸在脑袋上,我望着空地,幡然醒悟:我想要的是一块属于我自己的完美领土,如游戏里的世界一般,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自然会破坏它,他人会破坏它,连我自己也会破坏它,与其放任它在现实里遭受摧残,倒不如一开始就破除实体。
于是我开始在心中幻想出一座山谷的诞生,就以空地为依托。我收纳过这块空地上咖啡馆被毁灭的过去,也能让幻想在空地上凭空而起。
山谷有几千亩大,两边狭,腹地开阔,开阔地带有一座废弃许久的赛博朋克都市,名赛博城。赛博城扎进云海里的高楼外立面布满光伏板,底层灯火通明,机器人不知疲倦地打扫街道,每过八小时,城市折叠变形,确保永远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缓慢西落的太阳。城市北侧有一面湖,清澈如镜,名镜湖。镜湖雾气弥漫时会有倒塌落败的遗迹在湖中心显现,站在湖边能看见淡紫色的光斑浮现其上,踩着涟漪就能走过去,如显现神迹的耶稣。城市南侧空着,我暂时没想好。
我每天下午逃课来到空地,构筑这座山谷,建造每一栋楼,填满每一间房,为几十层高的立体街道设计互洽路线,我整备湖底和极少出现的废墟,还在已经足够隐匿的废墟里又设立了一道隐藏门。我从记忆里偷出曾在游戏机店玩过的各类单机游戏的碎片和影子,揉成一团,塞进这座无人知晓的山谷里。我为它起名空谷。
一个晴天,下午,云层辗转创造出忽明忽暗的地面,塑料椅面铺着一张法兰绒毯子,我坐在上面,决定进入空谷。我幻想自己正坐在赛博城运行中的轻轨上,摇晃中,能透过车窗看见遥远的天际线在钢铁森林之间闪烁,但并未成功,城市边缘如沙砾消散,然后是地面和轨道,一眨眼,我又坐在空地角落的椅子上。我再次尝试。我来到镜湖岸边一所木屋,波纹撞击码头,水珠碎裂会让潮湿的味道溜进鼻腔,我抬起头,看见山谷缓慢消失,我低下头,看见冰窖巷拐角空地的土地面,此时干燥,但泥泞痕迹仍保留下来。苏轼在攀登庐山时,曾写下题西林壁,最后两句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背诵过,如今方有感悟。
我不再建造空谷了,我惧怕近在咫尺却一触即碎的梦境变得更加诱人,以至于现实过早枯竭。我端坐塑料王座上,看着过往人群稍纵即逝的脸庞,我们是彼此的泡影,一个老人从人群中走到空地上,他是光头,留有垂至胸口的胡须,根根银白。
“你在观人。”
老头站在空地边缘,向我搭话。
我摇头,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观人,我在发呆。
老头笑起来,他说观人是练内功的方法,从明朝传下来的。找个人流熙攘的集市,静坐,仔细打量每一个过路人,从路人身体外在找到内里泄露出的蛛丝马迹,然后收归心中,你的丹田里就会有这名路人的一部分内在,多观一人,丹田里就多一人,人多力量大,内功自然有提升。老头说他年轻时深谙此道,观千人,身负千钧气力,解放初期凭借高深武功做过不少行侠仗义的事。宪法颁布后,他去峨眉山山顶,在日出霞光里散尽了内力。
我说我也想学,请老前辈教导。
老头搬了把椅子坐在我对面,让我盯住他的眼睛,想象把自己的目光化成一条线钩,探进他的脑子里,把其中的一部分钓出来。我照做,老头的眼睛十分有神,我把目光想象成一只蝴蝶,从他的双目里翩翩飞入,在他的精神海洋里抖动翅膀,色彩纷呈的光点沾染,蝴蝶飞回我的眼睛。我感觉一团火注进丹田,感到热和愤怒,班上带头欺负我的人外号叫“肥龙”,此刻,我决心在学校里打他一顿。
“你有天赋。”老头说,“你不应该练武。”
我说在学校,有因为我是兔唇而欺辱我的人。老头说你可以把他们都打倒,他们会害怕你,你想要这样吗?我在沉默中思考,我得出否定的答案。老头站起身,说他要走了,练习法我已经会了,希望我能在某个合适的时候把这门功法传给合适的人。
“为何我不该练武?”
“猎犬终须山上丧。退隐之战总以自己为对手。”
之后三天,我在空谷里观下十人。最开始很难,我没法快速进出行人内心,只能轻拭表面,如隔靴搔痒,一下午过去,我观到两人,第一位是坐在空谷对面的流浪汉,衣衫褴褛外貌脏污,我从他内心带出一种平和感,状若圆润水滴,第二位是女性白领,她在经过空谷时瞄我一眼,被我抓住空隙,从她心里带出一根纤细精致的藤蔓,有骄傲和怜悯,我通通藏进丹田。获得成功经验后,我进步神速,至学会观人法的第三天傍晚,我的丹田里已经收归十个形态各异的精神碎片,大脑、肉体变得比春天更丰饶。我想,既然能贮藏,也一定能释放,就如同空地的毁灭与创造一样,我决心举一反三,用丹田里的碎片在空谷创造出一位活生生的居民,他能弥补我无法进入空谷的遗憾。
我给他练武老头的炽烈,给他白领的骄傲,给他流浪汉的平和,给他一个年轻人的热情,给他一个母亲的包容,给他一个背着乐器女生的孤独,给他一个年长男性的思辨力,给他一只猫的灵敏,给他一个建筑工人的肉体,给他一个小女孩的清澈瞳仁。
他在赛博城醒来,全身布衣,背负唐横刀,刃长3尺3,出鞘声如猿啼。我看到他坐上轻轨,在最后一站下车,站在城市最底层,目视着掺杂云烟的密集楼群一刻不歇地运转,灯火辉煌。他喜欢去地下十四层的酒吧喝金汤力,从城市最高层用动力翼滑翔,他为唐刀和手臂加配各种芯片,有增强臂力与反应速度的,也有录入一整套完整剑谱的,他喜欢带有高速振动功能的剑柄,舞起刀来能听见蜂鸣。他夜间常去镜湖边打坐、冥想,赤裸上身,刀摆前侧,他跳下湖,从水底收集蚌壳,自己打磨、穿孔,挂在脖颈上,走起路来会哗啦哗啦响。
这些时日,我沉迷于这个游戏。我彻底抛弃学校,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空地上待着,沉溺幻想,我虚构他的一切,他的门派叫逻门,讲究由力到刀的百分百输出,杜绝浪费,极简主义,他喜欢紫色,每天日落,赛博城上空的电子烟雾总被霞光染成这种颜色,我叫他春庄,这是曾经位于此处的咖啡馆的名字。
我开始跟春庄对话。
我单方面向他诉说,讲述我在城市游荡时所见所闻。我收集瓦楞纸板、玻璃瓶和旧书籍换钱,帮饭店和网吧做杂活来换取饭食和游戏时间,这种方法对我来说屡试不爽,成年人爱用施舍代替歧视。我讲述我玩过的游戏,通关后都会失落,尾声在脑袋里不断回荡,留下淡蓝色的余响,然后现实和天黑一起袭来,我得挤进人群里重回福利院来完成我的一天。关于这些,春庄的回应永远只有一句:
“须臾罢了。”
一个雨天,体育课,学校里唯一计较我缺课的年轻男老师再次把我叫进办公室,他给我买来一罐柳橙汁,不再询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班里其他人聚在屋檐下聊天、下五子棋,老师用一根玳瑁色、闪烁瓷器光泽的细长钢笔批改作业,我看到雨滴化成水珠流过玻璃窗,纸张翻页声音夹在雨声中间,下课铃响,老师说他要调去别的城市了。
他的课在下午最后一节,上完后,我淋着雨走回空谷,篷布被积水捏出一个大坑,我坐在大坑下。我向春庄讲起我小时候的故事:工厂有三支高耸入云的烟囱,冒白烟的时候,巨大撞击声就能传到家里来,像巨人的脚步,父亲经常喝酒,喝多了就睡在沙发上,电视机连着录像机,播完后雪花被锁进屏幕,木茶几上、电扇上、玻璃屏风上、父亲身上都是一块白一块黑。我们住的房子很暖和,到冬天,暖气片上总架着四五个红薯。
后来烟囱被爆破定向拆除,父亲带我坐了14个小时火车,至一座南方省会城市。我们去了游乐园和海边,吃到了烤梭子蟹和章鱼,他给我买了一身罗纹布材质的新衣服,帮我整理好领子,我们坐在公园山头的长椅上,他告诉我现在是知了在叫,他说他去买包烟,让我在这里等他,千万不要乱走,他把厚厚一沓钱塞进我胸前口袋,后来我知道那是他两个月的工资,他走下山,走出了我的视野。那时候我刚上幼儿园,路走得很慢,英文字母记不清,不懂分辨,话也讲不大明白,唯独这段回忆能追溯出每一个细节,我看到父亲走下台阶的背影逐渐被森林遮蔽,我明白他不会回来,我的臀部贴着冰冷椅面,一动也没动。
雨砸上篷布,也落入镜湖,千千万万重涟漪。春庄坐在湖边小屋外的码头上,听完我的故事,站起身,突然从背后拔出刀,竖劈,一刀砍在镜湖上,湖面被分开数秒,猿啼持续,他看向我,说:
“我把我的刀传给你。”
这是春庄第一次主动对我说话。
出刀这刻起,春庄活了过来。
活过来的春庄喜欢阅读,如饥似渴,我不得不阅读福利院的每一本书,将之在赛博城幻想出来,他极富探索心,他会撬开高楼里每个打不开的房间,拿走私人物品,和机器人对话直到它们用完所有预设语音,他坐上轻轨,一路走到车头,望着花花绿绿的仪表台向我提问:
“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
“什么用都没有。”我说,“它们只是该在那儿。”
这段时间,我每分每秒都在幻想,春庄的下一步总是不如我所料,我只得在他落子之前铺好尚未完善的棋盘。为了消磨他的侵略性,我把神话故事,哲学名著、魔幻现实主义长篇,武侠小说都塞进空谷里,扔在路边,扔在轻轨上,扔在楼顶,扔在镜湖中,春庄捡到它们时总会很开心,他阅读的速度比我更快。有一天,春庄在赛博城中心广场的长椅上阅读中突然放下书,抬头问我,他是什么?
我说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春庄。
春庄低下头,看着广场的镜面地板反射他的眼睛,他说他没有人物弧光,只是一个为了存在而存在的角色,空洞单薄,尚未统一的刹那情绪充斥填满心脏内所有房间,无时无刻,虚无肆虐其中。他不像有一个完整的心智,更像是旅程中的插曲。
我说:“多出去走走吧,大自然会治愈你。”
之后几天我没再去空谷,我害怕春庄提出的问题。我把课桌搬到角落,背靠垃圾桶和干涸拖把,我用一张A4大小的纸画下空谷全景,思考空余的南侧究竟能放下一个什么样的景致来让春庄流连忘返,不在自身上钻研,我想象出一座高耸的塔,每层都由不同的机械守卫坐镇,击败会获得武器或装甲,甚至是小机器人随从,高塔的地形环境、守卫顺序难度、战利品全部随机生成,每次进入都是全新体验。午休,我继续构思,一个男人走进教室,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我低头在纸上画高塔内部地形,光线热烈,我眯起眼睛,男人开口,问我在画什么?
我听出是已经不在此处教书的男老师的声音,我说是我的梦,男老师静静在身后看着,有同学跟他打招呼,他也回应,依然站在我身后,看着我画,我收起画。我说要去吃饭了,他问方便一起吗,有事跟我商量。
他骑自行车载我。校门口有两排据说有五十年历史的梧桐树,枝叶繁茂,春天叶絮落满整条柏油路,如毛虫海洋,夏天蝉鸣不断,树影斑驳,烈日被打散。我们路过时,男老师突然说:
“我初中时候,这些树就有这么高。有人说他们有一百年历史了。”
我说不知道,说不定哪天晚上,所有人都放学回家后,一个穿斗篷的男人提着铲子,用完全相同的两排树替换掉这些树,轻挖轻埋,打扫路面,连叶子上的褶皱都捏成一样的,我们也不得而知,我们只是树的过客,谈不了永恒。男老师哈哈大笑。十分钟后,我们坐在一家牛肉面馆外等位,男老师说他曾在这附近上高中,中午常来这家店,偶尔会早退翻墙过来,避免排队,他问我上次考试的成绩,我报出来,他点点头,说:
“你很聪明。”
我们吃起面来,他问我想不想读高中,然后考大学,在毕业前,他负担我的一切学费和生活费。我没说话。吃完面,我坐他的车回学校,梧桐树道,我开口:
“你也觉得我很可怜。”
男老师停车,踢下车撑,转过身按住我的肩膀,直视着我,说
“你很可怜,但绝不要以此为耻,无视苦痛并非勇敢。筑墙容易,前进难,周生,你有过更好生活的机会和能力,就得拼了命地抓住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我带着画好的高塔回到空谷,春庄不在赛博城和湖边,我往南看去,透过赛博城昼夜奔流不息的灯光帷幕,我看见高大乔木的影子,摇曳着,在视野缝隙中起舞。我来到南边,这里多了一片森林,准确来讲是三棵树,三棵前所未有的繁茂、高大的树,肥硕根部如同从上而下浇下水泥一般堆叠褶皱,树躯交替攀援,时有空隙,所有树叶处在同一平面横向延伸,翠绿色天盖,春庄坐在枝丫上,空隙中,望着空谷更南边。
我问他这三棵树是从哪来的?
春庄说他在空谷里散步,思考很久,终于明白,原来他是世界本身。他拿起湖边石头,世界的石头就被拿起,他看见赛博城路灯闪烁,世界的路灯就在闪烁,他为意志,空谷为表象,所以他看见三棵巨大的橡树从土壤里拔地而起,结成一个世界,世界的橡树也就此茁壮。
“橡树不长这样。”我说。
春庄说他看见的橡树就长这样。
我扔掉画着高塔的纸,俯身下去,紧紧盯着他的眼睛,我说他不能这样,他怎么敢这样?
春庄把手伸向背后,他没背着刀,但仍做出抽出什么的动作,他握紧,高举右手,用力下挥,我看见怪异橡树的叶盖出现一道缝隙,赛博城的灯幕断开一层黑暗,镜湖上半部浓雾破散。
“我把我的刀传给你。”春庄说。
从校门口走到空谷是整300步,刻意控制下,偏差不超5步,每分钟呼吸35次,每分钟眨眼20次,福利院寝室的灯9点半熄,塑料开关发黄老化,延迟2秒才起作用,我13岁,还有8个月零11天就14岁,这些是数值,我这场游戏的数值。没能等到店主的日子里,我记录、控制这些数字,它们的规律是我成为主角的基础,烂熟于心,终有通关日,我没拿到作弊方法,只能如此笨拙。
赛博城有167座楼,4条轻轨,镜湖最深处9米,雾气总在凌晨4点产生,春庄身高1米84,他曾经总会坐13站A号线轻轨到马空站下,他曾经会坐电梯下到地面下42米,坐在吧台边第3至第6个高脚椅上,他有一双铃圆的眼睛,对视时能让我感到真诚,他总笑,偶尔发呆,从未哭过。
我说:“你没有刀,你的刀是我给的。我创造了你,春庄,你和空谷都是假的,你是一个影子,一句叹息,一个被迫早熟的男孩脑内粗制滥造的幻想,仅此而已。春庄,你什么都不是。”
状若西兰花的橡树摇晃着,我在空谷外,镜湖中心的遗迹正闪烁,走进去,第3堵墙的侧面能穿过,进入隐藏起来的湖底洞窟,春庄的剑扔在里面,赛博城环卫机器人扫着从一开始就一尘不染的街道,一只啄木鸟从橡树树窟飞出,落在春庄肩头,这不是我创造的。
“没关系的。”春庄说,“你我皆须臾。”
我终于醒悟,春庄原来是我通关前必须击败的BOSS。
春庄攻略战就此打响。我让电子病毒黑入赛博城的主管系统,轻轨跌落,砸塌光伏储电站,电流泄露,逃窜至每栋建筑外立面,整座城市都弥漫焦味,几百台智能机器人全部暴乱,钢铁拳头挥向春庄,但都被一一化解,我花费巨量心力幻想出的灾难甚至没能让他皱一下眉。他修好电站,修好轻轨,修好每台已成残骸的机器人,问我:
“何必搞得一片狼藉?”
我引入一场暴风雪,从北向南,镜湖被完全冻住,橡树枯萎,强风在赛博城街巷里穿行,温度跌至零下20度,春庄裹着外套,蜷缩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湖边木屋角落,涌进来的雪盖了满身。我在屋外盯着春庄在颤抖中入睡,等待着他的死亡,次日,太阳升起,春庄抖落掉一身积雪,再次站起来。
我击败过很多BOSS,我会在无数的死亡回档中记下它们的招式,找到它们的破绽,我在一张纸上抄写数值和机制,搭建对策和进攻方式,BOSS只会端坐在王座上等待我的下一次挑战,然后迎接命中注定的结局,但春庄不一样。他如此谦卑,还拥有让人不可置信的强悍。我燃起斗志。我查找地球历史中几次足以毁灭物种的灾难,陨石、氧气浓度、瘟疫,我背下核聚变的定义,我劝诱他自杀:
“你的世界有造物主,就是我,你怎么能忍受?”
他摇头:“这里现在是我的世界了。可你的世界不一定是你的世界。”
空谷战争期间,男老师来找过我一次,他问我考虑得怎么样,得抓紧时间准备中考,那时我忙着从一本名为《黑洞与时间弯曲》的书里整理出时空坍缩能引发的灾难,无暇顾及他,我说我不会去,我抓住了一个机会,能接着过日子。
“更有趣吗?”他问。
“更狂热。”我放下书,这么回答。
这场战争打得拖沓与决绝,空谷在几个月里被毁灭了数次,又被春庄重建,春庄建议我用递进战略,即在确定这次的打法比上一次更好之前,不轻易尝试,这对空谷的环境和我的脑力都有好处,我同意。我依然把新阅读的书幻想在空谷四处给他看,现在多是讲战争、物理、化学、历史、心理学、哲学的教材和工具书了。
临近中考前两个月,我不得不承认,春庄是玩家,并非NPC,我得用PVP的方式对付他。我再次开始观人,然后用内力赋予机器人生命力。我给它们从大量年轻人心中提出来的仇恨和愤怒,再给它们武功和钢筋铁骨,我按照12生肖的排次为他们起名。鼠、牛、虎、兔,它们有比坦克还厚的装甲和轰鸣声响彻天际的核心,它们没能给春庄带来伤痕。蛇、马、羊,它们有灵活的金属骨骼和最先进的系统与武器,它们开始让春庄重视起来,他用战术和克制招式对付它们。猴和鸡被我同时制造出来,它们是两台拥有飞行能力的高速机器人,一个主练上三路,一个主攻下三路,它们在报废前让春庄的脸上多了一块青肿。我花费一个月的时间创造出狗,狗是弓箭手,能开二石弓,三百米内百发百中,他们周旋许久,最终,春庄用计把狗诱骗到赛博城底,在巷战中拿到近距离,以被射中左臂为交换出刀,一刀毙命。我不得不承认,春庄早已进化,他比我乐观,也比我狡猾,甚至比我更能理解书中内容,前11位杀手都取自路人思想中的片刻弧光,只有打火机火苗大小的仇恨,远不能赢得战争。
中考前晚,我从福利院溜出,来到空谷,是夜,春庄正在木屋里睡着,镜湖水浪每隔几分钟就砸在码头上,我在铺了法兰绒的塑料椅上坐下,开始观自己。
我游进记忆深处,找到那些不愿重临的痛苦瞬间。幼儿园同学叫我丑八怪,我趴在桌上,看着窗外的滑梯尾端掉漆的筒壁,希望下课铃能提前响起,父母和我一起去公园,玩碰碰车前,母亲拽着我走向反方向,因她望见了同事,福利院有一名哑巴,小学毕业,我们一起爬上市南仙游山,在仅有我们二人的亭子里躲避突如其来的暴雨,男孩开口向我说话,说他只是不愿意说话,下山后,我再不见他,直到他被领养那天,我在二楼阳台和坐进副驾驶的他对视了最后一眼。
我把这些难以启齿的愤怒都塞进丹田里,待火焰燃烧到比恒星还壮丽时,白天到来,我把全部火焰都注入赛博城一名扫地机器人身体里,为他起名为猪,做完这些,没给他任何设定,猪看向我,问我:
“哪里是结束?”
我指明湖边木屋的方向,然后瘫进椅子里。
我坐着,冰窖巷缺口外面盛着蜂拥而去的车流和人群,城市楼群毛毛躁躁,太阳已经爬到电视塔旁,光竖着晕染,烧进我的瞳孔里,不远处有一所高中沦为中考考点,拎着透明文件袋的同龄人从我面前经过。
快到中午的时候,猪回来了,他说已经解决了。
我说镜湖中间的废墟里,第三堵墙可以穿过去,里面有一把刀,出鞘声如猿啼,它是你的了。
我听见宣布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我听见数千声脚步,嘈杂如雨,我想起父母,想起店长,想起练武老头和肥龙,想起春庄,他们都曾是我游戏的一部分,现在已成过去,我却仍未通关。
我在空谷里一直坐在傍晚,太阳落山,我看见空谷南侧那三棵大树,影子拉得细长。我低下头,第一次打量名为猪的扫地机器人,他有一个摄像头样式的眼睛,脑袋和躯体都是长方体,双臂是两根细长的吸尘器管,下身是履带,模样滑稽,我直视他的眼睛,火焰撞进我的心脏,我问他,是否有想过,他是什么,世界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