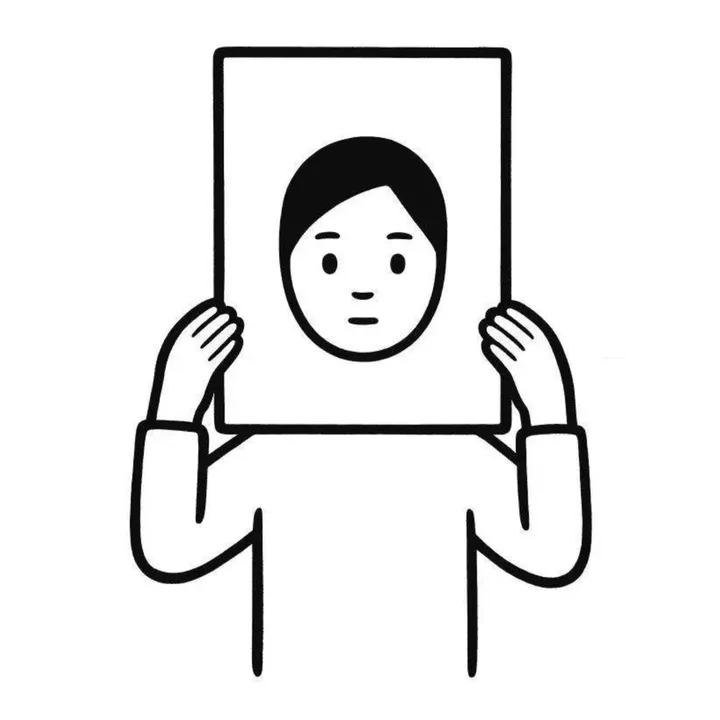洪水冲垮了可秉持的理性,舅舅开始用大白兔奶糖钓鱼,相信枣树是飞升的火箭,远在另一个星球的天堂里有失落的爱情。
母亲在堂屋低声啜泣,我们在隔壁听得极清,鼻腔像个针筒,不停地回抽。蛐蛐在叫,偶尔被狗吠折断,隔一会儿又续上,她也没闭眼,等着我说什么。老屋墙壁太薄,砖味浓烈,整体收拾得还算净洁,和记忆里也差不了多少。猛地回来,多少哪里都不适应,也怕她不适应,确实谁也睡不着,这个夜晚,赵振明躺在堂屋,赵振菊陪着,我们躺在里屋,土狗拴在大门口,玉米秆倾倒一片,沟渠有几只蛙鸣着,圆月高高悬在枝梢上。
一九九九年,我十岁,上小学四年级,在实小。我姐十八岁,学习不好,在县卫校念护理。她交了个蹩脚李姓男朋友,二十岁,是个盲流,有一辆红色的宗申摩托,引擎声震耳欲聋,像一万只振翅的蝉粘在车轮上。如此高调,我妈一下就发现了,那个暑假,大概是最热的一天,空气扭曲,万物蒸腾,她打了辆车,花了半个月工资,把我们突然送回了老家,大汶河不远处的赵家庄。经过了大概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听着司机时不时的抱怨,我们到了这个极为陌生的地方。当时的脑海里是没有关于老家的概念的,也不知道我竟然还有个鲜活的舅舅。不知道他是在等我们,还是习惯性站在村头,背着手,佝偻着,又在突然间挺起脊背,快步朝扬起的土灰中走来。我们一下车,姐姐就因晕车吐了,司机骂了一句,后来他又骂了,因为他还要原地等我妈十几分钟,招待所客人的脏床单还需要人往洗衣机里塞。说白了,她就要把我们放在这里了,放在一个陌生的舅舅这里,然后立马赶回去。
那个舅舅上来接行李箱,我妈递给他,他扭头看我和我姐。圆寸,黑白相间,面部沟壑深,皮肤暗棕色,笑起来牙齿略黄,身材削瘦,穿一白色背心,棉麻短裤,灰色凉拖,整体上有一种沉旧的年代感,不知道是不是记忆填了色,他更像是通过词语出现的,我的,舅舅。我和姐姐跟着走,没几步就进了掉漆的红铁门,舅舅家就在村头,门一开,能完美接住乱石路上刮来的所有的土。院子里是一棵长势旺盛的枣树,枝头挂满了早熟的果子,地上零星也有散落,在韭菜和小白菜之间。我随手捡起一个,舅舅低头朝我嘟囔,皱起眉。我吓得藏起手里的枣,他掏起我的胳膊,扒开我的掌心,指了指那颗青枣,继续嘟囔,我勉强听到他唇齿间的一句话,这个太青,不好吃。
当然,这话没我描述得这么流畅,在他暗黄的牙齿后面是一块极大的舌头,说话不太利索,像含着难以化开的大糖果,加上正宗的土话,在刚到的一两天里,完全像是后来中学里的英语听力,尽管集中了精神,依然不知所云。不过后来好多了,基本都能听明白,因为我和他走得近了,这是后话,所以,我就不用磕绊的语言转述了。
姐姐伸手拍掉我手里的青枣,舅舅冲她笑,嘟囔,别欺负你弟弟。我不介意,她一肚子气,放了暑假,没和男朋友见几面,就被我妈送过来,来了一招距离战胜一切,可恨的是我也得跟着,做了可怜的陪葬品。舅舅把主屋腾给了我们,我姐住最里间,屋子最大,本来是一堆杂物,都清到了院子里。我住堂屋隔壁,就是我躺的这个,也不算小,摆着一张一米五的钢丝床,一个黄课桌,课桌底下压着层层老旧的照片。侧屋舅舅住,两间房,一个土坯炉灶,一个放着二八大杠和柴垛。他在柴垛上铺了一层棉被,弄了个小木凳子当床头柜,别的也不需要了。我们就算住下了。
我妈给舅舅塞了些钱,又说了几句,舅舅嘟嘟囔囔的,两人推来推去,她一直在嗯啊的点头,随后匆匆走了。走前拍了拍我的头,让我听舅舅的话,又剜了眼姐姐,一副看我治不了你的意思。事后证明我妈失败了,我姐只伤心了三天,这也是后话。我妈走后,我们三个愣在院子里,互相看,不一会儿,有青枣落在我姐头上,砸得疼,她骂了一句,和那出租车司机一样。舅舅摆手让我们躲进柴屋,也就是舅舅的卧室,我们站好了,舅舅抄起墙根的一根木杆子,劈里啪啦朝着枣树枝乱打了一通,枣仓皇掉落,有的落在他的脸上,他会缩起脖子,叫一嗓子,因为发音问题,那一嗓子像一只嵌住脖子的鹅,逗得我和姐姐都笑了。随后,他把满地乱滚的青枣用大扫帚扫到菜地里。砸人,不好吃,他说。他弯腰站在菜地里的憨厚,让我开始对他有了一丝好感,也有了一些好奇。姐姐笑罢就回主屋了,我被舅舅盯着尬尴,也跟着姐姐跑了过去。她跨进门槛时说,咱舅舅,脑子有问题。我没明白,跨进门槛跟着她,她不愿意多说,回了里屋关了门。我站在堂屋里,才注意到暖炉旁边桌子上有一台开着的大背头电视机,画面有些模糊,在播放什么新闻,上面还压着一本泛黄的书。舅舅也跟着迈进来,手里拿着几块大白兔奶糖,我捏起一块,他笑着看我剥开糖纸,我把它塞进嘴里,慢慢咀嚼起来。他指了指自己的嗓子,大概意思我能明白,他说他说话不清,不好理解,我点点头,说,舅舅。他说,对,立民。我很高兴他能叫出我的名字,我说,是的,孙立民。他摸摸我的头,坐在正对门方桌两侧的一张木椅子上。那椅子下沿的一根腿还用铁丝绑着。屋里地面凹坑不平,是硬化的土,抬头还有一面斜挂的镜子,镜子的边缝里插满了泛黄的照片。我踮起脚来看,谁也不认识,好像不是一个世界。
我姐经常往村另一头跑,她不跟着舅舅,我不,我喜欢跟着他后面。早上,他给我们弄过米粥,米粥里添个鸡蛋,吃完,他就拿上那根打枣的杆子,那时我才知道那是一根自制的钓竿,杆头绑上一根细线,用力一甩就能三米开外。我帮他拎着一个红色塑料桶,桶上有盖,不算轻,我猜是鱼饵,要么就是昨天钓上的鱼。他扛着钓竿,在前面带路,顺着乱石路走,穿过自家的玉米地,就是一片开阔的花生田,田埂不算宽,我们像猫一样前进。太早了,烈日还没彻底醒来,汗都没爬上身子。过了花生,有一处巨大的水井,已经废弃,看上去像个炮弹坑,但是周围有石砌,断了一撇,他让我小心,我偏故意探头看。井底大概深六七米,绿藻和垃圾漂浮,有些反胃,立马缩回头来,但不甘心,捡起一块石头丢进去,等着那噗通一声,伴随着的是舅舅的手,轻柔又有力地拍了我的脑袋,我才往前跑去。
河面宽阔,看不到对岸,水质沙黄,流速均匀安静,大汶河像蠕动的用旧的地毯。舅舅走到河边,找了一处缓坡,丢下随手拎的马扎,压在泥里,让我坐着。我才不会坐着,放下红色塑料桶,就蹲下看浅滩里的草,根部还有小虾。河风吹来,扑在脸上凉得透彻,把热都抵消了。我穿着凉鞋踩在那些小河虾上,它们跑得快,我追得紧,还没出去几步,被舅舅拽住衣领,说,掉进去。他比较急躁的时候,会只说几个字,我能明白,于是退回来,在他脚边玩。他开始穿线,绑好钓竿,检查鱼钩,让我打开红色的塑料桶。我照做,打开盖子,里面没有鱼饵,而是密密麻麻的大白兔奶糖,错落地码在一起,估计有四五十块。我蹲着没动,他说,递给我,一块就行。我拿出一个,递他手里。他把钓竿紧在腋下,拨开,糖纸丢回桶里,糖块放在嘴里片刻,又吐出来,然后从钩尖上穿过,推了推我。我站到一旁。他向后摆着胳膊,猛地往前甩出,那块大白兔奶糖拽着鱼线噗啦一下落入水中,接着他把鱼竿插在泥里,用一块石头垫好,不会真的有鱼上钩,没有鱼会吃奶糖,他又从塑料桶里拿出一块,剥了糖纸给我吃。我接过来,含进嘴里,他笑了笑,就那么坐在马扎上看着河面。
我在浅滩上垒起巴掌大的墙,把一围水圈住。记得父亲跑大车前也喜欢钓鱼,我跟着去,也会这样帮他弄个小水坑,他钓起的鱼可以丢进去,我就蹲着看鱼,那鱼嘴一张一翕,身子转着圈游,总是逃不出去,也不知道它会不会难过。但我挺难过的,我没有鱼可看,能钓上个鬼来,我这个舅舅。我把泥墙推塌,又踩上几脚,说,鱼不吃奶糖,你是个傻子吧。他不说话,只是盯着河面。没一会儿,站起来,把鱼竿拿起来,那根光秃秃的线聚过来,只剩个钩子。他说,你看,吃没了。我噗嗤笑出来,叉着腰说,那是化了,化了,什么吃了。他说,嗯,你再给我拿一块。我喘着粗气照做。他又重复着之前的动作,重新把奶糖甩进河里后,也叹了口气,说,你舅妈也爱吃,我想着能不能把她钓回来。我怔在原地。他接着说,你舅妈已经吃了一块了。在那个状态下,我是没法进行想象的,我不知道舅舅那是什么意思,他的语言无法表达清晰,都是我一处处拼凑的,意思大概是这样,他把大白兔奶糖甩进河里,还带着根线,竟然是跟我舅妈有关。我想起姐姐说的那句话,他脑子有问题,不禁觉得浑身发冷,尽管已经热得汗涔涔了。
舅舅看着平静的河面,说,特大洪水,死了很多人,你知道吧,立民。我听我妈说过,去年电视新闻里铺天盖地都是。他说,一九九八年,那是一条快车道,有人赶上了,有人绕开了,不一定是个坏事,不一定。我看着河面的塑料浮标,饮料瓶盖穿了个孔做的,没有实际作用。舅舅说,我在湖北,跟着老张跑建材,夜晚赶路,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水像是脚底下长出来的,就一瞬间,房顶变了岛,有猫围着屋檐鬼叫,它大概理解不了为什么突然没了陆。雨没停过,我和老张弄了木筏,绑了彩色塑料瓶,看不出颜色,雨线遮盖了一切。我们循着一棵棵树,去一个个岛,什么都救,还有趴在屋顶的猪,不知道怎么上去的,匐在那儿,一动不动,被吓坏了。我和老张把木筏挂在瓦上,勉强搭住,上房撵猪,那猪太胖了,我们轮番抽它屁股,它叫都不叫,纹丝不动。老张开始踹它,我掐着它的短尾巴,它才开始往前拱两下,又猛地发起疯来,猪蹄扒瓦,头仰到天上。我没抓住。猪沿着屋檐倾下,一头栽进水里。我和老张愣在原地,看着猪往下浸,头立在水面上,接着被落雨往下摁,只剩两个鼻孔,最后是个波圈。
河面反射着阳光,波光灿灿,我好像看到一个个发光的猪鼻。舅舅一下说了很多,很流畅,健谈起来,尽量咬清每个音。我说,那后来呢?舅舅从口袋里摸出根烟,朝我递,我摆摆手,他憨厚地笑,兀自点上,继续说,接着是老张。我说,他怎么了?他吸了口烟,说,我跟他说那猪沉了,他还是跳进水里追猪,我上了木筏,拿起桨跟着他。一头猪而已,你说对吗?我点点头。他说,我们好几天没看到一个人了,这猪就是个人。老张潜进水底,比这汶河浑浊,能看见啥呢,再说能看见,一头猪,是能拎得上来的吗。天越漏越大,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风,涌来一波浪,我也掉进河里,木筏漂出老远,河面汹涌起来,四周没有地可落,像在海上。你看过海吗?我摇摇头。烟他吸了一半,丢了,说,我抱着块漂来的浮木,觉得自己像个鱼漂,周围视野涨大,但全是水,其他什么也看不见,老张没上来过,可能救到猪了,也可能被猪救走了。我问,被猪救走了?他笑起来,说,本来是下午,但又像晚上,我不知道漂了多久,不停地喝河水,发苦,这水里什么都有,稻子、木门、电视机、桌子、椅子、猪、人,天上的雨帘突然开了,有一束光打在我的脸上,特拉法玛多。我问,特拉什么?他说,特拉法玛多,那束光来自特拉法玛多,是光说的,像个滑滑梯,不过是倒着滑,把水里的东西往上吸,坡面光洁,像金子做的,向两侧散光,把雨线照得分明,我看到那些草、树、家具、农具、猪、鸡、羊、老张一并往上去了,我怕我眼花了,用手背揉眼,泪都出来了,再定睛看,老张确实拽住了那头猪的尾巴,死死地拽着,那猪像头豹子,挺起身子,踩在金光上,进了快车道,往光的尽头奔,那里是一个比太阳还要耀眼的圆球,特拉法玛多星球。他说到这里,眼睛眯成一条缝,就好像看到了什么。我顺着他的目光远眺,汶河上有条小舟,独自漂着。他说,我喊老张带上我,声音太小了,实在太小了。他扭头,张大嘴巴,伸出舌头。我看到在他满嘴黄牙的中心,是一块肥大的舌,瘫软在口腔里像一只搁浅的鱼。他微笑着,像个怪物般看着我,我咽下口水,他合住嘴巴,咳嗽了几声,又说,回吧。吐字变得生涩,松散,不再紧致。
夜里,姐姐回来了,换了件衣服,穿着短袖皮衣,左右口袋的拉链各有个银色星星吊坠。我问她去哪了。她说要你管。我大概也能猜到,来了几天,他们又接上头了,姐姐这一身行头明显是那盲流给弄的,不知道摩托车是不是换了,或者村里太空旷,没听到那骇人的引擎声。我说,我告诉妈。姐姐说,打你屁股。我在她床上翻找着,果然有那盲流带来的零食,还有盒烟。我问,他怎么找过来的?姐姐说,你小孩,不懂,距离是情感的黏合剂,万有引力。我说,你抽烟。姐姐把烟递给我,说,我偷咱舅的,味冲,你拿去还了吧。我把烟塞进短裤兜里,顺着问,姐,你知道特拉法玛多吗?姐姐说,什么玩意?我说,特拉法玛多,一束光,一个圆球,哦,地球那样。姐姐说,你今天干嘛去了,什么球的。我说,舅舅带我去钓鱼了,不是,钓舅妈去了,还说看到过一束光。姐姐把我拉到身边,凑到我耳朵边说,舅妈早就死了,我跟你说过,舅舅脑子有问题,你别离他太近,不行你就跟着我,李哥带咱俩玩就行。我说,那个盲流?她说,他叫李灿基,怎么样,时髦不?
我坐在堂屋的椅子上,腿够不着地,两条腿前后荡着玩。屋内外都是一团黑,夜已经深了,我还是睡不着。院子里有声,悉悉簌簌的,不像老鼠。我往门口走,看到舅舅在枣树上立了梯子,已经钻进了枝条里,骑在一根较粗的干上,不是在那睡觉,两个手还忙着在上面绑系一个棉麻布包,之后从布包里掏出一本书,开始翻着。我走出去,站在枣树下往上看。斑驳的月影被繁复的叶子切碎,还是会有枣掉下来。我大叫一声,枣砸到了脑袋。舅舅探头往下看,咯咯笑,让我也上来。我爬上梯子,他拽着我的手,拉了我一把,我踩上了那根最粗的枝干,如履平地,不知道是不是舅舅削过,这上面平坦,没有一处树疙瘩,勉强能挤上一大一小,布包就坠在脚底下。我们坐下来,他把书递给我,开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削弄一根细长的枝条,把叶子刮掉,试试弹性,觉得差不多了,就弯过来,用枝条围住我,说,这叫啥,知道不?我咯咯笑,说,知道,安全带。舅舅也笑起来,说,咱俩一人一个。说完他又削了根粗点的,把自己围住,另一端绑在干上。我翻看着那本书,月光太稀,看不清字,纸页皱巴巴的,好像泡过水,封面写着五号什么的。舅舅说,老张给的,是一扇门。我不明所以,坐在枣树顶,系着安全带,眼前没有多余的枝条草叶,再往远处看,月依旧圆如锅盔,暗影淋在其中,像烙糊了。夜风不时吹来,浑身凉爽,不比城里的空调差。我记起那盒烟,把它掏出来还给舅舅。舅舅说,正好。他掏出一根,火机也在里面,点上了一根,说,这是火箭。我又开始纳闷,问他,什么火箭?他拍拍屁股底下的粗干,说,这树,火箭,咱俩系好安全带,准备好。我说,准备什么?他说,特拉法玛多,就那。他指着月亮的方向继续说,月会让路,更亮的圆球显露出来,火箭从地底窜出,搭乘金光,去特拉法玛多。我听着,看舅舅脸上堆起了一沓笑,眼神泛光。远处的夜空开始低垂,大地旋转,零落的星闪烁,眼睛睁不开,我揉了揉,舅舅已经跳下了枣树,又重新拿着一根电视天线爬了上来,比对着月和星,说,到底在哪?到底,在哪?我看清了那本书的名字,五号,屠宰场。
白天,那盲流果然骑到了村子里,摩托车嘟嘟嘟空响着,他熄了火,倚着村头的电线杆等姐姐。姐姐拉着我一起去镇上的游戏厅,我有些抗拒,她说,让姐夫带你玩。我白她一眼,她和盲流哈哈笑起来。我被夹在他们中间,像个饺子馅,紧紧贴在盲流的背上,姐姐手臂绕过我搂住他。摩托车重新启动,车轮扭了几下回正,沿着乱石路往汶口镇去。
驶到水泥路面,他才开始张口,说,你舅舅就是个神经病。我说,你就是个盲流。他大笑,说,丽丽,你弟弟怎么骂我。姐姐说,他说你是盲流,不是流氓。车速太快,风兜着我们的话,能听个百分之六十。他把摩托车慢下来,又说,没人不知道的,我老家就在镇子上,张翠红在汶河漂了三天才捞了上来。我说,张翠红是谁?姐姐说,咱舅妈。一辆沙石车掠过,姐姐又说了句,舅妈。盲流继续说,洪水的事儿,捞上来面目全非,泡发了,躺在小船上,你见过丢水里的馒头吗,差不多吧,还有很大一阵臭味。赵振明从南方回来,说是也遇了洪水,拼了命活下来,没想着自己媳妇却被洪水吞了。他蹲在河岸上抽烟,一言不发,也不给钱,要知道捞尸捞了三天,起码一辆二八大杠了,两个人下了船,就站在岸上等,可能想着给家属个缓和的劲儿,缓和好了再把尸体拽上来。岸上围了一堆人,都想看看啥样,我也在那儿,骑摩托在堤坝看热闹,我烟还没点上,就看赵振明站起身子,跳上船,抱起桨,插进河里,推走了。所有人都愣住了,尤其是那两个捞尸的,这下连船都没了。那天下着小雨,河面一层雾,不出几分钟,船和人都不见了,赵振明和张翠红。姐姐叹了口气。我说,舅舅和舅妈?盲流说,一人和一泡发的尸体。我说,我才不信。姐姐说,咱妈也跟我说过,舅妈是淹死的,那年洪水面积太大了,她是个跛子,没机会跑。我说,舅舅说他弄了个木筏,和老张救一头猪,还看到一束光道,去特拉法玛多的。盲流大笑,说,你舅舅被解放军捞上来的,也算命大,挂在一棵枣树上,怀里揣着本盗版书,昏迷了好几天,手里还死命握着一个浸水的手电筒,醒来后一直嘟囔,谁也听不清在说什么,两个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几个人按住他,才有人发现他口齿不清,算半个残疾人。我说,后来呢?姐姐说,三天后,赵振明撑着船回来了,一个人,把桨抵在岸上,那两个捞尸人苦苦等了三天,往船里看,什么也没有,吓得腿都哆嗦,明明捞上来了,这会儿人又没了。我说,人去哪了?姐姐说,杀死一个死人算不算杀人犯?盲流说,还能去哪,张翠红已经死了好几天了,赵振明觉得臭,把她推河里了吧。我说,我不信。姐姐说,你不信自己去问他。盲流说,你弟弟才不敢。那俩捞尸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也不知道到底算不算捞上来了,钱都不敢要,跳上船划着跑了。摩托车拐了个弯,碾上一块石头,差点歪倒。姐姐骂了他一句,说,你把摩托都吓到了。接着俩人都笑了起来。我搂紧了盲流的腰,后颈出了细密的汗,直咽口水。
再去汶河,我还是拎着红色塑料桶,踩在田埂上,跟着舅舅。他抽烟着走在前头,钓竿搭在肩上,说,跟你姐去过镇上了。我点点头,他又说,你好像怕我了。我赶紧跟紧,说,没有。舅舅停住,回头笑着看我说,我知道你姐姐说了什么,我是个神经病,对吧。我说,没有,没有。他舒了口气,不再说话,站在那处井边,等我过了,才开始往前走。
到了那处河滩,我后来又围起来的泥坑还在,多了两处缺口,抓的小虾都跑了。我蹲下,从桶里拿出大白兔奶糖递给舅舅,他勾在鱼竿上,甩出,我就不再看他了,自顾自地蹲下。我从远处捧了几坯干土,糊在水围的缺口,两个手对住,夹稳夹紧,又开始淌水在附近扣虾。舅舅照旧抽着烟,看着河面,如有所思。我抓了一大一小,把它们放进水坑,实在太无聊了,有鱼竿却没有鱼,我又把小虾放了。从桶里摸出块奶糖,吃了起来,说,我舅妈去哪了?舅舅过一会儿才回答,就从这走的,还记得那道金光吗?我跟你说过的。我说,记得。他说,晚上,夜才会劈开,金光射下,你舅妈就从那儿走了。我说,张翠红被洪水淹死了。舅舅说,我和她在船上,汶河的夜里冷得很,我脱下衣服给她穿,她笨得很,一直哆嗦,我剥了块奶糖给她吃,她才精神起来。这个娘们,怪得很。我说,她被人捞上来了。舅舅说,她站起来活动身子,我听着她关节都出动静了,她爬上那道光就开始跑,我当时也叫她了,她回头看我,跑得极快,跛脚不跛了,像个运动员。我说,她死了三天了。舅舅说,我让她等我,她不理我,但后来说了那棵枣树,我们院子里的枣树,特拉法玛多的火箭,还记得吗?我说,那只是一棵枣树。他说,只有火箭可以刺入黑夜,把星星击碎,最终到达。我不再听他胡说,走到一边,半蹲着身子,往水里探,看到一条肥大的草鱼栖在水草底部。我轻声缓步过去,猛地扑下身子,扣住那洼水。鱼跑了,我重心不稳,跌进汶河,即刻喝了口水,那河像是有手,又把我往深处拽。我扑腾着身子,但是没劲,喝了几口水后眼睛都睁不开,直到头发全湿,我才意识到自己落水了。水草在河底摇曳,我转着身子,没有方向感,水下像是藏着黑夜,聚拢的窒息感撕扯着我,远处看到几只鱼,摆尾却能甩到我的脸颊,距离感已经消失了,浑身开始疼、指尖生凉,有什么缠住了我的脚脖子,把我往下拉,我看到舅舅的鱼钩,上面那块大白兔奶糖已经不在了,更远处,是一个人形,回了头,我看不清,是一只巨大的鱼,还是张翠红,是我自己,是死亡的具化,是舅舅,是赵振明。他把我扛在肩膀上,推出水面,我吐了几口水,咳个不停,他向前游着,把我甩到岸上,我落进自己的水坑里,像一只真正的鱼。
等我醒来,我们还在岸边,舅舅蹲着看我,眼里有大面积的泪。他又抹了几把眼角,说,我对不起你。我不敢说话,总觉得他看见的不是我。他说,为什么不跑,你这个傻子,为什么不跑。我说,舅舅。他拎着桶站起来,把所有的大白兔奶糖全部倾进河里,大喊,吃吧,你全部吃光吧,别回来了,再也别回来了。我爬起来,觉得舅舅好像疯了,我转身往回跑,浑身湿漉漉的,不敢回头,姐姐说得对,他是个神经病。
姐姐给我换了衣服,李哥问我这是咋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擦了擦头发,说我掉河里了。姐姐神情紧张,李哥说,赵振明?姐姐说,我们得回家。李哥说,不是我想的那样吧。姐姐说,你别说话,你别说。我说,不是,我抓鱼掉河里了。姐姐朝我说,你也别说话,让你远离那个神经病,你就是不听。我低着头。
母亲晚上来不了,但是姐姐一刻也不想等了,她跟李哥说好了,晚上10点过来接我们,行李箱都不要了。舅舅回来后,给我们做了些吃的,我和姐姐什么也没说,吃完就回了屋,等着夜深。引擎声响起来时,姐姐拉着我往外跑,李哥在门外大喊,快上来。这像是在玩一场逃跑的游戏,我也兴奋起来,跟着跳上摩托车的后座,又被他俩夹在中间,三个小时后,我们会回到县城,舅舅这仿佛从没来过。跑出来时,没看到舅舅,姐姐头也不回,我扭回头看了眼月亮,又下意识看了眼越过院墙的枣树。在那棵枣树的梢上,赵振明正坐在上头,用一根削光叶子的枝条绑住自己。他停住,往引擎声这里看,他看到了我,冲我喊着什么,我没听清,那声音是原始的,像最初站在飞土里的那个舅舅,残破,不可理解。李哥收起脚撑,拧转把手,摩托车全速前进。他说,坐好了,我们要飞起来了。
后来我没再去过,我姐说是舅舅推的我,母亲气坏了,我应该反驳了,应该是的,我扭过头对她说。未婚妻说,我还要跟着跪吗?我说,不用了,没办婚礼,不算过门。她又问我,你舅妈到底怎么回事。我说,九八年洪水把村子淹了,后来退了,院子里只剩了棵枣树还活着。她哦了一声。我说,明天乐乐也来。她说,你外甥。我说,李乐乐,三岁,也得叫你个舅妈。母亲不哭了,夜里只剩下了虫鸣,院子里的那棵枣树也没了踪影,听母亲说是砍掉了,谁砍的,她也说不上来,大概是舅舅吧。他正躺在棺木里,因肺部感染过世了,六十岁,狗狂吠不停,邻户敲不开门,进去时发现尸体,已经好多天了。明天上午最后瞻仰,完了下午就去火化,彻底画上句号。我说,你知道特拉法玛多是什么吗?未婚妻没有回答。我再扭头,她已经睡着了。特拉法玛多是一个星球,冯内古特书里说的,死了很多人,洪水也和战争一样,一条快车道,光打过来,一切坐上火箭。
第二天,姐姐带着乐乐来了,老李开的大奔停在村头,他早就不骑摩托车了,过了那个花哨的年代,带我姐去深圳下海经了商。我和未婚妻出去迎,老李抽着烟,打量着她,说,你小子也出息了。我笑笑,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老李谈了几个项目,赚了些钱,还投资了一家艺术展馆,最后话题又绕回来,说,赵振明,也是我舅,走了倒是解脱,那会儿你记得不,我救了你,带你跑了。我说,记得,夜里的摩托车。乐乐围着我和未婚妻转,姐姐说,我进去看看,你看过了吗?我说,没。姐姐嗯了一声,又说,走,还是看看吧。乐乐拽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叫我,舅舅,舅舅。我说,乖,乐乐乖。进了院子,姐姐问,枣树呢?我说,妈说舅舅砍了。姐姐说,死前还怪有劲的。她说完往堂屋走,母亲在里面等着,棺木往下开了一半,能看清人脸,我后退了几步,不愿看,总觉得那里不是舅舅。
未婚妻和老李一同站在大门口,那只被拴着链子的黄狗摇着尾巴蹭他们,乐乐拽着我的手。屋里放着哀乐,不好听,乐乐貌似明白了什么,安静下来,问我,舅舅,人死了去哪呢?我抬头看了看天,摸着他的后脑勺说,咱俩这儿原来有艘火箭,枣树做的,夜里飞到天上去了,另一个星球,特拉法玛多。他闪着两只大眼睛问我,什么?我笑起来,说,人死了,就会去另一个星球。他说,我才不信。
堂屋大门敞着,姐姐在棺木前跪下磕了个头,又站到一旁搀着母亲。我渐渐觉得,前几天夜里,天上劈开了一道白光,像个金黄的滑滑梯,赵振明终于等到了,坐上枣树,系上枝条做的安全带,朝着特拉法玛多飞起来,他从布包里掏出那本书,路途遥远,还可以最后重看很多遍,那已经不是书了,像某种救赎的圣经,私密的通道,精神的光。他点上根烟,也许回头了,也许没回,烟雾弥漫在半空中,没一会儿,月开始让出一条道,更远的星就要到达。
已经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