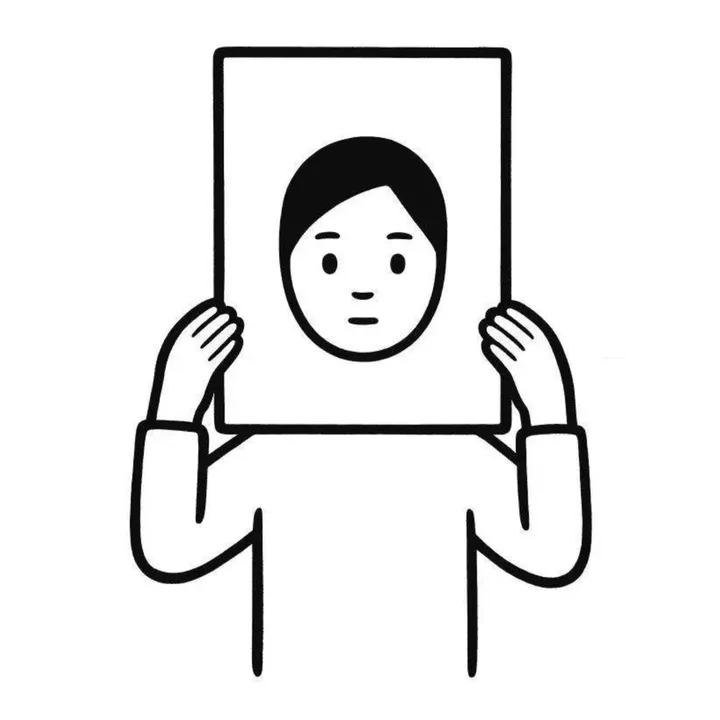热血的少年总是不计后果地出走,但当李建成从北京闯荡回来,一无所有。带着工伤的残腿他开始寻找自己的爱情。
这是一篇大多数人的故事。在东亚文化里,每个人都被教导平凡有罪,却没人考虑这个动态的变量何时得以止休。挣扎失败的我们,最终也不过是被束带缠回老家的夹缝里,低头三分地,抬头井中天。西小麦则在这篇故事里,展示了该如何挺起小人物的脊梁。
—— ONE编辑部年度推荐
1
瓜子皮在李建成手里攥着,没地儿扔,他继续嗑,瓜子皮越来越多,在掌心团成个球,湿乎乎的,分不清口水还是汗。他盯着胡丽丽,递给她些瓜子。她坐在对面椅子上,缩着脖子,大衣裹住身子,头歪向一侧,翘着二郎腿,手指弯过来扣住座椅的人造皮革。坐的人多了,皮革露了海绵,还有些没扫净的污渍,回头下来,得拿抹布挨个好好擦擦,李建成心想。胡丽丽看上去多少有些害怕,也没接他的瓜子,随着两声咣当,手指头一下戳进了海绵里。李建成抬头看了看蓝色的铁皮,说,没事儿,连杆,机械装置,马上就到顶了。
透着两侧的玻璃往下看,临西县像糊在了地面上,零星的街灯和半高不高的楼交错,水泥路和土路纵横,几辆车打出的光凝聚在微小的车头前,像贴地的萤火虫。星星近了,散着寒光。十分钟前,李建成拉着胡丽丽钻进了这蓝色的小方盒子,两排面对面的座椅,只够容纳四人,红色,黄色,绿色,总共二十四个同样构造的盒子,平均分布,挂在巨大的钢铁构架的圆周上。李建成说,摩天轮,八十九米,30层楼,我打赌你之前没坐过,我头一回坐,也是你这怂样儿,缩着脖子不敢动,现在习惯了,天天和这玩意打交道。胡丽丽扭回头说,广州啥都有。李建成说,别提广州了,你这不是也回来了吗,咱俩差不了多少,我在北京那会儿,搞建筑,水立方,鸟巢,你知道吧?胡丽丽说,知道,北京奥运会。李建成把瓜子皮塞进夹克的口袋里,继续说,我都参与了,工期紧,大伙热火朝天,干劲也足,爬上拱顶,站那钢梁上,都烙脚。揩把汗,放眼看去,都是高楼,北京是真大。胡丽丽说,那你咋回来了?李建成拍拍右腿说,后来刷外墙,让脚手架砸了,我就知道,这下好了,可以拿钱回家了。胡丽丽噗嗤笑起来,说,你这人,这玩意还有高兴的。李建成抻抻右腿,站起来,原地转了一圈,说,你看不出来吧。胡丽丽说,和好人一样。李建成额头的汗涔了出来,右腿不太利索,硬撑着走了正常的几步,又原位坐下,说,啥话呢,本来就是个好人。
相亲是父亲李德华安排的,李建成三十五了,倒是不着急找个伴,从北京回来就没什么正经工作,腿不灵活,生活就像被砍了一半,送个外卖慢半拍,老有差评,有时候解释几句,对方听也不听,总感觉他在卖惨。夜市摆摊,卖寿司,不用走路,但双手太糙,净是老茧,捏出来的好不精致,卖相难看。父亲托人安排到游乐场,小吃车轮子卡住,搬个凳子在控制台旁坐下,开关也不用操心,摩天轮转起来就是一天,速度极缓,事故率为零,送人上天后,李建成喜欢抬头看,总感觉那些骨架像是北京某一艺术建筑的雏形,自己还在首都的土地上,即将攀附高耸入云的脚手架,去焊接或是敲打,像某种苍凉而又遥远的弦击乐。摩天轮三十分钟一周,铁皮盒子升上去再下来,再升上去,有人钻进去,他就嘱咐两句。没人,他就趁着铁盒子贴地的切角,拿块抹布进去擦擦座椅,再把垃圾捡利索,一步小跳出来,重新坐到凳子上。胡丽丽这人李德华提前跟他说过,比他小几岁,二婚,之前在广州沃尔玛当营业员,想回来开个小超市,拾起在广州的老本行。李建成联系了胡丽丽,说带她来坐摩天轮。李德华在教育局上班,但跟教育没关,负责水电,认识人多,哪家办公室灯泡不亮了,哪层楼厕所水龙头不听使唤了,人们第一个想起来的总是他。不只在单位,在整个教育局宿舍片区,李德华都是被需要的人,谁家都进过,谁家都得好生伺候,楼建得早,李德华来了,坏的插座,破了的水管总能修得好。有一回,李建成听他讲,局长家里发了大水,李德华故意不慌不忙上楼,慢吞吞维修,水闸拧得比平时都慢,两个水龙头在维修包里翻找半天,又仔细比对,为的是多在局长家里待上一阵,好事后留个充足的印象。临走时,大水散去,实木地板已经有几处肉眼可见的鼓包,局长拿着一条中华递到李德华手里,说,你们也不容易。李德华将近六十的眼眶里竟然湿润了,倒不是因为一条烟,而是觉得威望一下子有了着落,有了认可。但在李建成看来,这都是虚的,水电工而已,和自己拿铁锨和水泥也没什么区别,在局长家还是在首都,也都是一个意思,待得再久,终究也不是自己的。李德华就看不惯他这一点,人穷志短,说话难听,他说,你在北京待了八年,混得个残腿,我在老刘家待了半个小时,一条中华。李德华还说,你不满意,你爸我继续给你找,怎的,还能不管你了不成。李建成其实也不挑,自己的情况自己清楚,也不藏着掖着,那样都没趣,残疾证他也有,不过拿出来说事有点卖惨占便宜吓唬人,他做不来。
咯噔一声,铁盒子升至顶点,左右摇晃了一下,胡丽丽抓紧一侧扶手,李建成说,别怕,我们到顶了,别浪费了风景,快瞅瞅。胡丽丽又往下看去。摩天轮建在临西北头,再往北,是崎岖的几拐土路连接着的临西煤矿,山头早不见了,两年前发生了严重的坍塌,埋了十几个人,至今有一半没有找到尸体。往南,是晚上九点的临西县,灯熄了大半,黑像一只饥饿的虫,啃噬着这座城。李建成指着青年路的方向说,我家在那儿,教育局宿舍,七十多平,但三室两厅,够用,就我跟我爸。又指着城边的清凉河说,那条河,小时候能一口气游个来回。胡丽丽说,现在呢?李建成说,现在?全是煤渣,舀一盆水,滤干净,能烧火。座舱开始下落,胡丽丽舒开了身子,说,你能挣多少钱?李建成说,我算过,这个大家伙转一圈,我能拿五块钱,一天下来二十来圈,一个月三千来块钱。当然,咱俩这回不算,我算偷着带你来的,这一圈,我至少得赔一百。胡丽丽笑起来。李建成接着说,你别往心里去,我乐意,带你看风景,请你看故乡。趁着胡丽丽乐呵,李建成坐了过去,靠在她身边,去摸她的手背。胡丽丽先是一惊,并没有缩回手去。李建成摸着,觉得像在摸自己的手,胡丽丽手背也糙,座舱顶小黄光洒下来,能看到指甲剪得倒是齐整。胡丽丽说,孩子得过完年接过来,幼儿园这个学期费用退不了,实在是贵。李建成猛地挺直身子,手倒还是紧紧握着,说,孩子?胡丽丽说,照片不是都发给你了吗,四岁半,男孩。李建成说,照片我倒是没看着。摩天轮开始往下落,他看着远方几处夜灯相继熄了,对李德华有些生气,可又没地撒。李德华没说实话,也没有给他看小孩的照片。李建成把手从胡丽丽手背挪开,从口袋里掏出瓜子皮给胡丽丽让了让。胡丽丽说,我前夫车祸,人没得快,没啥痛苦,那时候孩子两岁,不懂事,找了爸爸一阵儿就忘了这事了,上了幼儿园就又开始找,我跟他说,你爸爸出差还在路上,就要回来了。他问我是不是在非洲。他说非洲的时候,我问他知不知道非洲在哪,他说知道,远,非洲就是爸爸。也就是打那起,我想着得找一个了,我实话实话,有一半也是为了孩子。李建成不说话,继续往外看,晚上临走时李德华穿着西装革履,夹起工具包出的门,像个老干部替工人拎包,在眼下这些亮灯的房子里,兴许就有这个老头的身影,把西装外套往沙发上一撂,蹲在卫生间拧洗手盆下水管窄口螺丝。想到这,李建成决定把戏演完,起码给足李德华面子。他说,你也不容易,现在的小孩都精,糊弄起来比较费神。胡丽丽说,我没想着糊弄,感情我也不想凑合,前夫那里有笔赔偿金,在广州不算什么,回来,起码能开个小超市,一个人弄弄货,两个人也行,有个伴,活得能快活些。李建成说,下来了。
座舱降到底,李建成打开门,让胡丽丽快出,她迈了一步,他跟着跳了一步。蓝色座舱又缓缓升了上去,李建成再次抬头看,觉得它们都有些厚重,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这声音没有规律,连不成乐,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音,又不知疲倦地发出。胡丽丽牵起了他的手,李建成指骨一紧,胡丽丽又松开了。她说,挺好玩的,没想到咱县城还有这个玩意。李建成挪到控制台前,按下红色的按钮,庞大的机器顿时缓慢停止。胡丽丽说,乐乐要是能坐一回,准高兴坏了。李建成说,等他回来,我请他坐。胡丽丽真心高兴,李建成看得出来,她脸上堆着笑,一说到孩子,总是这副表情。他不理解,也不想理解。他说,临西正在转型,你看这游乐场,就是下半年才建好的,那边的海盗船,云霄飞车,还有大型3D电影,生命起源,恐龙危机,不过这么看,也就我这儿的摩天轮适合孩子玩,其他的,都太刺激了。胡丽丽说,咱县变化挺大的。李建成说,矿塌了,不得不转型,说是明年,就在那一片,要建个动物园,拉一头大熊猫过来,乐乐喜欢大熊猫吗?胡丽丽说,我觉得你真是个好人。
2
李建成和李德华吵了一架。
他们也没少吵架,不过这回两个人说得都很难听。李建成骑着电动车从摩天轮回来,一路上都在想胡丽丽的孩子,仿佛这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儿子。推门进去,李德华正在沙发上看晚间新闻,李建成把遥控器抓过来按死,电视画面立刻闭了。李德华说,你发什么彪?李建成说,你骗我干啥?李德华说,人家是局长家远房亲戚,她没说吗?回来开超市,局长那里,几下就给她弄好证了,你觉得这条路不够宽吗?李建成说,她有孩子了。李德华说,那不更好,我当爷爷。李建成说,你当局长得了。李德华站起来瞪着他说,当初你要是听我的,你能混成现在这个样?还弄个残腿,咱爷俩现在出门,你都追不上我!李建成把右腿踩在玻璃茶几上,哐当一声,他拍着自己的大腿说,你拿走,我把这条残腿还你。
技校毕业那年,李德华在局里跑关系,按以往的惯例,子承父业,李德华的工具包马上就能落在李建成肩膀上了。局长点了头,单位也没人反对,入职申请书都是李德华亲自写好的,又从他钱包里抽出李建成上技校时拍的一寸照贴上。这些,在技校磨锤子的李建成毫不知情,他学的机械工程,钳工,铣工,车床,锯条,花样多,最后啥也不会,不是学校的问题,是自己不上心,总想着大城市,那时候的李建成是浪漫的,不羁的,有着健全的双腿和只会做梦的脑子,一毕业就被社会所淘汰,还没毕业,就已经上了逆流漏水的小船。他说,你别管我,老子能干你那水电工吗?李德华能忍,哄着儿子去单位入职,哪怕李建成还没拿到毕业证,有关系在,李德华还是有把握的。入职那天,李建成跑去了北京,火车14个小时,绿皮,行李架也是人,李建成头一次觉得那种在仲夏夜浑身是汗的列车上奔赴的是滚烫而又炙热的未来。下了火车,有小学同学接,住首都师范大学宿舍,李建成有种恍惚,连续跟着同学去了几趟教室,在听不懂任何知识的情况下等待一次被念到名字,幻想自己是其中的一员,几天之后,名字确实被念到了,宿管阿姨查寝时总是会多一个人出来,问了他的名字,又仔细比对了名单,叫来了老师,保安,兴师动众地与其进行了谈话。文明,风度,礼仪,典雅,李建成在当天晚上都体会到了,拎起自己从家里带的背包走出了首都师范大学,同学也羞愧难当。李建成出了校门,找了一部路边电话机给李德华拨了电话,在对方在接听话的瞬间,他挂断了,并决定混出个名堂。桥洞,水泥桶子,地下室,他都住过,后来在中关村的一处民房门外遇到一名工友,带他到了一处挖埋管道的建筑工地,他才缓缓地意识到,自己除了一身力气,已经别无所有了。
李建成从不后悔,包括他的残腿,但李德华这几句话相当于扒开了他的旧伤,抠着他的断骨。李德华说,我稀罕你的腿,我不管你谁管你。李建成挺直了身子,看着李德华喘着粗气,发出嘶嘶的喉音,手掌握拳,脖颈青筋暴起,像爬上了一条幼蛇。李建成又顶起肩膀,说,我听你的,我他妈全听你的。他摔门出去,下了楼,围着几辆乱停的轿车一圈圈走。他扭头看了看车,又贴着窗玻璃往里瞧。他开不了车,右腿肌无力,踩不下去油门和刹车,只要坐在车上,就无法自己做主。从北京回来他试过一次,坐进桑塔纳里,当时车还在,是李德华的,黑色,看上去极其商务,他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买车,单位和宿舍楼的屋子,轿车开不进去,路程电动车不足十分钟,有什么意义。李德华坐在副驾驶,说,抓紧方向盘,两眼看前面,别着急,离合,挂挡,油门,前进。临西县东边没有开发,紧靠小凉河的是大片荒草地,偶有几棵树,构不成障碍,李德华已经把车停好,前面百米处是河滩,树在后头,视野里一片开阔。李德华继续说,小心踩,别冲进河里,这一片够你耍的了,试试。李建成没有驾照,头一次开车,坐在驾驶座上,浑身冒汗,他握紧方向盘,两眼直视前方,小凉河的水闪着耀眼的银光,像极了在北京站脚手架上时对面高楼大厦的反光,两种光在眼前冲突交织起来,他左脚猛踩离合,按照李德华的指示,挂上了1挡,雨刮器蹭蹭划动。过了许久,李德华说,现在滴滴很流行,别管什么车,别人要坐,你开过去接,送到位置,就能赚钱。你别光听我说,你踩油门,踩啊。李建成咽了口水,他难道不是在踩了吗,车子在离合的带动下,龟速移动,挡风玻璃上贴近了一只苍蝇,振翅摇摆了几下停住,好像在看他。李建成已经在踩了,还准备在转速飙升,引擎轰鸣时按李德华的指示换挡,他觉得他的力气完全可以让车子发出一阵狂吼,径直冲进小凉河底。李德华什么也没说,从副驾驶下来,等李建成自己下车,又坐上去。两人换了位置,回去后,李德华把车卖了,说,油耗太高了,保险又太贵。
两支烟抽完,李建成收到两条信息,他把烟丢到地上,右脚无力地踩了踩,掏出手机。微信图片点开,是一个小孩,留着规规矩矩的寸头,头真不小,手里拿着奥特曼,木讷,没有表情,看上去像个奥特曼的摆架。第二条信息写着,乐乐。李建成点开,又放大看了看,不知道怎么回,就是一小孩,长得像胡丽丽吗?他又带着这个想法看了看,回复道,长得和你挺像的。过了一会儿,月亮从云里跳了出来,远处能看到摩天轮的一廓白亮的影儿。胡丽丽写道,你还没睡。李建成这才看了看表,将近夜里十二点了,他问,乐乐跟谁睡?胡丽丽回,他姥姥还在广州。李建成没回。胡丽丽一会儿又写道,其实长得像他爸。李建成也没回,继续围着汽车转圈。胡丽丽又发来信息,你真能带他坐一回摩天轮吗?哪怕咱俩没成。李建成没犹豫,回了过去,说,真能。
李德华在沙发上睡着了,呼噜打得震天响,李建成站在客厅看了一会,去卧室拿了床毛毯,轻手给他盖上。期间李德华扭了下身子,李建成憋着气,生怕吵醒。李德华不高,2米长的沙发,腿伸直了还剩一个屁股的空,李建成灭了灯,坐在了那个空里。他想起来了早年去世的母亲,那时还没上技校,兴许母亲活着,他就不会上技校了。归咎于母亲的死,有点不孝,可是无论再说什么,母亲也回不来了。她死于肺癌,一生没抽过一根烟。医生说烟与癌没有必然联系。李建成懂,两扇肺叶和烟,脚手架和腿,都是随机的。母亲的死是随机的,她在中心医院呼吸科的26号病床,李建成记得很清,当晚他陪夜,父亲回家休息了,母亲还能说话,说些胡话,他听不太清,也听不太懂,他才十六岁,看着自己的母亲瘦骨嶙峋,像一根筷子被丢在白色的餐布上,他想拾起来,却不知道怎么用力。母亲说了很多,嘀嘀咕咕,自己擅自拿走了氧气面罩几回,又陷入沉睡。李建成回忆起来,觉得那几声嘀嘀咕咕可能是某种预言,如果他能够听懂,兴许能够阻止什么的发生。可惜的是他什么也听不懂,只能握住母亲干枯的手。母亲死后,李德华害怕起来,总是处于一种极度的恐慌,企图控制一切,而李建成则不是,他最后握着母亲的手,从温热到冰凉,觉得什么被抽走了,一种无法抗拒的意识被抽走了,不,他决定,他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左右自己,他不应该被任何人和事抽走。李建成侧头看着熟睡的李德华,他的鬓角是黑的,染得仔细,胡子剔得极净,而鼻毛多数是白色的。
3
胡丽丽的超市就选在了青年路,在路中巷口,原来是家小型理发店,老板娘将近五十,一个人剪发,前一阵儿还未成年的儿子死了,无心打理,店空了大半月。李建成知道肯定是局长给打听的,这个位置还真不错,回来进家属院,总会顺手买点什么,离家也近。胡丽丽没有家,出去好多年了,老房子本来好好的在北山底下,渣土车运煤车一进,连着挖了十年,矿山一塌,竟把自家房子砸了。再去找,谁也不认账,埋人的事儿还没有处理干净,埋房的都是小事儿。当时胡丽丽回来一次,扒拉着人群往里走,管事的站一水泥平台上,紧皱着眉头,手里拿着泡了半杯茶叶的玻璃杯,啥话也不说,像根柱子。起先人们叽叽喳喳,还想着上去拽拽他的衣角,好歹也使使劲,算是对得起自己的亡夫家属。胡丽丽在里面喊,我家房子塌了,人们歪头看她,附近的人问她,砸死了几个?胡丽丽说,房子没了。附近又有人说,我们人都没了,你算啥。李建成说,你这是参加了攀比大会。胡丽丽不吱声,继续往下讲。当天她做好登记,往塌方区走,救援早就停了,七八辆轧土机轰轰隆隆在路面来回开,这哪儿是山,像一条宽阔无比的马路,能一望无际,直通北京。胡丽丽按记忆找着自家的房子,院墙有些破损,大门用木头别着,院子里种着两排矮银杏,屋檐下都是燕子窝,最后一次回来房顶有只斜卧的黑猫,半眯着眼瞪着她。沥青碾出的灰味呛鼻,那味道像块橡皮擦,在胡丽丽脑子里来回擦拭。当时说能按回迁房算,等了大半年,啥消息也没有,前夫也是外地人,说不行回他老家,家在南方,水多,净是开鱼塘的,反正饿不着。广州,只是个打工的地儿,落不了脚。李建成觉得胡丽丽挺可怜,是同样的苦命人,听她讲了这些,决定先帮她把超市整好。
理发店的招牌被李建成三两下用锤子敲下来,弄了一头灰,胡丽丽说小心点,李建成说,好歹是干建筑的。胡丽丽没再讲,进了里屋收拾起地上的碎头发。沙发和镜子老板娘都不要了,李建成找了个收二手家具的,价格很低,胡丽丽同意了,一会儿人就来拉,一张椅子40,一面镜子带灯25,也算能回个血。胡丽丽说,地方小点,但能放两排货架。李建成说,把里屋洗头的拆了,能再放一个生活用品的。胡丽丽说,里屋得住人,货架就不摆了。李建成说也是,心里想着要不邀她去住,也就几步路,三室两厅也是浪费,但没说出口。也不是太快了,是心里没底,感情还兜不住,拿不准。
一连忙到夜里七点,店里收拾得差不多了,收家具的没来,又约了明天。灯打开后门口地上还映着永红理发店的光标,激光从头顶射出,李建成还以为是个监控,想着回头能用上。两人就坐在光圈里,几个圆弧的红字还在转动,李建成说,寓意挺好,永红。胡丽丽说,那就叫永红超市。李建成摸出一支烟说,你这涉及侵权,问题可大了。胡丽丽咯咯笑。抬头往远处看,摩天轮亮起了彩灯,交替闪烁。胡丽丽说,多像个地标,广州塔。李建成让海盗船的同事顶了个班,自己还真没从这个角度欣赏过,远远望去,半幅圆环像座城市的永动机,安稳地旋转着,推着临西,也推着自己。外卖一会儿就到了,拉面炒得有点咸,吃完了,李建成去里屋接水。突然就被人从后面环抱住,他腿站不了那么稳,猛地被人使劲,转身坐到了洗头沙发上。里屋没开灯,胡丽丽盘的头发散下来,垂在肩膀,立刻坐他身上。李建成看了看她,嘴角好像还带着红油,他伸手去揩,胡丽丽径直吻了过来,红油全被李建成的嘴唇抹净了,她又坐起身子,开始脱外套,拿住李建成的手,隔着毛衣放在自己的胸上。李建成上次还是在北京,洗脚房二楼,也是关了灯,那时候腿脚利索,浑身是劲,从工地下来衣服都没换,在洗脚房一顿折腾,弄得小妹哇哇直叫,他叫她北京,黑灯瞎火中,他抓着两个胸脯,觉得自己还握着一把铁锨柄,还没弄完,警车来了,李建成裤子都没提好,跑得极快,从二楼窗子跳到车棚上,像只猴。李建成从毛衣底下往里伸手,摸着文胸,这才真的起了兴趣,身体开始发烫。胡丽丽索性配合,站起身子,把自己脱个精光,又蹲下开始褪李建成的裤子,那东西已经如钢筋般硬挺。李建成目光瞄着门缝,门缝外是行走的人,来往的车,还在旋转的地面光圈。胡丽丽转回身,砰的一声把门紧住,光束了回去,李建成挺起了身子。
饭桌上起码有八个菜,半数是李德华自己整得,两个是胡丽丽带来的,李建成啥也不会,起了三瓶啤酒。规矩没那么多,弄得挺隆重,三人落座后,李建成觉得把胡丽丽叫到家里来是不是太快了,不过关系都发生了,也没啥可说的。李德华盯着胡丽丽可劲儿看,说,人比照片好看。胡丽丽不好意思,李建成接话说,比你高半头呢。李德华说,看你那个德行,起先咋说的,这下又咋说的。李建成把鸡肉夹到父亲碗里,说,吃肉吃肉。这次聚会也算是给胡丽丽庆祝,聚丰超市,李建成起的,在北京就经常在那买东西,回到临西,不算侵权,牌子昨天下午挂上去的。李德华问她会不会开车,胡丽丽说在广州学了,花了小四千,但是没开过。李德华说,早知道不卖了。李建成说,又提那茬。李德华咕咚咕咚喝酒,脸颊已经潮红,对着李建成说,滴滴司机就挺好的,那二手车就是给你买的,哪知道你脚使不上劲。又对着胡丽丽说,咱家人都实诚,有啥说啥,建成那腿不好使,残疾证就在屋里,不行你就看看,仔细瞅瞅,如果嫌弃,咱今天吃完明天散伙也行,不知道建成跟你说没,他那腿,走路你也能看得出来,不利索。又对着李建成说,咱老李家从不骗人,有啥说啥,过体面日子,教育局这口的,都这样儿。丽丽,你能听明白叔说的啥不?胡丽丽没搭话,李建成说,爸,你喝多了。李德华继续说,你小子是不是骗人了。他站起来,拍着李建成的大腿,俯下身子对着胡丽丽继续说,就这条,自己他娘的上北京,摔下来,砸得,还不说,回来拐着个腿,要是告诉我,我非上北京301医院,军区医院,我就不信还治不了,能留个这残疾吗?你说当爹的图个啥。胡丽丽说,叔,你坐下。建成都跟我说了,我知道他的情况。李德华被李建成按下来,说,小乐乐,以后是我孙子,上学不用愁,只要我活着一天,在这教育局里干活,上到高中都没问题。不用管学区,看上哪所学校,别不好意思,都是自己人。车你也别管,别说桑塔纳,宝马奥迪,兰博基尼。后来又说了几句,李德华恍惚得不行了,李建成扶着在卫生间吐了几口,回卧室打上了呼噜。胡丽丽问李建成,你爸是到底是干什么的?李建成说,一辈子水电工,合同的。
4
李德华死的那天,李建成在超市帮胡丽丽理货,收到消息他觉得不可能,李德华从没去过远地方干活,教育局宿舍区和单位足够他忙活的,从来不接私活。到了地方,李德华已经被盖上了白布,救护车收起了抢救设备,两个人找他签字确认。户外高压电箱坏了,李德华不知道接了谁的电话过来维修,也不知道是修好了电死的,还是没修好就电死的。李建成抬头看了看这片居民楼,窗户里亮着零星的灯,和教育局宿舍的居民楼没什么区别,又完全陌生,他从没来过这儿,也不关心这里发生的所有的事儿,在确认单上签了字,又走过去掀了掀白布,李德华浑身焦黑,身子绷得硬挺,面部呈现块块白斑,像撒上的大片珍珠。
火化用了三天,临西下了场大雨,聚丰超市斜角被雨水泡得厉害,李建成爬到二楼连夜盖塑料布,胡丽丽在屋里拣货,用大盆接水。李建成先是把伞夹在腋窝底下,风太大,伞被吹跑后,李建成脸上全是雨,一束束像刀子慢慢划拉,他忍不住了,痛哭起来。没人听见,风呼啸着,雨把什么都切断了,哭声传出去不到十厘米就弥散了。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他不知道在哭什么,上天像破了大洞的旧水管,等着李德华来修,李德华是来不了了,永远来不了了。第二天雨停了,李建成才把李德华从停尸房冰柜里拉出来,往殡仪馆送。阳光明媚,像极了桑塔纳的那天下午,几朵懒云飘在天上,秋尾的风已经寒凉,李建成可以用左脚开车,他见过短视频上,左脚先踩离合,再踩油门,踩离合,换挡,再踩油门,车子飙出去几百米,扬起的灰尘迅速模糊了挡风玻璃。哪怕他冲进小凉河里,如果再来一回,他就试着用左脚开车,让李德华死死系住安全带。来悼念的人不少,邻居大大小小都来了,他们的话语间有种莫名的焦虑,好像一致担心接下来的水电坏了该去找谁。局长也在,已经将近退休,头发白了大片,拍着李建成的肩膀说,李德华是个好人。李建成记得父亲的话,想借着问问上学的事儿,他说,领导,外地孩子上学,您能办吗?局长愣了一下,说,李德华就不该接私活。李建成哑了口,看殡仪馆烟囱飘出几缕青烟,不到三秒,隐没在了蓝色的背景里。
抱着骨灰盒回家,第一眼看向沙发,觉得李德华还在那里坐着,又看了看手里抱着的骨灰盒,觉得这几天跟开玩笑似的。胡丽丽接过骨灰盒,摆在架子上,用抹布擦了又擦。
连续几周,李建成都跟丢了魂似的,站在摩天轮底下往上看,觉得那东西高大,可怖,冰凉的寒气直逼面颊,哐当哐当细微沉闷的响声穿透耳膜,他开始感到害怕,想着摩天轮倒塌的那一天,什么都躲不过去。胡丽丽住进了家里,但话也少了,李建成下班回来,胡丽丽早把饭做好放在了餐桌上,自己就去超市坐着了。晚上九点胡丽丽闭了店再回来,李建成干坐在沙发上,她脱了大衣坐过去,轻抚他的背部。李建成穿着毛衣,吱啦吱啦起静电。胡丽丽停下手,李建成知道她在安慰她,可又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安慰的。夜里,胡丽丽和李建成并排躺着,伸手去摸他的肋骨,说,你都瘦了。李建成嗯了一声,说,往常这会儿,李德华的呼噜是最响的,总能把我吵醒。胡丽丽嗯了一声。李建成接着说,我又打听了几个同事,外地小孩得先落户,要么不好上学,乐乐五岁半,年后得上一年级,李德华已经没了,这事儿就算他活着也办不了。胡丽丽说,你别说了。李建成说,我实话跟你说了,李德华攒了不少钱,我到时候还得去找局长,我先送个五万试试,用黑色塑料袋,要不就买两瓶酒,把钱都塞进去,或者买购物卡,现在都兴购物卡。乐乐得上最好的学校,我当初要是听了李德华的,真不至于就上个技校。胡丽丽认真听着,也没回话,手从李建成胸膛上抽走。李建成侧身搂住她说,咱俩结婚吧。
胡丽丽从他身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坐在床沿上。李建成问,你咋了?胡丽丽一反常态,闷不吭声,低着头看着地板。李建成说,这都十二月了,下个月过年,我和你回去,咱把乐乐和你妈接过来,都住我这儿就行,地面不大,你别嫌弃。胡丽丽扭头看他,说,你当真的?李建成倒是有点生气,说,难道你以为我过家家呢。胡丽丽说,你看上我啥了?李建成说,不知道,说实话,在摩天轮那会,我是真没看上你,我不知道你有个孩子,我不是说讨厌孩子,总觉得不是自己的,别扭。现在又觉得,这世界上的东西,有哪个真是自己的呢,就这房子,这日子,咱也不一定说了算数。我是看开了,就我爸说的,实诚过日子就行。胡丽丽站起来,抱着胳膊走到窗户边,拉开窗帘,映着月光能看到摩天轮安静地立着,静止不动,停滞不前。她说,乐乐上不了学。李建成说,你别担心,不行我找我那小学同学,他在北京混得挺好,老家也有点关系,你怕啥。胡丽丽看着窗外叹了口气,说,乐乐是个智障。李建成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想起那张拿着奥特曼的照片,小男孩脑袋大得离谱,看着确实不太灵头,他没多想,他怎么会多想呢。胡丽丽穿好衣服,往门外走,李建成说,你去哪儿?胡丽丽停住,转回身说,我回来,也想着把这事儿忘了,从没想过要把乐乐接过来,我过我的日子,乐乐不和姥姥在一起,他奶奶看着他,我爸妈早就没了。你明白了吗?李建成心里一颤,说,那你为啥开始就说你有个孩子。胡丽丽说,我也不想骗人。李建成说,你就是个骗子。胡丽丽低头穿鞋,原地跺了跺脚,说,你说得没错,我无法面对自己,乐乐不像个孩子,他像块石头,你不明白的,总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是我自己不够狠,我早该掐死他的。胡丽丽说完走了出去,门重重地摔上。李建成穿好衣服想跟出去,但最终只是坐在沙发上抽烟,一支接着一支。
聚丰超市闭了店,从玻璃橱窗里看过去,货架积了灰,李建成进不去,钥匙之前他没要,从没觉得胡丽丽会走。李建成给胡丽丽打过电话,没人接,又发了几条短信,随便问了问,都不着调,胡丽丽不回。最后李建成写了一条,说,聚丰超市斜角漏雨已补,花了五百。又把花了五百删掉,发了过去。那天下午李建成雇了个泥瓦工,看着老师傅搭好脚手架,他躲在一边看。老师傅爬上架子,把防水材料和好,一团黑沥青似的,用刮板开始往斜角那块檐挡上抹。李建成说,比例你整对了没,刮板不能老斜着弄。老师傅说,你之前干啥的。李建成说,我在北京干工程,水立方,鸟巢,你知道不?老师傅说,北京大不大?我娃今年高中都不想考了,非得去北京,那儿就真有那么好吗?李建成没说话,看着老师傅一点点泥涂料。老师傅说,我劝不了,由他去吧,孩子也不容易,考试回回倒数,学也学不会,你有娃没?李建成点了根烟,说,还没。说完又改了口,说,有一个。老师傅说,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嘴变得真快。李建成掏出手机,又给胡丽丽发了信息,说,把乐乐接过来吧。
摩天轮运转时停过一回,李建成猜是控制机坏了,不过也就五六分钟,游客感觉不到啥,还挺高兴,高处的能多看一会儿。李建成刚打了后勤电话,还没接通,机器又自己转起来,别的没什么异样。过年下了两场雪,摩天轮歇了一个月,李建成独自去过,座舱上都是冰凌,在阳光下耀眼得很。天渐渐暖起来时,已经入了三月,游乐场重新开放,旁边的动物园也有挖掘机入场,在摩天轮上,还能看清进程,不出半年,说不定真有大熊猫。李建成去城北广场相亲角看过,这回不想找个二婚了,可总没合适的,见面不是谈房子就是谈钱,李建成有底气,房子在教育局,三室两厅,除了以后不能开车,也没什么不方便的。期间有一个,对方还不到三十岁,李建成让她说实话,为啥相中自己,他把残疾证给她看,对方不知道怎么回答。李建成总觉得不配,对方没有掏心窝子说话,也就散伙了。聚丰超市的招牌被大雪压塌了,房东收了回去,货物都处理了,现在房子空着,听说老板娘又想回来理发了。李建成心想,是啊,有什么过不去呢。
一天夜里要收工了,海盗船和过山车都断了电,李建成按下红色按钮,摩天轮缓慢停下,又熄了彩灯,同事说要捎他一程,他说想再坐会,一会自己走就行,今天正好凉快。已经五月底了。动物园的围挡拆了一半,还没有动物进场,木栅栏和水泥房子都修好了,李建成坐在凳子上,翘着二郎腿抽烟。夜风从入场口吹过来,煤味今年小了很多,北山都平整了,开发了旅游区,种满了桃树。李建成眯眼看,往这走来了两个人,一高一矮,他说,关门了,赶明儿再来吧。两人脚步没停,他站起来,皱着眉看。女人说,想坐个摩天轮,师傅,你看还行吗?李建成刚想骂,她们走进小吃车的光里,他看清了,愣了一下,女人手里牵着一个大头小孩。李建成把烟从嘴里拿下来,说,赶巧了,末班车。他重新按开红色按钮,摩天轮咔哒一声,缓缓启动。他又拨开侧面的拉杆,座舱彩灯全数亮起。李建成低头看大头小孩,说,今天没带奥特曼。小孩不说话,抬头看天,李建成顺着他的视线跟过去,摩天轮像巨大绽开的烟花,绚出层层叠叠的色彩。她们选了蓝色的座舱,女人抱小孩进去,又看了看李建成。李建成把烟头就地踩死,扒住门框,钻了进去。
大头小孩反坐在人造皮革的座椅上,紧贴着玻璃往外看,女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瓜子,递给对面的李建成,他接过来。两个大人开始嗑瓜子,李建成说,瓜子皮别乱扔。女人说,都在兜里。座舱攀升上去,连杆处两声咣当。女人说,快到顶了。李建成抬头看了看,又往外望了望,北面桃树成群,中间还有个人工湖,像颗没剥的花生。县城里修了路,东西国道贯穿,夜里车辆也多了起来,像一粒粒发光的胶囊,滑进临西的肠胃,又在尽头迅速消化。大头小孩转回身子,说,飞,我们在飞。女人摸摸他的头说,对,我们在天上。座舱到达顶点,开始左右摇晃,摩天轮闷的一声,停下来了。李建成站起来四下看,女人说,停了?李建成说,停了。大头小孩说,我们在飞。李建成又坐下说,等一会儿可能就好了。女人说,说了算数?李建成笑起来,说,算数。大头小孩站在了座椅上,说,爸爸,爸爸。女人说,别乱说。大头小孩说,我们在飞。李建成说,很可爱。女人说,我到哪儿都带着。李建成点点头。
座舱横亘在临西上空,摩天轮一动不动,钢梁上的彩灯闪烁不停,李建成看着大头孩子在女人身上乱爬,她把他拉回来,抱在腿上。大头孩子终于也安静下来,转过头和女人一起看着李建成。李建成不知道摩天轮什么时候能再转起来,他说,再等一会儿。但有些东西他们都知道,谁说了也不算数。女人说,没事儿,我们不怕,不怂。李建成笑起来,突然觉得,哪怕是摩天轮就这么停下了,也挺好的。在将近九十米的高空,他们三个在县城里,又不在县城里,在生活里,又不在生活里。李建成想说那天他是准备出门追的,乐乐没关系,他也问过,学能上,哪怕不行,他自己教,没什么大不了的。胡丽丽不该不回消息,哪怕说一句,他一定会赶到广州,陪他们过年,或者把聚丰超市开起来,盈不盈利不说,起码留着店面。他想说的还有很多,但一下子开不了口。
李建成看了看窗外,他在等待摩天轮的闷声一响,连杆装置重新启动,又静静地看着浓厚的夜像一团黑布,慢慢向他们温柔地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