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长河
我又一次听见河水的声音,那些前人后事都在蓬勃生长。
河水依旧和往日一样,保持着无尽的絮叨。学校的四周都是用水泥和砖块砌起来的,顶部还插满了破碎的啤酒瓶子,光从高处扑过来,青绿色的玻璃便把一道道闪亮的光芒映射进我们的眼中。远远望去,像是一池湖水发出亲切的问候,水深处,波光粼粼,让人神迷。水泥墙无法阻挡河声缠绕,像是寺院深处的经声,一圈一圈向远处荡去,这时,你细听便会发现河声中延绵着群鸟的鸣啼。那声音似是水面上激起的一层水花,在腾空的那一刹那便获得了空灵的加持,幽深而辽远,妙不可言。
我们便享受着这自然的音乐度过了最为欢快的中学生活。河水再往前走的时候,遇到一个崖壁,河水拗不过崖壁,便在这里拐了个弯,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水潭,水潭之下潜藏着一股旋涡的力量,很难通过肉眼辨别。顺着崖壁朝上望去,先是看到几棵碗粗的核桃树,一场雨水过后,露骨而又新鲜。再一细看,学校的围墙到崖壁上这一截就断了,树影的背后是一排十间平房,左边两间房的房顶高出一截。外人看了,便明白是拿这排房子当另一层意义上的围墙了。树下堆着煤炭,码成圆形的坎子,像是平排的八座坟墓,又像是八个黑色浓稠的句号。这十间房,便是学校的“商业中心”了。每间房的大门都是一扇漆了红色的木门,门中间画了一个大大的圈,圈中的白色阿拉伯数字从1升到10。左边两间房是商店,后面八间房都是食堂,经营者都是学校里老师的家属,几乎都是男人教书,女人做饭,到了饭点老师下课以后再到食堂帮忙。一早一晚卖菜夹馍和肉夹馍。菜夹馍五毛钱,夹的是酸菜辣子洋芋丝;肉夹馍一块钱,夹的是肥瘦相间的农家腊肉和涪陵榨菜,配上一勺醇厚的肉汤。再到后来,又开始经营米线,一块钱一碗,配上熬好的汤汁,外加两片绿叶菜烫熟即食,要比卖馍简单,轻松。
前年回老家,我在镇上的客运站买票,却发现窗口里坐着的是邹老师的媳妇,我跟她打招呼,她已经想不起我是谁了。我说,我在学校上高中的时候办过文学社,出过报纸,还刊登过邹老师的古体诗呢。她笑笑掩饰着尴尬,我记得那阵子,他们家做的肉夹馍最香,生意最好。邹老师教历史,喜欢写毛笔字,课间拿出一沓陈旧的报纸,一行行端庄雅致的小楷便活灵活现。报纸浊黄,那些字带着潮湿,像是河里的鱼片刻便能游荡起来。
我问她怎么不干了,她说镇上高中撤销了,学校重新盖了食堂,加上年龄也大了,腰椎不好,找个清闲的活路度日就好了。
我记得上初中那会,学校饭菜也比较便宜。一顿饭一块钱,除了镇上的孩子,其他人基本要寄宿,一个星期的饭钱就是九块钱,可以一次性付清,也可按顿支付。两者各有优劣:如果是一次性付清,则可以避免中途生活费丢失的风险,没有挨饿的可能,缺点在于个人自由支配的灵活度降低,只能在一家吃到底;按顿支付灵活度比较高,可自由选择,但风险是自控能力较差的人,可能到了周三就花光了,要挨饿。在学校里饿一两天其实也无关紧要,但对内心的打击却不容小觑。当所有人都去食堂吃饭的时候,你只能默默在教室里枯坐或者喝一顿凉水充饥,还不敢轻易运动,要留存体力周五走回家。当然也有挨不住饿的,可以向老师求助或者问同学借,但脸皮薄的人往往拉不下这个面子来。
初一,我就为此挨过饿。国庆节后的一个星期三,山里落了一场雨,天晴过后,山岚的颜色便不再是单一的青色了,黄和红搅动到满山跳跃,这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油画大师的影子。不过是一两天的时间,山中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这天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中午放学后有两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初中三年我几乎每天放学后都泡在水泥墙内的乒乓球案子上。我虽然个子小,但是动作灵活,抽、拉、抵、挡、劈、切、晃、挑、摆、点,样样精通,同龄人自是不消说了,就连一些高中生也不是我的对手。打得正是激烈之时,背上沁出黏糊糊的汗液,我把衣服一脱,往案子后面的瓷砖花坛上一扔,衣服正好落在一棵刚修剪过的矮树上。等到晚上我回到宿舍,右手往衣服口袋里摸的时候,里面早已空空如也。我当时心一惊,一阵酥麻从胸口向四周跑过去,鼻尖也慢慢渗出一层汗珠。世界一下子变得安静下来了,我能清楚听见自己的呼吸声,我在怀疑刚刚的真实性,于是又将手伸进去,还是什么都没有。我开始慌神了,左手掏左边的口袋,两手把大腿两侧的裤子口袋也翻出来,还是空空如也。我心想完了,这下糟了。
饿第一顿的时候,中午放学后同学喊我一起去吃饭,我假装不舒服趴在桌子上睡觉。那会儿其实还不算太饿,不知是饥饿还是其他原因,我趴在桌子上竟然很快睡着了。在梦中,我回到了家中,母亲请人来杀年猪,锅里煮着热气腾腾的美食。我还纳闷,正想问母亲怎么这么早就要准备过年了,母亲却斥责我才星期四怎么就逃学回来了?我一时之间也慌张起来,我无法自圆其说。就在这时,一个同学的声音穿透进来,我揉揉眼睛才发现,是同学之间在嬉戏打闹。饥饿感顿时涌了上来,肚子里空空的,我带着恶狠狠的眼光望向他,而他一脸无辜地看着我。下午上到第二节课的时候,我的肚子就开始唱歌了,我几次欲向同桌借钱买点吃的,可始终无法张开嘴巴。坐的时间太久了,我起身朝门外的栏杆走去,却感觉眼前一阵眩晕,铺天盖地的黑暗袭来。我强制让自己镇定下来,摇晃的身子终于能够按照大脑的指令行动了。我靠在水泥和钢筋砌成的栏杆上,阳光绵绵地垂下来,它像是一位母亲一样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颊、皮肤和毛发,我像是从冰窖里逃出的叫花子,那一刻,阳光的味道和食物一样芬芳。我翕动鼻翼,浅浅地将这气息迅速装满整个腹部,我竟然感觉自己又吃饱了。
上课铃声又一次响起,我带着满足而又疲惫的心境走进了教室。刚刚在室外积攒的那点温度就像装在身上的火炉,在失去了柴火之后又一次靠近了寒冷。老师在讲台上说话,那声音时而缥缈时而鼓荡,像是细雨斜织,大风过境。我从未觉得时间会过得如此之慢,仿佛每一秒钟被切割成无数个小段,而那一小段还在继续分裂,没有尽头也没有希望。我的肚子又一次叫了,它接二连三地发出提问引起了同学们的哈哈大笑。老师扶了扶眼镜,朝我这边望来,我愧疚地低下头来,刚刚冰下去的脸颊像是泼了一大勺辣子油。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熬过那漫长的一节课,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所有人都离开了教室,而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我只好和他们一起下了楼,他们往食堂的方向涌动,我只好走到水龙头跟前,扭动开关,洗了洗手。凛冽的冰冷漫过手背时竟然有了一定的灼热感,我把头仰起来,像一个杯子一样朝水龙头递过去,凉水顺着我的咽喉落入肠道,很快就填满了我的肚子。一种无法言喻的力量在我的心头升起,我感觉自己又饱了,下脚有力了。下了晚自习以后,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河水声从窗户里灌进来,身体内部的河流与之呼应,激荡。我觉得应该是我下午凉水喝得有点多,它来回晃动,肚子上像是绑了一个未被装满的水壶。
我是被尿憋醒的,河水的声音在黑夜中变得急切。我从大通铺里钻出被窝,穿上衣服,从宿舍走到厕所。厕所在室外背阴的地方,人说这里以前是乱葬岗,迁坟以后才建的学校。月光铺在地上,糯软,人踩上去,影子就从后方钻出来。借着朦胧的月光,周围的杂草和山石都像是获得一种灵气,加上自己的想象,它们似乎都活过来了,在微风中摇曳。我越想越害怕,心脏上面似是被人架起了一面鼓,一直响个不停。我不敢向四周望去,更不敢打量身边的事物,只好低着头鼓着劲往前走去。双脚一左一右,竟走出了一条歪歪扭扭的曲线来。推开厕所的木门,吱呀的尾音拖得老长,让我后背发凉。我站定位置,身体里的河流倾斜而下,真是一条完美的曲线,身体里晃动的水声消失了。
终于熬到星期五,我赶在天黑之前爬上了庙沟的山顶。那晚,我吃着母亲煮的苞谷糊糊配上酸辣白菜,味道好极了。我甚至觉得那应该是我童年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饭了,它将让我铭记终生,它用教训教会了我成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丢过钱。
上初二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邹老师因为岳父病重便不再担任班主任,那会儿老师们也不用坐班,上完课摩托车一轰就消失在大街上,留下一串青烟在风中逃窜。接替邹老师的人是贾老师,他是学化学的,教我们生物。那年,贾老师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县里的招考以第一名的成绩分到我们学校。贾老师一看就没有教学经验,脸上写满了腼腆。学生们就喜欢欺负他,他说话有点结巴,声音小,不像是邹老师还没有上楼学生们就规矩了。
有一次,上早自习的时候,贾老师让某个同学站在走廊里,那位同学不听他的,便上演了贾老师和他在教室的过道里你追我赶的场面,甚是热闹,如同赶集。班里人跟看戏一样,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怪异的笑容。事情最后是怎么结束的,我的脑海里已经没了印象。直到多年以后,我在帕米尔高原支教的时候在教室里追着塔吉克族学生,由于缺氧,两眼冒着金光,从教学楼追到操场上最终把学生说服后,我才恍然明白当初贾老师的不易。
快二十年过去了,上大学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贾老师的任何消息。之所以提到贾老师,是因为某种程度上我跟他有点像,不太会懂得拒绝别人。到镇上上学的人大部分离家都比较远,偶尔便会发生和我一样的丢钱事件。或许大家觉得贾老师为人谦和,有求必应。于是,有同学开始向贾老师借钱。贾老师可能也是没经验,也不让学生写个借条什么的,随便糊弄两句就把钱给学生了。于是,大家都听说贾老师那里的钱好借,这就像是在大坝边上开了一道口子,河水便会源源不断地灌进来。越来越多的人问贾老师借钱,不光是我们班的学生借,其他班的学生也跟着借,要知道他当时带着整整一个年级的生物课,七个班,三百多号学生,哪里经得起这么借?就是一座金库也会被搬空!贾老师最后把自己弄得跟我一样挨饿,于是他抹不开面子就问邹老师借钱。邹老师就觉得很奇怪,一个刚刚才参加工作而且才发了工资的老师竟然没钱吃饭了,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闻所未闻。后来,邹老师在班里发了一顿火,明确强调不许跟贾老师借钱,凡是借钱了的赶紧归还,否则他就要上点颜色看看。哪些人借了钱,哪些人还了,哪些人没还,我想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有一次,我跑到学校对面的一座山上玩。回来的时候,刚走到大桥头上就听见铃声,等我到操场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十几分钟。上那节课的是一位极严厉的老师,我害怕遭到他的惩罚和训斥,走到操场前的校门口便止步不前,于是顺着小路下到河里,捡起一块石子朝水中扔去,石子在水上跳舞,像是穿针引线,牵起了整个河道。就在我满心欢悦,为翘课而沾沾自喜之时,我发现教师公寓五楼的阳台上赫然站着一个人,白衬衣,戴着眼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以为贾老师发现了我,我的大脑高速地运转着,想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毕竟为了爬山而迟到,这对于大山之中的老师来说实在难以置信。很快,我就发现他并不是在看我,而是望着远处的山。只是,他一直对着那山看了半个多钟头,我很好奇他究竟在想什么。其实,他就是一座移动的山。
最后一次和贾老师打交道是在中考前夕,那阵可能迫于某种危机,我开始秉烛夜读,他巡查时发现教室里有火光,推门发现我在复习物理,我清楚地记得他还问我会不会做。上大学以后,春节前的同学聚会,我们仍会聊起贾老师来,可是没有人知道他调往何处了。我们说他的时候还是笑哈哈的,可笑声过后却又是满心的难过。
下课铃声响的时候,学生们从四层楼左中右三个方向的楼梯朝平房涌去,人头攒动,像是大坝泄洪一般涌向了食堂。狭窄的房间自然无法容纳那么多的学生,我们在队伍里把洋瓷碗递给打饭的师傅。食堂里一顿饭一般两个菜——一个荤菜,一个素菜,说是荤菜也就是一个大锅里零星有几片肉,有味儿就足矣。饭菜都装在洋瓷碗里,先打米饭再添几勺菜,米饭到碗口填平,叠上一层洋芋片或者锅贴豆腐。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捡几个肉丁。饭吃到一半的位置,菜便吃完了,这时食堂里饭菜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我们便跟进去,灶上放着一个大铁锅,锅里是菜汤,一人一大铁勺。菜汤是白菜剁碎了加开水煮的,有盐无油,倒也能泡着把剩下的饭顺畅地送到肠胃里。
食堂前有一片空地,空地上建了两个长条形的花坛,花坛的一侧是羽毛球场,并没有人打球。网子早已掉色,水泥面上画的线,白色的漆已经翻起来被风吹跑,隐隐能看见曾经的印记。
我们端着饭碗,三五成群蹲在花坛的四周,零星散落的米粒便迎来许多麻雀,人走过去它们也不害怕。吃完了掉在地上的米粒,麻雀们就站在网子上,左右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这时,学生中便有人朝空中扔出去一块土豆片,麻雀们有如泼出去的水一般,在空中迅速接住,啄食着土豆片。有同学故意撒米粒逗鸟儿玩,逗得急了,胆子大的,也敢到碗里来夺食,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这样的场景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了。久而久之,那群麻雀似乎能听懂学校里的铃声了,赶着饭点儿就来了,肚子也变得圆鼓鼓的。饭毕,便四散而飞。我们与麻雀似乎建立了某种契约关系,它们按时而来,准时而归。有鸟相伴,越来越多的喜鹊和布谷鸟加入进来,有一阵还有过路的鸽子俯冲下来,脚上绑着两个红色的圈圈,有时它们的声音甚至盖过了崖壁下的河水声。
我们有时去得早便坐在食堂里面的长条板凳上,或者端着碗蹲在食堂后面的树下,在崖壁之上,水声蒙着一层水汽氤氲而至,像是另外一个长者正在滔滔布道。食堂做得不太好吃或者胃口不佳的时候,我们便将剩饭剩菜从高空倒入河中,那米粒便随风沉到了潭底,菜叶也被水中的生物消解。
我吃过饭后就泡在乒乓球案子前走不动路了,稍稍掌控不好力度,乒乓球便飞到水泥墙外的坡地上。我站在花坛的台阶上,看见坡面上落了好几个乒乓球,于是从操场外的小路下去,一路沿着河中浮出水面的石头向坡地行进,回来的时候口袋里就装了五六个乒乓球,又够玩一阵子的了。往回走的时候,我路过崖壁下的水潭,能清晰地看见水中有鱼儿游动,身形又粗又黑,见人便钻到石头缝中。远处有几个房子大的石头竖在河谷中,有好几个女生坐在上面,似在背书,奇怪的是,人在河中却听不见河声。风穿过我的腰间,也把她们的读书声吹散了。
我记得学校那年来了一个诗人,他带的学生比我们低一级。每天饭后,校园广播里都播放着他写的文章,隐隐记得都是关于海子的。山中交通落后,信息闭塞,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上有一个叫海子的诗人,并且年纪轻轻就卧轨自杀了。但是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迅速在校园走红。学生们自然无法理解诗人之死,听人说他在课堂上讲海子,老泪纵横,把学生娃娃们都讲得掩面而泣。巨大的哭泣声吓坏了校领导,他们围在教室外面,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问其原因,原来是讲海子呢。后来,诗人便把课堂搬到河边,学生们四处散落,高声诵读,而这一举动引起了更多的围观者。一时之间,“诗人”这一词汇成为飘在学校上头的话题。四年后,诗人被调至县教体局,半年后进入县委工作,几年以前再进一步留在了市委办公室。他走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他骑着摩托车驮着行李,酷似远行的侠客,这或许就是诗人的气质吧。
十二年前,我带着录取通知书和村上开的贫困户证明以及一大堆复印材料到县教体局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所有资料齐全,工作人员要求必须有监护人陪同并且当面按手印才能办理。排队轮到我的时候,无论我怎么解释,工作人员就是不松口。我只好带着一堆资料从里面走出来,这时却遇见了诗人。我实言相告,父亲在外务工,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母亲在家要照看年幼的弟弟还有牲畜和庄稼,实在是脱不开身。诗人把我带到他同事跟前,好说歹说,最后才同意让诗人为我担保放贷。随后我便启程北上,一路向西,穿过漫长的河西走廊,抵达西域边陲之地。
那几年,我们之间并没有过多的联系。人人都羡慕诗人一路仕途向上,可在我看来,他逐渐变得谨慎稳重,所有的才情因大量的公务来往而搁置。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写文学作品了,反倒是经手的公文已经堆积成山。短短数年之间,他经历了婚姻的破裂,再到重组家庭,为了改善生活,也曾让父母到县城客运站盘下生意,可是时代在进步,原先的经营模式已经行不通。没赚上钱,还受了不少的气,算是给房东白白打了两年工,后来父母又回去种茶,可电商如火如荼,终究没能成事。受伤的老两口,心如死灰,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人,他们实在学不会城里人的那套说辞,学不会与人周旋。他们只好钻进山林里,与蜜蜂为伴,这来自山水间的甜蜜事业反而迎来了春天,为诗人一地鸡毛的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据说,蜜蜂居住的地方也有一条河,还有个美丽的名字——香河。听着河水声,采着山间的野花,正如清代诗人郑珍的诗一般:又看蜂酿蜜,万蕊同一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也有自己喜欢的生活。人世浮沉,不经历风浪如何得见彩虹。当然,也有人更喜欢平平淡淡、柔软而舒适的生活。学校旁边的那条河流奔涌而粗野,恨不得一夜之间将所有的石头送走。而城里的汉江几乎是没有水声的,它的平静足够掩藏底部的暗流。诗人与他父母的生活似乎掉了个,久在樊笼里的他最向往的就是父辈的生活,他们之间像是隔了一条河,眼看触手可及却又总是难以抵达。
有一年,路过县城,我借宿在诗人家里。房子是他到县城以后贷款新买的,在一个菜市场旁的顶楼。他还是骑着当年在学校的那款摩托车,轰隆之声穿过街道。住在这里大概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意思,其实是我想多了,房价便宜而已。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起自己的一位远房表亲在县医院治病,病人的子女也不管老人,把人撂在医院就回山里了,没有一个孩子去看望。诗人专程跑到医院,送了水果,还给老人留下了两千多块钱,他说,恐怕这辈子也无法忘记老人的眼神。
人心幽微,而他依旧保持着足够的朴素与善良。我从诗人的脸上获取了从容,但我看见更多的是迷茫而舒适,那个在校园里头也不回,大跨步走路的青年再也看不到了。相比从容,我更喜欢那种生涩的真诚,并不是说诗人现在不够真诚,而是我见过他最具体、最真实的样子。我们喝了几杯啤酒,彼此都不是嗜酒之人,点到为止。诗人说起,那几年,他在学校里教书,游遍了周边的山山水水,碰到谁的学生家里有人“老”了(方言,去世的意思),他还会上个礼,拿出个本本和乡民们围坐在火炉旁,专门记录孝歌的歌词。他说,诗的形式就是巫术,歌就是要唱出来,人“老”了以后唱的孝歌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为人与魂灵而歌。在那一刻,我再次确认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那天晚上,我的思绪又回到久违的学生时代。我又一次听见河水的声音,那些前人后事都在蓬勃生长。
|
点击 快速访问「ONE · 一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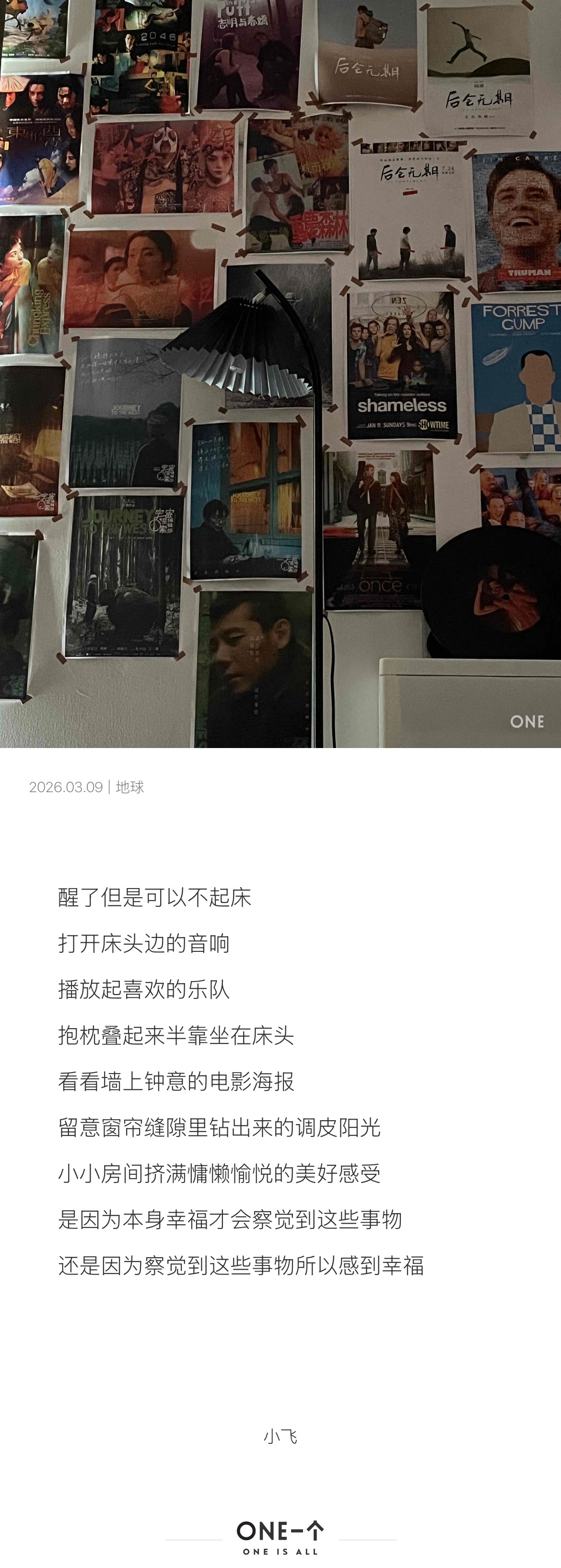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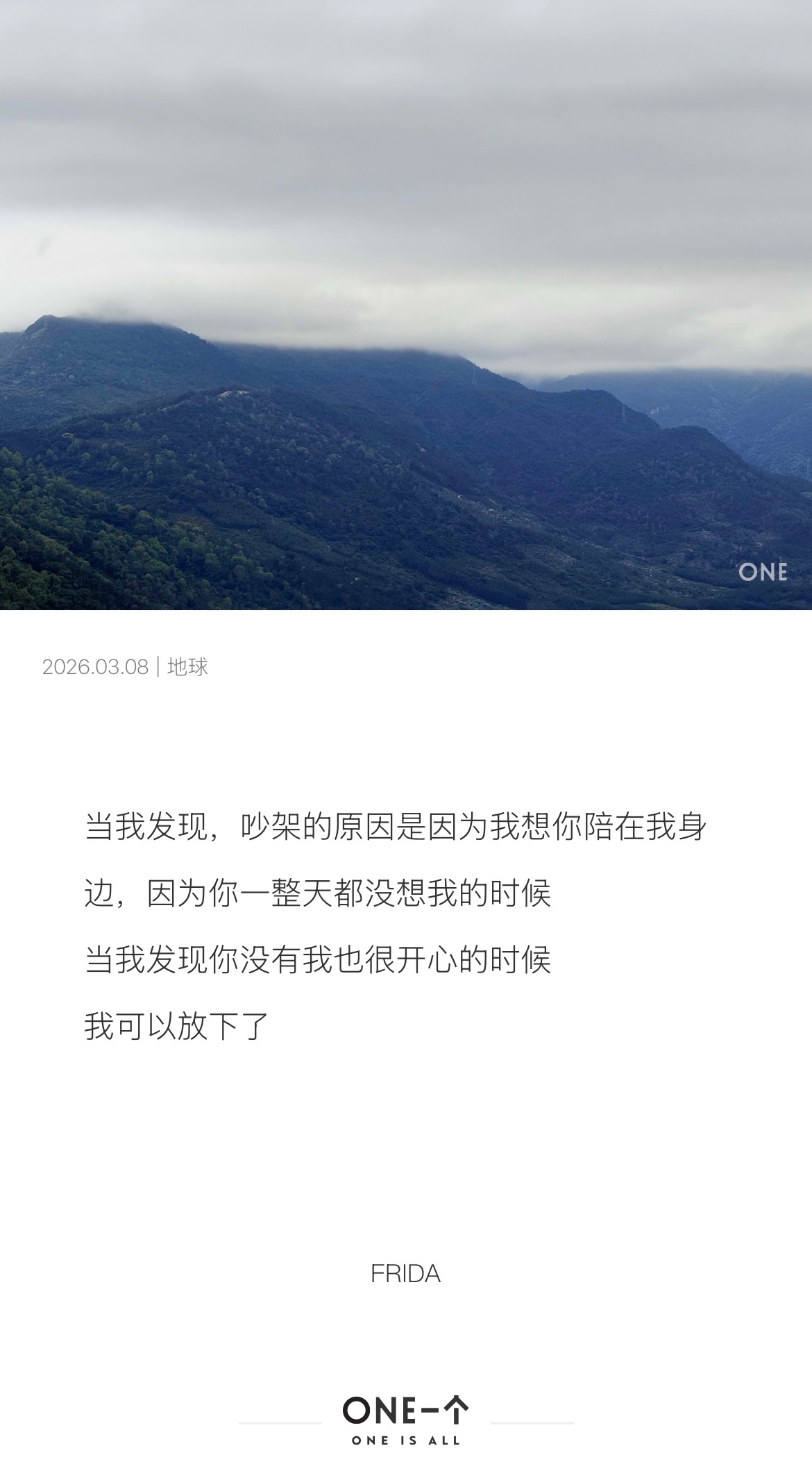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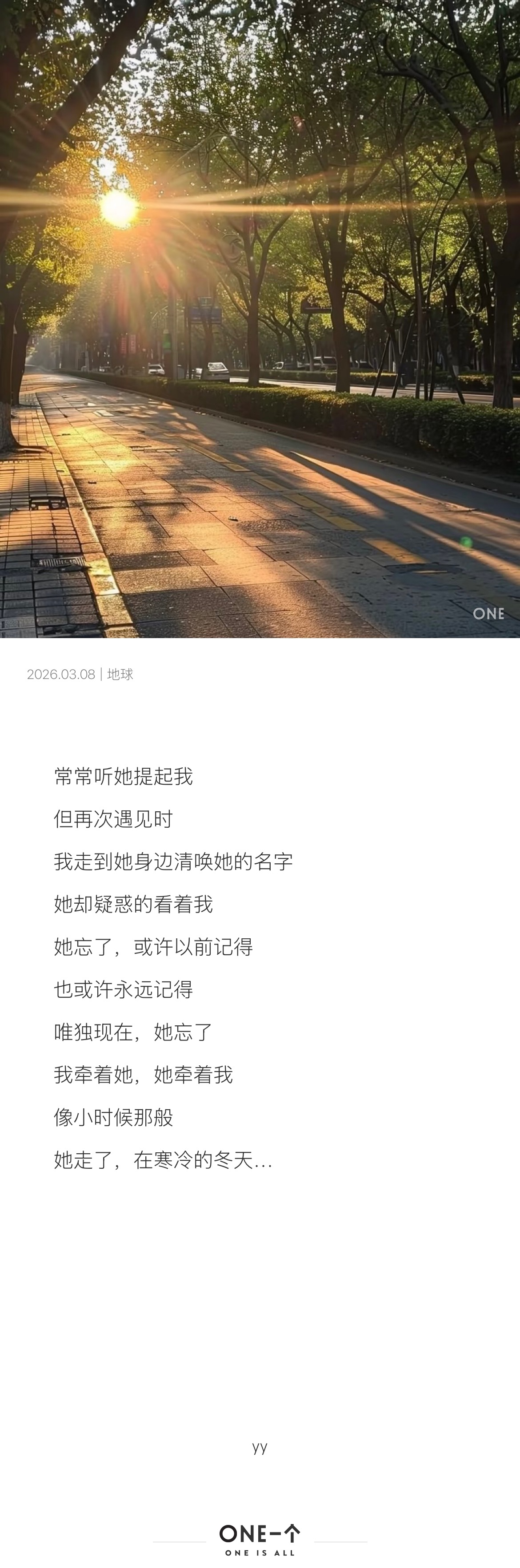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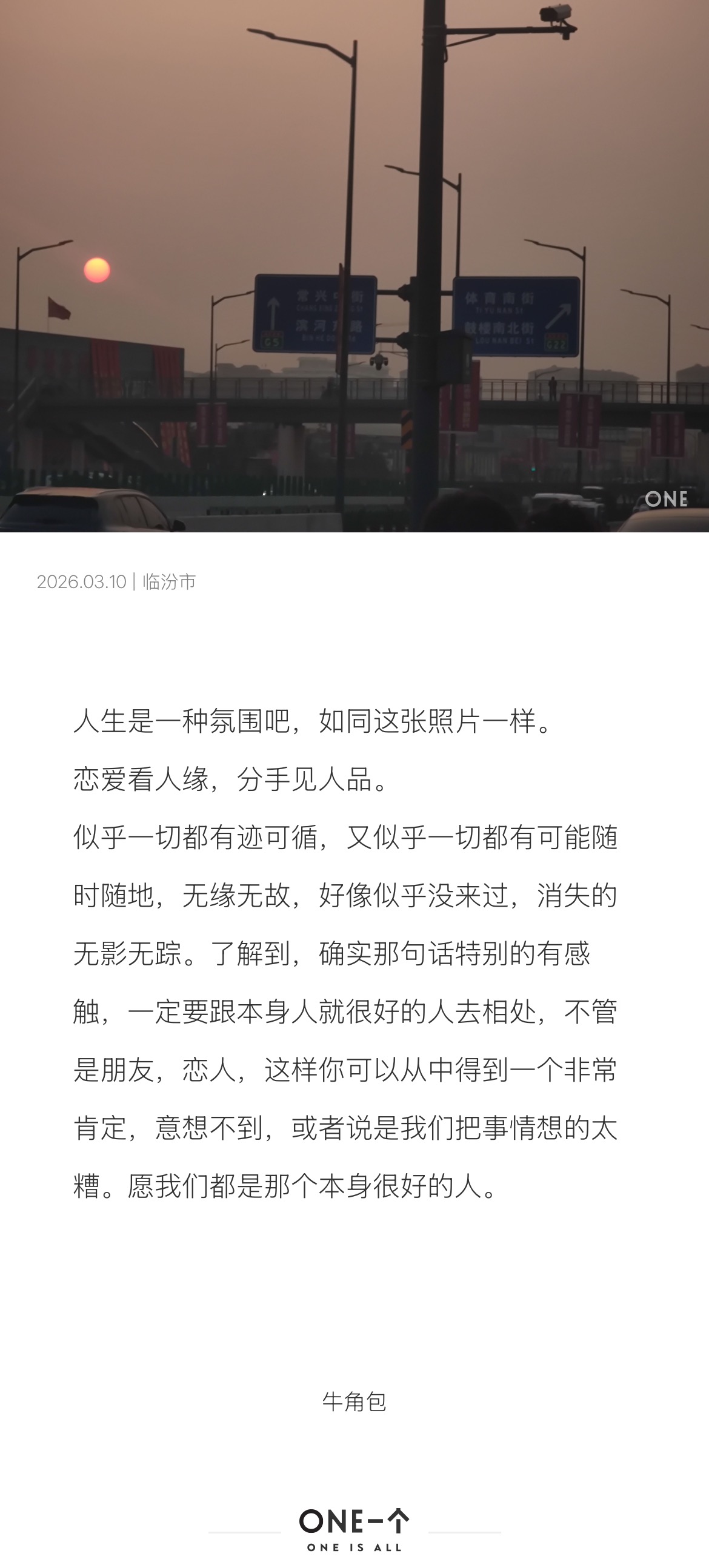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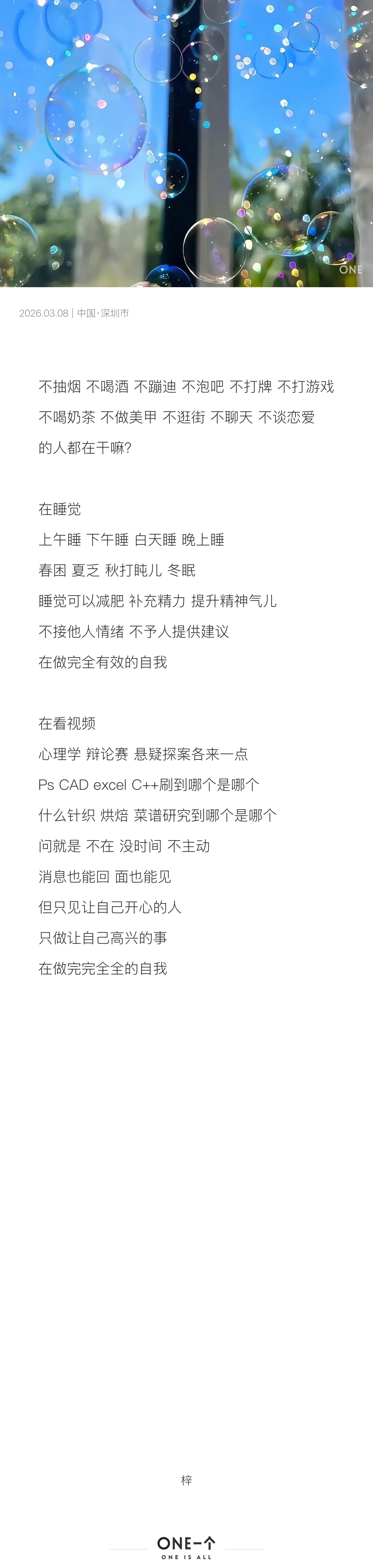
 →添加到主屏幕
→添加到主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