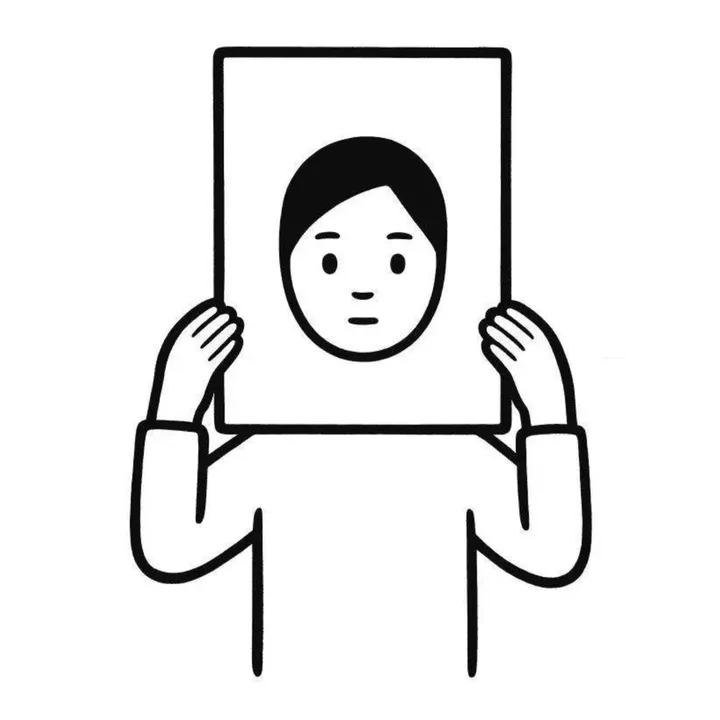二〇〇二年,我十五岁,在林校操场放飞过一个风筝,燕子形,夜市买的,十五块,绳子太短,下午两点和魏洁一起刚把它腾空起来,两点十分,绳子断了,燕子彻底飞走。我们站在原地,看它越升越高,跃过操场对面大酒店的屋顶,不见了。我收回绳子,连手圈一块还给她。她气急败坏,捶我胸口,拳小,力度不足,软绵绵的,说,你刚送我的礼物。那时候还没有这些小拳拳的烂梗,只觉得她颇为可爱。魏洁出生于一九八九年九月,处女座,小我半年,我是射手。她经常研究星座,说射手座是花心大萝卜,能一次处好几个女朋友,我调侃她说处女座真是处女吗,她哑口无言。对于十五岁的这种玩笑自己还没有成人后的那种猥琐感,男男女女之间更多的是一种青涩到底的纯洁,处女和处女座对我来说,还仅仅只是一种说辞,没有太多的言外之意。她说,自己特别爱干净,喜欢整洁,甚至有点强迫症,处女座大概都是。我看看自己拿着风筝的袖口,满是油渍,索性弯回四根手指将其挡住。我们最终坐在操场的看台上,在聊完星座之后,我对她表白,我说得直接,没有任何套路。我说,你真漂亮,我喜欢你。她没有迟疑,说,我也是。我问她,也是什么。她说,你傻啊,我也喜欢你。她扔下手里仅剩的风筝线圈,拉紧我的手。我看着线圈一层层顺着台阶滚落,线头仍旧留在脚下,扯开的线缓慢拉长,安静地割开了大地。
那个下午格外漫长,直到手心都是汗,谁也没想到要松开对方。我问她关于杨凯的事,她一遍遍澄清,好像那个名字是一种背叛,杨凯在追她,但她不会答应,因为他总是拿袖子抹自己的鼻涕。我又把袖口藏得紧了一些。魏洁问我,你躲什么。我说,没什么。我妈早上炸油条的时候我会帮忙,在教场街和傅公街交叉口,我们四点多就出门,支好摊子,一口大油锅,一个面板,半袋子面粉。有时候四点半就有人了,赶上岱庙城墙修缮的工程,戴安全帽的人比较多。等我妈弄好了面团,拉成扁长状,我就开始拿夹子下油锅。干到六点半,面粉几乎都让我妈团完,我就开始往学校跑,因为校服出门就穿好了,袖口总是会弄上些油,但我从不用袖子抹鼻涕,也不知道怎么跟魏洁解释,还好她没看到。我补充说,杨凯学习挺好的,我比不上他。魏洁说,以后放学就在这,我给你补功课。我笑了,说,我抄作业行,其他不好说。她又捶我。我问,听你的,补到什么时候?她拉我站起来,看了看远处暗红色的晚霞,说,补到燕子飞回来。
林校操场年前就封闭了,裂口的塑胶跑道常年无人管理,随着风吹日晒,雨雪浇灌变得满目疮痍,从马路对面打眼一看,像无数将要饿死的雏鸟张嘴对着天空。我带女儿去过一回,把她扛在肩头,跟她说,爸爸以前在这练跑步,抄作业,还放过风筝。女儿一脸不屑,说这破地都是坑,没有幼儿园的操场好。我把她放下来,她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根小木棍,照着塑料跑道的一处裂口扒了起来,没一会儿便玩得不亦乐乎。现在的小孩,童心都被刻意的价值观掩住了。因为穿得薄,女儿直流鼻涕,我摸口袋,除了手机,什么也没拿。看着她不停地吸溜鼻子,我蹲下,拿袖子给她抹了一把。也是在这个时候,我重又想起了魏洁。初中毕业,她考上了一中,我在二流中学,距离七八公里,开始我会在每天晚饭的两个小时骑自行车找她,背包里总是会带着两块五买的菠萝面包,二流中学最出名而又好吃的自产面包。不到半年,她吃着面包对我说,她觉得学习是比一切都重要的,她的父母指望她考上重点大学出人头地。我全明白了,推着自行车往回走,晚自习没上,一直把自行车推到林校操场,坐在台阶上看天空,月亮是一把镰刀,总感觉那个燕子形的风筝还在上面,什么也没有结束,但就这么结束了。第二天我妈没出摊,一早就被叫到学校,从办公室出来,我妈就说了一句话,以后你别跟我炸油条了。我就站在办公室门口一把鼻涕一把泪,我伸出袖子,只抹了眼泪。
女儿叫我,我低头看。她从大裂口里拽出一块布,撕不动,我让她躲开,我两手使劲,把它完整地扯了出来。是一个燕子形的风筝,没有龙骨,只剩了残破的布,暗淡发黄。女儿兴奋地大叫,是风筝,风筝。我站起来,把它展开,说,是小燕子风筝。女儿跳着问我,爸爸,能飞吗?我笑了笑,说,能,等着。我拿着风筝跑上了看台,手里拿着燕子的脖颈儿,从最高一阶往下跑,女儿在操场上拍手看我。我跑到最低一阶时跳起身子,把那块破布扔到了天上,有一瞬间,它遮盖了冬日的太阳,像极了二十一年前的那个下午,可是它不会永远飞走,总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提前落地,变得真实而又残酷。在风筝落地的那一刻,女儿说,真的飞起来了,好漂亮。我把她抱起来,笑了笑,用袖子再次抹掉她温润的鼻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