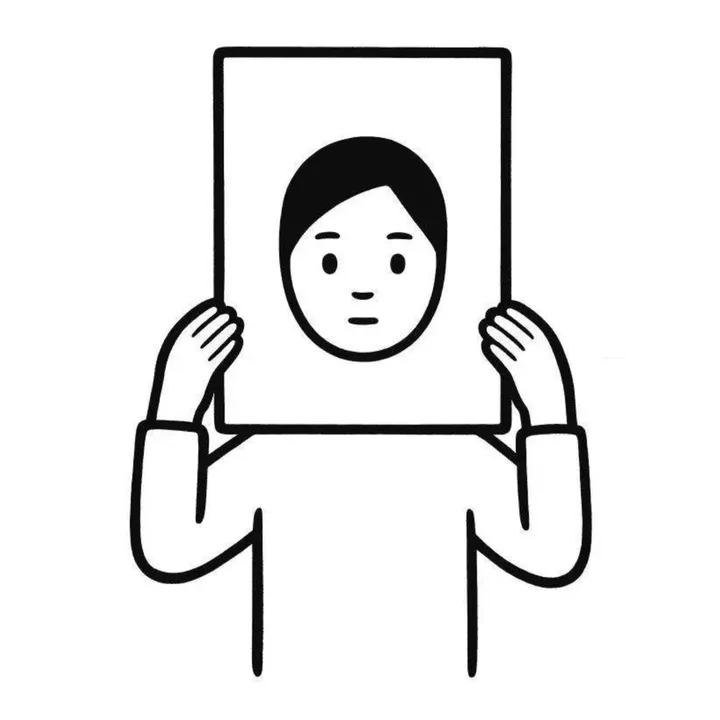因机缘的网络联系,已婚男人认识了神秘女人。婚姻对这些人如同海底作业,需要暂时脱离呼吸新鲜空气。西小麦在本文运用大量的环境、琐事和对话来塑造每个人迷茫又心安的处境,带入浸入人物的立场去感受。平淡平凡又想要波澜,每个人就这样被红白瑰刺钉在十字架,供人审视。
他准备买两份汉堡套餐,但是加冰可乐未免太凉,那就不加冰,反正刚才吃了很多盒装小西瓜,都是她外卖点来的,彼此应该不太渴,干脆就单点,她只是说有些饿了,语气中满含抱怨,于是他自告奋勇,从床上爬起来,下楼去买点吃的。
这一片儿他不熟,她详细地用手机地图指给他看,这里、那里、红绿灯、人民广场、解放碑,听上去只需要拐几个弯,并不远。原本酒店楼下就有个小吃街,一排米线牛肉粉麻辣烫,但是凌晨一点半应该只有肯德基还在开门。她也不确定,她说她不常来,但是他看得出她在撒谎,酒店WIFI自动连接,卫生间花洒冷热装反她也不奇怪,他没有戳穿的欲望,距离天亮还有很早,他买完吃的回来他们还有大把的时间进行交流,在不睡觉的前提下,当然他并没有打算睡觉。
出门前,他问她去不去,她在床上翻了个身,拍了拍从被子里裸露出的大腿,那两根大腿纤细得要命,和她的小腿一致,先前他压上去的时候上下抚摸,只觉得像是摁住了谁的脚脖子。他是太粗暴,毕竟她太瘦了,一顿折腾,弄疼了她,扯到了筋,扭伤了胯,都是有可能的,总之下不了床。他给她找着理由,尽可能理解她,理解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他突然觉得可笑,他对她说,你可真懒。她哈哈大笑,手肘抵着往床头爬,那里有她的黑色长方形手包,上面布满菱形格子,他认出了牌子,是三宅一生的,他老婆也有,上个月吵架前他花三千五百块买给她的。她从里面捏出一根烟,他不喜欢抽烟,但是假装也有这个需求,和她要了一根。她递给他,按开打火机,捧着火苗给他点上。然后背靠床帮,抱起胳膊,调整好抽烟的姿势,打开电视机,频道里有些电影点播,有一些是他们在豆瓣里火热讨论过的。他看着仍旧在被子外的那条大腿,想开口嘱咐她穿点衣服,一会儿他要敲门,房门在走廊尽头,是最隐蔽的一个,但是门框的吊顶有个黑色监控,他怕她的裸体被拍到。他不能有如此多而细致的体贴和关心,完全没这个必要,他用力嘬了口烟让她看见,她微笑着回应,选中了一部欧洲电影,在切瑟尔沙滩上。出了门,他就把仅吸了一口的烟丢进了贴紧走廊墙壁的垃圾桶里。
路上的行人像是瞬间蒸发掉的,办理入住时街道两旁熙熙攘攘,他惊讶于这个小县城的繁华,她像个导游一般止不住地介绍自己的家乡。她欢迎他的到来,他像是空投的一枚惊喜的种子,正步步往更深处扎根。重新打量空荡的城市,路灯射出昏黄的光线,笼络着他若隐若现的影子。它跟着他,匍伏在一块块所有城市人行道都一个模样的暗粉色地砖上。他有些恍惚,像一个普通晚饭后的散步,他略走快了一些,老婆牵着那只喜欢在草丛里大便的金毛乐乐,再走几步,来自老婆的指责就会跟上来,他并没有真的不管不顾。他回头,马路尽头一辆陌生牌照的出租车驶来,向他按了按喇叭,湘J,他这才缓过神来。他看了眼手机,一点五十分,他打开地图输入肯德基,最近的需要1.3公里。尽管她已经用手指给他演示过了详细的路线,他也并不信任,他向来谁都不信任,只是嘴上说着,好的,好的。
他走出小吃街,路过一家金店,一家小超市,一家水果店,站在了十字路口。根据导航的提示,他应该朝着左上方走,对角线的马路边有一家如家酒店,黄色的招牌极为醒目。他和老婆出门旅游的时候经常住如家酒店,因为价格相对便宜,可以把更多的经济投入到游玩中,买买当地的特产,关键是当地的啤酒,他岳父喜欢喝啤酒,号称要在这辈子喝遍全国特色啤酒,老婆和他一直在帮忙实现,他也觉得很有意义,每次出差,也还会想到啤酒的事。也许明天飞回去之前,他会在机场超市买上两瓶当地特色啤酒寄回去,他宽慰着自己,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挺好的。老婆其他方面算是节省,还偷偷存了一笔钱,也不能说是偷偷,她会暗示她有一些钱,是留给以后怎么,怎么的,听上去是些过分现实落地的未雨绸缪,还买了一些保险,老人重疾,安心意外,包括自己经常在外的出差险,他也总是一脸期待地点头,参与感十足,尽管他根本不想以后的事儿,并且觉得没什么意义,老婆把该想的早都想好了。他们在如家酒店不会做爱,在她看来,那就是个休息的地儿,玩了一天落落脚,好第二天继续去一些网红打卡地游玩。她甚至备着旅行睡袋,床上一铺,往里一钻。她说你知道这个床上睡了什么样的人吗,睡过多少人吗,你怎么知道热水壶里有没有煮过内裤?他点头,附和着她,他的附和几乎成为了他的性格。老婆睡后,他在睡袋旁辗转反侧,看着如蚕蛹般缚住自己的女人,身子莫名火烈起来,他爬下床,去卫生间坐在马桶上,焦躁地搜索小视频,一些露骨的画面,擦边的暗示,激起他言不出来的憋闷。磨砂玻璃的隔断,粉色的瓷砖,瓷砖上残留的水珠,粗重又克制的喘气声,他很快完事,关掉手机,闭上眼睛,幻想床上躺着另一个女人,沉浸在高潮后几分钟的余波里。随后,他蹑脚走回去,爬上床,假装睡得比睡袋里的她还早,发出呼噜声。
手机蹦出语音提示,请在此掉头,然后直行五百米。他已经走过了刚才的十字路口,站在如家酒店门前,倾着身子往里看,女服务员在前台低着头整理些什么,他们之间隔着一道厚厚的玻璃门。他想了想,推门进去,站在服务台前。女服务员不漂亮,但妆容很精致,像是夜班前刚化的,但他们看上去都一样,让人记不住,大概是制服的原因。女服务员问他有什么需要的,房间剩得不多了,只有一间大床房和一间标间。他似乎忘了自己出来是要干什么的了,他又把目光从玻璃门内透出去,望向十字路口,问她,你们的烧水壶里,会煮内裤吗?女服务员一下尴尬起来,不知所措,无法回答,她似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其实他也没有,他扭回头看着酒店尽头电梯屏显的红色数字正在变化,4,3,2,1,门打开,并没有人。
她发信息过来,问他到哪了,她快饿死了。他才继续朝肯德基走,女服务员欢迎他下次光临,他突然觉得老婆说的可能是对的,因为刚才女服务员那种尴尬的表情表明了事情的真实性。他也庆幸自己没有图便宜,他现在住的是弗尔曼酒店,楼高三十层,小丽在第十七层走廊尽头的房间里躺着,没穿衣服,等着他买回汉堡。
他们在豆瓣小组里认识的,那个小组的名字叫睡不着你在干吗,他进去的时候不需要审核,小丽正在发疯,一条条主题地发,他好奇她如此爆裂的情绪,在一条条主题后面耐心地回复,只是出于好奇,她竟然在网络上用一个睡不着夜晚的时间把自己袒露无疑。小丽,二十七岁,三线城市的小县城,经历了一场恶心的恋爱关系,以男方嫖娼为结局,视情感为看不见的生理顽疾,她在睡不着的夜晚尝试给自己开刀,投资一家倒闭的酒吧,有一窝后院小狗,勉强可以供给吃穿。他加上她好友,她意外打来语音电话,把男人骂了一顿,他只是听,并没有任何非分之想。那时的他,还仍旧在努力挤进老婆裹身的睡袋里,试图占据一处温暖的方寸。
他给小丽回复了信息,就快到了。她回复过来,你刚才去如家干吗?他猛地一惊,慌乱地点开手机,查找我的朋友,小丽的头像在弗尔曼酒店立体标志的上方悬着。这是他主动提议的,方便他下了飞机找她,他冷静下来回复,我去上了个厕所。她回复,哦。他想好了,如果她再追问,他就去找那个女服务员,让她作证,他在如家酒店里什么都没做,他没有人在那儿,没有另外的人了,但是小丽没再回复。是啊,她怎么可能像他老婆那样。他安下心来继续往前走,并给小丽接着发信息,两个牛肉汉堡,一份大薯,一个玉米杯,可乐伤身,我看看有没有卖水的。他继续走了几步,信息回了过来,小丽说,随便你。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他和老婆都在上学,打听到学校里选拔志愿者,可以去奥运会场。她没去过北京,觉得机会难得,托他帮忙,他问了家里在学校当老师的亲戚,选拔标准可以变动,但是身高是硬性条件。他回复她,遗憾间,关系也熟络起来。她长得不高,但很活泼,总是像个鸟一样蹦跶。假期他们去当游客,他陪她转,水立方、鸟巢、五棵松体育馆,一直转到深夜。他们兴奋地结束一天的行程,住回胡同的小旅馆里,小旅馆已经是最好的标准了。她当时并不在乎烧水壶里装过什么,立马喝下半壶,然后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他木讷地站着,好像要参加什么运动,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过来吧,她说,当不了志愿者,那我们就当远动员。他被她逗笑了,浑身突然发起痒来,立马爬上床去。
他没再想下去,他有点讨厌那种历史长河里的黏腻又熟悉的感觉。他现在周遭的环境没有任何亲切感,目光所及的陌生正一点点吞噬他的原生感受,他不应该再想起什么之前的事,大脑里属于原来世界记忆的部分就该宕机,彻彻底底宕机。
肯德基里还有不少人,他站在三个年轻人后面排队,距离上次来买快餐,大概十年了,结婚后他老婆不允许他吃这些。前面的人挪一步,他挪一步。轮到他时,服务员示意他可以用手机点餐,他抬头看了看电子屏幕的数字,被告知那叫出餐码。他惊讶地看着,他问服务员,这里的肯德基这么高级吗?服务员说,全国的都是一样的。他收起惊讶,觉得自己刚才很土。他幻想了一下,如果自己生活在这里,他希望天天吃肯德基,就当下的感受,他是愉悦的。他要的餐已经打包好了,可乐换成了珍珠奶茶。他给小丽发了个信息,他说,已经买好了,马上回去。
他快步往回走,这一路比刚才熟悉,街道在脑子里已经建模,他的步伐变得沉稳又疾速,路过如家酒店时,他看也没看。
门打开时,她确实没穿衣服,赤条条地站着,上下打量着他,让他这个穿着衣服的反而觉得很尴尬。我以为你坐飞机回去了,她打趣说。他笑了笑,我舍不得。你还想干吗?她说。他想了想说,我还想干。她哈哈笑起来,接过打包袋转身往床边走。她的屁股窄小,皮肤白皙,背部轮廓清晰,骨感十足。他跟上去拍了拍她的屁股,她扭回头白了他一眼。
他们没在一起正式吃过饭,他也不是来吃饭的,他们彼此都明白,吃饭不过是补充能量,保持激情罢了。他现在突然想进一步了解她。那个语音电话以后,她把所有主题都删掉了,他再问起那些零碎的现实生活,她就说自己当时喝了酒,编的故事而已。越是神秘,就越具有无穷的吸引力,他看她坐在床边,把双腿拧在一起像两条蛇,夹角处一小团黑,两个尖形胸部上翘。她喝了口奶茶,想说点什么,但没有,接着吃了根薯条。电影已经播放过半,男女主角正在吵架,他们隔着千里看过多次,相爱的人终究分道扬镳,爱情的肿瘤是治愈不了的。你到底叫什么?他问。问题抛得直接,真实姓名像把不堪的钥匙,能互相扭开对方。小丽咽下薯条说,我叫胡丽丽,怎么,你要娶我吗?他没想到她会这么说,他说,是啊。我彩礼很贵的,她说。一顿肯德基够不够?他问。胡倩把薯条捏起来扔到他身上。他仿佛看见她笑了,他们都知道这是扯淡的,他又想,谁知道她有没有老公。
他安静地等她,她吃了很多,两个汉堡都吃完了。他什么也没吃,他不饿,他等得越来越焦躁,她看出来了,把床铺整了一下,想拉他躺下,期间还拿出两根烟,但是没点。她一直不穿衣服,他一直盯着,多少觉得有些看腻了。他把眼神转到她的脸上,陌生感就来了,他看着她的刘海和眼睛,她的鼻子和嘴巴,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完全没见过,他刚才只顾着发泄根本不太在意她到底长什么样。现在,他边脱着衣服边盯着她的脸,开始认真看。许久,他得出一个结论,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被这个结论吓到了。你有老婆的吧?她问。他浑身一抖,裤子又好像是在往上穿。谁有那玩意,他立马回答。她咯咯笑起来,那你谈过几个?这个问题他很拿手,他就和他老婆谈过一个,但是他在社交平台上总是会说七八个吧,然后编一堆浪漫、悲哀、可怜和令人困顿的桥段,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很单纯,他的经历过于简单,简单到让他自己变得虚假起来。他说,七八个吧,女人而已。胡丽丽咯咯笑起来,你这个骗子,她指着他的裤裆说。
他有些生气,他脑子里在编造一系列的名字,用来佐证他拥有过的七八个女人是真实的,他甚至都给他们编好了职业,护士、医生、教师、公务员、街道办事处新进职工、网约车司机等。但是他似乎发现她怀疑的不是这个,他不想继续了。那我走,他说。好啊,那你走,她说。他穿好衣服,站在床前。她点上其中的一支烟,夹在手指头之间。他们都看着烟头在燃,烟雾妖娆着飘散。他舍不得,他嘟囔了几个不成形的词,把穿好的衣服脱下,冲了上去。要打一场硬仗,他下定决心。
和前一次一样,他自我感觉良好,胡丽丽提不起兴致,过后的两个人有些生闷。他主动从她三宅一生的手包里掏烟,然后倚在床头上抽,刚才手指头感觉被硌到,他又重新回去掏,拿出了她的身份证。她叫王丽,比他小七岁。她抢过身份证说,你干吗!他说,不干了,累了。
他能猜到她是个骗子,没有表现的过于惊讶,他其实无所谓她叫什么,他又不和她结婚。当然他自己也是个骗子,他觉得这样真累,他想了想问她,你和别人来过这个酒店吗?她说,没有。他接着问,这个酒店里的烧水壶不会煮内裤吧?她笑着说,你想什么呢。这会儿,他已经给自己点上了烟,又递给王丽一根,说,起码还有个丽字。王丽呵呵笑,说,我搜过你,老婆在机关上班,朝九晚五,倒是你,到处跑,也没什么太大的业绩。他说,你当初楚楚可怜,我还真信了的。王丽说,谁不是楚楚可怜呢。他继续说,狗是真的,男友嫖娼是假的。王丽说,狗是假的,猫是真的,男友嫖娼是假的,前夫嫖娼是真的。他拿烟把碰了碰王丽手指里夹着的烟,说,没有酒,将就吧。西尔莎罗南在海滩上正和男友做最后一次争吵,风团把雾携来,海浪瑟缩,阵阵鼓闷。王丽关掉电视机,把争吵彻底停在海岸上。她说,我们一起看了多少部电影?他没有摸出手机打开豆瓣确认,随口说,大概六十多部。王丽说,八十七部,有两部没看完,你说临时开会,我猜你老婆找你。他没有回话。房间内只有烟头的火光明灭着,像两颗悬在空中的星。王丽继续说,假就假下去,哪有那么多意义可说,过了今天,也就过了今天,也只是过了今天。这一点他表示同意,看着靠在床头的王丽,觉得她渐渐立体起来,但这种打碎陌生随之而来的恐惧感又迅速膨胀。
抽完这支烟,他走进卫生间关上门,隔音效果出奇的好,他打开花洒,坐在马桶上。这个酒店的卫生间装修风格很冷峻,墙壁是灰色带暗纹的瓷砖,花洒和水龙头一律是黑色的,浴巾和毛巾搭在支架上,他们至今仍未使用,干净整洁。他听着哗啦啦的水声闭上眼睛,想着另一个女人躺在门外的床上,这个女人也是从模糊到立体,又变得模糊,最终他意外地想到了他的老婆,浑身一惊,睁开眼睛,看了眼手机,三点二十六分,他才发觉自己已经很累了,想爬回床上睡一会儿。继续点开手机,是老婆傍晚发来的几条信息,那会儿他的飞机还没落地,他想着回复几句,内容还没想好,就这样睡着了。
再醒来,他已经躺到了床上,王丽穿好衣服在镜子前打扮自己,她涂了口红,扑了粉,正在给自己带隐形眼镜,她把一只眼皮撑起来,眼珠子在里面圆滚滚的,他看着有点害怕。你干吗去?他问她。上班啊,难道你养我啊,她说。她穿上衣服后不显得特别单薄,还有些充实,她现在是一个实体的人了,他的结论更加坚定,她甚至还有点好看,他说不出来,不是化妆不化妆的区别,大概是年龄的问题,他想。他睡了一觉,脑子清醒了一些,他说,你现在是不是我的人了?她扭过头说,你又想什么呢?
他往后抽了下身子,靠在床头上看她,在他的感受里还是挺愉悦的,他在想办法把这种愉悦感长久保持下去,唯一的办法可能就是离婚了。他有这个念头后竟然首先想到的还是他的岳父,他想他还是会在旅行的时候买酒的,再给他送到家里去,会不会很幼稚,他自我怀疑。从他只谈过一次恋爱来说,他是不会主动考虑离婚这件事的,他概念里没有分手这种说法,他完全无法应对,但是他现在被陌生吸拽着,他一点也不想回去。他只是想到了保持愉悦感的办法,但并不一定真的执行这种办法,他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自私,于是对她说,在哪上班,我送你。王丽当然是拒绝的,他没有再问。
天亮了,她在刻意保持距离,冷淡了许多,她总是看手机。他从被子里钻出来,从后面抱住她,她哎呀了一声试图推开。他感受到某种不耐烦的情绪,莫名其妙地哭了。
她看到他的眼泪,才耐下心来,低着头看他。你这是什么意思?她说。眼泪太廉价了,尤其在两个骗子身上,她莫名的冷静。他其实也说不清楚,好像一旦她走了,他就决堤了,可是为什么决堤呢?他十年来没哭过了,外壳早就坚硬无比,情绪稳定像个百年王八,历来让人觉得镇定,可靠。突然间,就完蛋了。他搂紧她的身子,把她箍进胸膛里,他是想再和她做一次?他想到和老婆做爱是半年前了,她会计划好日子,把自己清洗一遍,再把他清洗一遍,把床单被罩铺好,仿佛某个宗教仪式一般,只能在固定的垫子上活动。期间,她会提醒他是否越界,那些体液是否会不自然地倾出去,他神经紧张,又像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也不知道哪天开始就这样了,还是从开始一直这样,他说不清。又或者是她骗了他?她不叫王丽,连身份证也是假的,她没有什么工作,她准备去下一个酒店,这仿佛就是她的工作,他不喜欢,他希望她能找一份正经的工作,不能太累,她实在太瘦了,做苦力,搬什么东西都不可能。他可以下班接她,每天都接她,一起去吃肯德基,这里的肯德基是手机点餐的,出餐码跃现电子屏上,不到两分钟服务员就可以备好餐,他感到神奇。再或者是,这不是他的城市,他不认识街角卖豆腐脑的大妈,他不知道这里的苹果多少钱一斤,有几个可以遛弯的公园,坐几路公交车可以到商业中心看一场电影,这里的房价多少,他是不是可以买得起另一栋房子。
想到这,他像自己融进了她的生活里,像一个犯了错的婴儿,用尽力气在啜泣。她俯下身子把他的眼泪吻走了。他站起来,去咬她的嘴唇,她没有拒绝,弄了他一脸口红。他们都笑起来了。她重新补了妆,说,上班要迟到了,从这里走,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到,他得放她走了。他让她说,她爱他。她咯咯笑起来,好像哄小孩似地说了两回。他心满意足。他下定决心了,他要离婚,从蚕蛹般的裹尸袋里爬出来。
王丽走后,他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他分不清这种亲近和离开的冲突是哪里来的,但就是要去做。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开始掌控自己,他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此时的王丽在脑子里又变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开始失焦。他上飞机前,给王丽发信息,让她等他,她没有回复,他过分的热情久久未能散去。
他回去后的几天,一直在做计划,老婆在等着他去接,他忘了他们之前因为什么吵架,她回了娘家。不过这不重要了,王丽的热情在减退,他有些着急,他短信发过去,她两个小时后才回,不温不火。他的情绪很乱,在屋里踱步,他学会了抽烟,一根接着一根,他想明天去把老婆接回来,不,不是接回来,是谈一谈,他迫不及待。
他给王丽打了电话,她没接,他看了看手机,又是午夜十二点了,也许她已经睡了。他还没想好怎么跟老婆说,不行他就摊牌,告诉她他和王丽做爱的事,他这么想着,觉得有些自豪,他知道这种情绪不对,但是抑制不住。他试图躺下睡觉,但失眠袭来,他打开手机豆瓣,群组还在,他在王丽新发的几条主题后还是挨个留言,但是意外发现有人早就跟帖了,她用俏皮的口吻与那人回复,他熄掉屏幕。胃里咕噜起来,他饿了,于是出门找吃的,想到了肯德基。他在手机地图里搜索,最近的一家1.8公里,这里他很熟悉,他手动调整路线,把距离缩短为1.1公里,他出门了。
他想好了,要买两个牛肉汉堡,一份大薯条,一个玉米杯,一杯奶茶,他上次什么也没吃,这回要吃个够。路上他继续给王丽打电话,嘟了几声没有人接,点开信息,十分钟前收到回复,王丽说在加班,明天再联系。他低头看着人行道的瓷砖,安下心来,得过且过,生活不过如此。等明天把想法跟王丽说说,不会太久,他知道手续怎么办,那些睡不着的夜晚他都查过,王丽也曾经试探过,界限在哪,彼此也都清楚,生活即将重新开始,豆瓣和网络终究要落到实处,他体会过实处,王丽的身子骨是软的,她同样不期待但积极的态度确实在无形中感染他,他决定就明天,把什么都摊开来。
肯德基里只有两个人在吃饭,他走到柜台前,服务员给他示意手机点餐,他说,全国都这样了啊!他的语气没有一点惊讶,倒是很骄傲。服务员点点头说,是的。他打开点餐软件,和点餐软件放在一起的是查找我的朋友,他下意识点进去,看到小丽的头像在那家他去过的如家酒店上方悬挂着。他关掉软件重再进入,头像还在那。
愣了几秒,服务员说,先生,要不要我帮您操作。他小声嘀咕,你说,烧水壶里会煮内裤吗?服务员皱起眉毛前探着身子,没听清他说什么,但还是礼貌地回复说,是的,先生,全国都这样了。他回过神,咯咯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