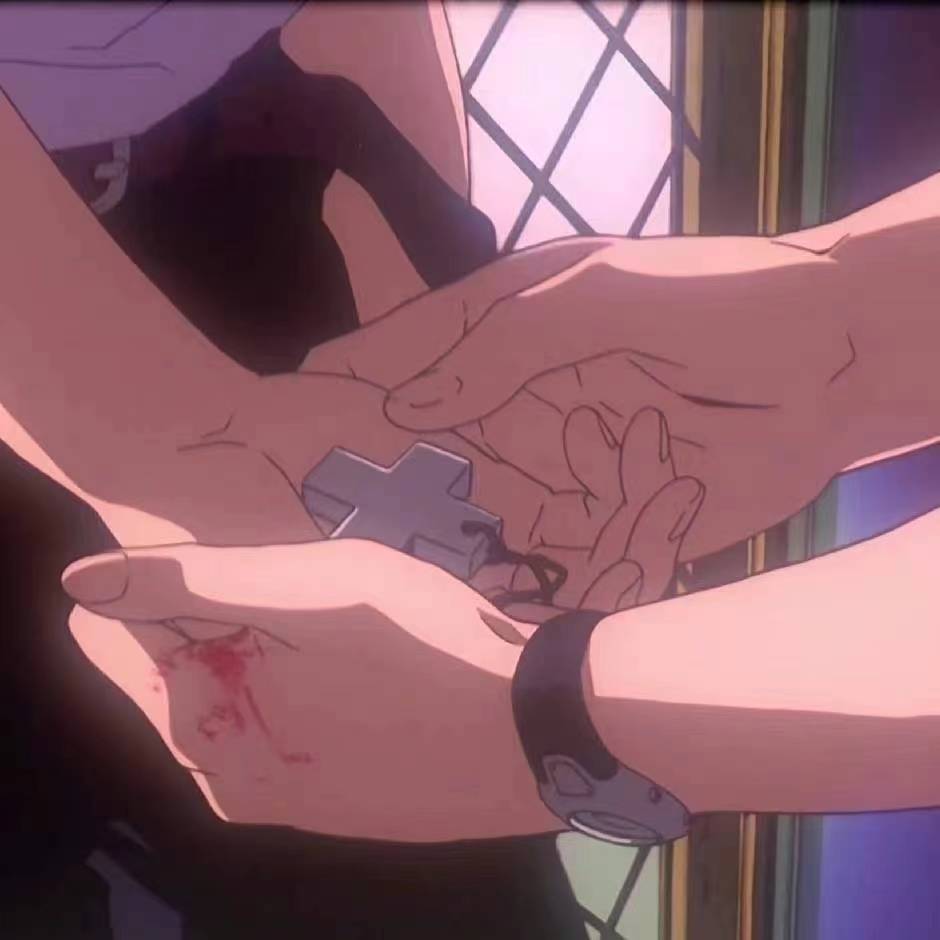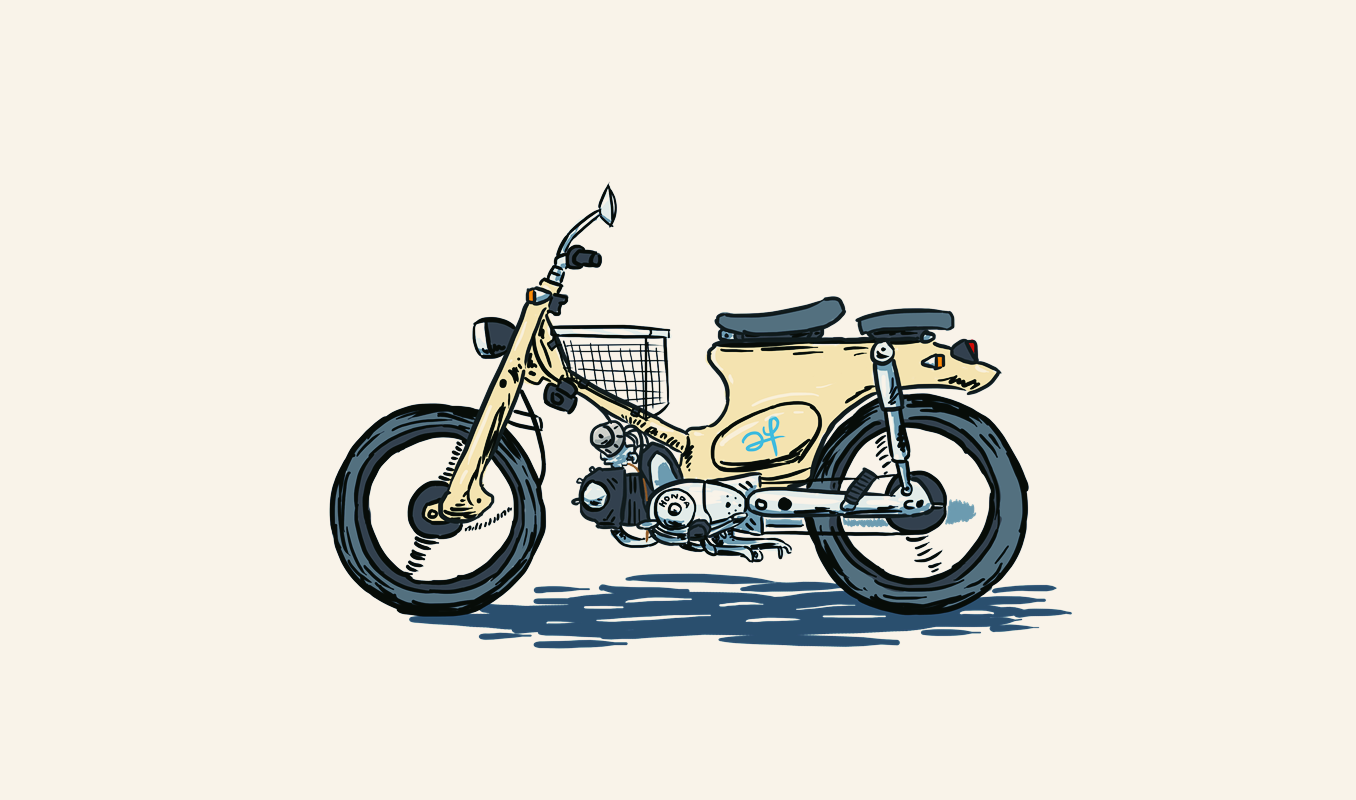
开平,广东中南部城市。在这里,理想与现实不断交错,过往的记忆层层叠叠,身处时间切片的夹缝之中,我们注视着阿杰不断下坠的生活,亦是回望一个人漫长旅程的编年史。
2012年夏天的某个傍晚,黄杰坐着破旧的城乡巴士回德堡,车上的座椅被烟头烫出几个洞,发黑的海绵从洞里面粉一样掉出来。回到村里,他发现这里的小孩已经不骑自行车了,他们卷起满是泥土的牛仔裤,骑着会发光的绿鬼火,整齐的蘑菇头和黝黑的脸庞写满了朴实与躁动。这个男人顺着新翻修的水泥路一直走,走到水泥路的尽头,踏上坑洼的土地,砾石摩擦的声音在乡间回响,他想起老父亲干瘪的手。他的蛇皮袋挂耳破了,一道口子顺着挂耳处从内而外裂开,掉出了一个带锈斑的钢碗。蹲下来捡的时候,黄杰呜呜地哭了,眼泪在银色的土地上留下了痕迹。
五年前
黄杰刚到深圳的脚手架场时,拖着一个崭新的彩虹蛇皮口袋,穿着一条迷彩裤。老板问了他许多事情,黄杰却羞于表达。老板抽了支烟,觉得这留长发的小伙不靠谱,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于是伸手招呼远处吃饭的师傅过来,让师傅带带这个年轻人。第二天上工,师傅说:“你看我做,看明白了就自己来。”黄杰接过师傅递来的脏手套,戴上面具,抓起电焊枪对着脚手架的裂缝仔细焊接,焊条末端跳出银白的火花,打在他的纸板面具上,他不为所动。当天晚上师傅让黄杰带包红双喜回来,过了一会,黄杰拎着一瓶玉冰烧又带了一包利群回来。师傅拍黄杰的背时,他知道自己可以留下来了。
每天中午,厂子里吃饭,工人们一起围在大圆桌前,他们露出古铜色的满身肌肉的身躯淌着汗。黄杰穿着松垮的汗衫,白色的手臂显得扎眼,一个叫老炳的工人笑道:
“似个散扪女。”
其他工友跟着笑,黄杰也跟着傻乐。他其实听懂了这句方言,是说他像个小女孩。厂里每次有货要装卸时,他都扛两人份,一个架子二十五斤,他一下扛五个,一直上完上千个也不吭一声。如此重复,从阴雨到烈日,他的眼睛看到工友当面给老板刷鞋,背地里诅咒唱衰老板,看到工友搬两个架子喊累,他看着看着,把自己看病了。
那是个回南天,被褥湿透,生锈的铁门往下淌着黄水,黄杰的风湿不可避免地发作。他左半边身体无法遏制地疼,疼痛从骨髓钻到关节,他想到爬山虎在裂开的墙上蔓延。但他照常卸货,脚手架框在他背上像把他框在里面,下车时他的劳保鞋打滑,人滚到了车底。工友们看到他的脚踝起了一圈环形的红斑,额头滚烫。老板要带他去医院,他执意不肯,老板瞪了他一眼,把他拉去医院。
车上,老板问他为什么不吱声,表情严肃,这个光头厚嘴唇的胖男人有一种不怒自威气场,黄杰打哈哈说:“我怕要我给钱,我要寄钱回家。我病了,我爹怎么办。”老板看着当时21岁的黄杰,没说话。从医院出来后,老板告诉黄杰,以后有事,要说。
黄杰的皮肤越来越黑,他身上的肌肉线条越发硬朗,他也会在中午脱去上衣,在老炳的叽喳抱怨声中,黄杰骂道:“鸭丐䔳多,似足嘅老婆乸。”
五邑方言里,这话意思是:叽叽喳喳,像个老太婆。吊顶的绿风扇转出哄笑。
厂子里的生活很累,每当夕阳沉下,空旷的厂里就会响起工人们的粗口声和麻将声。还有一些人会洗干净身体,在头发抹上廉价的啫喱水,出去嫖娼。黄杰喜欢看书,看那本发黄的《林海雪原》,看《射雕英雄传》。他偶尔也打打麻将,赢多输少,却经常向老板借钱,老板觉得奇怪,工资加上打麻将赢的钱,怎么不够生活。黄杰告诉老板自己在恩平有个妻子,她的名字叫小芳,再过一个月就生了。说罢看向老板的儿子,他抱着玩具在一边抬头看黄杰,又开口说想把小芳和孩子接过来。
老板娘常打麻将,这个爱穿松垮白背心的风骚女人很喜欢黄杰,厂子里的狗经常能在麻将桌底下看见一双白皙的脚在黄杰发黄的牛仔裤上滑动。黄杰从未回应这个女人,他觉得老板对他有恩,甚至把自己当成家人,但黄杰却还是忍不住平时多瞟老板娘几眼,瞟她择豆角,瞟她看书,瞟她在藤椅上昏昏欲睡。他们俩人中间隔着一层薄蚊帐,这层蚊帐在夏夜的风里摇摇欲坠,可一转眼已经是秋末,他只差一点点就忘掉了小芳和孩子,只差一点点。
黄杰拿出老板发的奖金买了台二手的破奥拓,开回恩平,去看他的老婆,回恩平的路上他发现高速边上的巨大广告牌从“凤铝铝材”变成“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平碉楼申请成功”,他记得厂子里的人包括老板和老板娘,都是开平人。
在家门口黄杰发现换了新门,钥匙开不了,他敲开门,房间里热闹非凡,他老婆已经生了,是个女孩,在摆满月酒。开门的是他老婆,门内的热闹仍在继续,有一个以前糖厂的同事过来问是谁,他看到黄杰就愣了一下,随后立马搂着黄杰的肩膀说:“虽迟但到,孩子爹回来了!”
孩子很可爱,眼睛滴溜溜转,像她妈。黄杰喝了很多,边喝边吐,大家都在劝酒,到他彻底醉了之后大家也就不管他了。昏沉中黄杰开门离开了不属于他的家,他扒在他的奥拓上吐,眼泪鼻涕都吐了出来,吐到后面他只感觉到胃袋在收缩,其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他带着满身的污秽坐回他的车里,睡着了。差不多是半夜三点钟他醒了,他开始扒在方向盘上哭,他的目光瞟到仪表盘前的mp3,发狠地扔出车窗,下车死命踩,踩到不能再烂后,又吐在了车门上。强忍着头晕把车开回深圳。凌晨五点,他到厂了,一直按着喇叭,大灯在蓝色铁皮门上反射着刺眼的光。老板娘出来开门,一下车他就抱着老板娘在哭,老板娘抚摸他的头,久不说话,俩人伫立在太阳升起的前一刻。
黄杰和老板娘的关系持续了一年,厂里来了个新的小伙子,叫小刘,戴着个小眼镜来做会计,能说会道,长得斯文白净,还是个大学生。小刘学东西很快,他一开始不会打麻将,打了几圈就开始赢钱了。后来他学会给老板或者老板娘点炮,大家看起来都很喜欢小刘,只有黄杰除外。
某天黄杰拉完货回来,他在门口看见老板娘在麻将桌底下用脚在小刘的裤腿上蹭,像曾几何时对自己一样。黄杰扑过去把小刘按在地上打,“操你妈!你以为你是谁?操你妈!”掀翻的麻将散落一地,电视上的刘翔低着头走向场外。
小刘住了一个星期医院,黄杰找老板辞工,老板想挽留他,他不敢看老板,他忍着把一切告诉老板的冲动,沉默地走了。辞工的那天晚上黄杰喝醉了,他点了两箱青岛,喝到喝不下的时候就去厕所扣喉咙,吐完了回来接着喝,再吐,再喝。吐到最后他的呕吐物里已经没有食物,只有酒。黄杰跪在马桶前面晕乎抬头,过了会,用小灵通拨下了墙上的号码。那个40多岁的女人在昏暗的白炽灯下脱掉自己的上衣,小腹下部蔓延出一条长长的疤痕,然后说喝酒不包出。黄杰躺了下来,眼睛看着在白炽灯上绕来绕去的蚊虫,生出一种可悲感。女人骑上黄杰胯部,上下晃起来 ,嘴里发出些黏糊的声音。
恍惚中黄杰把她当成了那年夏天里慵懒的身影,他流泪问她,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她操着一口熟悉的广西话问“去哪里?但你要把我赎走”。 然后伸手抹了黄杰的眼泪,抱住他的头,黄杰感觉到自己的头发在女人的指缝里变得柔软。他噙着泪晃身把床底下鞋盒里的所有的钱给了这个陌生女人。宿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傍晚,屋外零星的小孩笑声回响。女人消失了,连影都没有,黄杰一个人在床头坐了很久。
七年前
黄杰初到恩平的时候感觉这里和德堡没两样,都是这么穷。宿舍里的同乡告诉黄杰,珠三角之外的广东不算是广东,他们把这些地方叫做粤西、粤北。他们带黄杰去网吧玩儿,在前台听到网费一块五后黄杰转身就走。同乡拦住他,给他开了一个小时的机子,又请他吃了个泡面。黄杰不会操作,只能盯着同乡的屏幕,上面在放电视剧,是《东京爱情故事》。
在糖果厂,黄杰认识了个女孩,叫小芳,她长得很瘦,眼睛很大,肤色呈一种健康的小麦色,这使她看起来灵活、能干。但她似乎和另一个工友牵扯不清。
后来工友辞了,她就天天跟着黄杰,一开始会从家里带些零嘴分享给他,后来就慢慢给黄杰带饭、教黄杰说五邑方言,他从小芳这里得知,五邑方言是粤语的一支,这就是为什么电视上的粤语和恩平的方言听起来完全不一样。小芳送了个mp3给黄杰,黄杰蹭同乡的网费在网吧偷偷下歌,用蹩脚的粤语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后来小芳怀孕了,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黄杰刚从机床上下来,准备抽根烟。同事把黄杰叫住了,说小芳在门口。
小芳在门口踱步,她背着光让人感觉有些刺眼,脱掉手套走到她跟前,她说“我怀啦”,眼里带着一种得逞的狡黠。
黄杰带着小芳回到了家,他的父亲刚刚扯着一头跛牛进门,看到他俩,拍拍手上的灰“诶,来啦”。黄杰问父亲的腰有没有好转。父亲没有回答他,而是问起小芳一些事情。在谈话中,小芳得知,黄杰的母亲已经去世几年了。
最终这门亲事谈了下来,黄杰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了同村人几万块。在德堡的时候,黄杰和父亲把小芳当宝贝惯着,不干家务,不干农活,黄杰也不吱声,小芳说东绝不敢说西。直到小芳嫌这个腰折了的公公碍眼,跟黄杰提出了分家,留他父亲一人在这里。黄杰眼睛红了,想扇小芳,但看到她的肚子,就想起家里的牛,慢慢背过身说了句“好。”
从德堡回到恩平后,黄杰就跟着小芳住进了岳母家。恩平的路边栽满了芒果树,一到夏季,树上的芒果会一个接一个成熟,掉下来,然后烂在地上,散发臭味,招惹蚊虫。那天黄杰下工晚,走在路上差点被芒果滑到,到家门口时听见岳母在骂女儿也没出息,他正想冲进去的时候,听到小芳说孩子不是自己的,黄杰停下了开门的动作,在门外听着小芳抽泣的声音,岳母接下来骂的话他完全没听见,一个人在屋外轻轻颤抖着,楼道里的垃圾桶更臭了,他胃里往上反酸,但他还没吃饭。他慢慢下楼,在楼下点了根烟,想压住呕吐的欲望。烟雾在灯光里勾勒出风的轮廓。约莫半个小时,黄杰上楼敲开屋门,说“我回来啦”。
十年前
黄杰刚上高中时,家穷,住在德堡的深山里,要翻两座大山才到家,父母是憨厚老实巴交的人,种点小麦玉米,上山盘点山货过日子,家里最值钱的是一头怀了孕的老母牛和一匹矮马。他父亲把母牛当宝贝日日天未亮就赶上山去放,等牛犊生下来了,可以穿过国境线拉到河内去卖。母亲则拔拉点黄豆花生,有时拿些去镇上卖,一去一回也大半天不到家。在学校的广播里,他听到中国和中国台湾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有天母亲带着一大筐山货去镇上顺带一块陪黄杰上学,去的时候一块去的,黄杰嫌母亲背着箩筐土货丢人,在前面走得很快。中午的时候,学校外面跑进来一个同村的,告诉黄杰“你妈在路上晕啦。”
后来拉去镇上,查不出原因。转到大医院,发现是晚期肝癌。
那段时间黄杰在家陪母亲,父亲一个人干两份活,也是个回南天,路滑,牛失蹄滚下山坡,把父亲扯下,腰伤了,牛流产了,跛了,倒在地上吼叫,血和泥水混在一起。父亲抱着母牛,像抱着老伴般啕啕大哭,响彻山谷。
家里唯一的经济断了,父亲把跟了自己十年的矮马卖了,也凑不够钱给妻子看病妻子。没钱医,母亲熬不过,拉着父亲的手,让儿子读书,就撒手了。
父亲扯着跛牛,天天爬山去,每当腰痛得厉害,就坐下歇。他要搜点山货去卖,让儿子读书。黄杰自母亲去世后,成绩一落千丈,本来就不太会说话的他,更加孤寂,他原本成绩在班里第三第五,现在成了倒数。
不久,父亲的病情恶化,黄杰还是辍学了。他的语文老师觉得可惜,因为他喜欢黄杰的文章。刚得知黄杰情况时,他想帮他一把,但最后还是作罢,大家都穷。想起曾经羞涩但真诚念着自己范文的学生,他摸向自己年轻时最喜欢的书。
黄杰在宿舍收拾行李时那个老师站在门口,他过来送黄杰,这个带着眼镜的矮小中年男人有一些发福,他们并肩走到校门口。校门口有一条江,据说顺着江往上走就是越南,黄杰听说那是一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国家,在那里草丛里会突然冒出几个人来,在那里每个人都像猴子。江风从上流吹下来,穿过两人之间,黄杰哽咽着凑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老师给了他一本《林海雪原》。黄杰颤抖着告诉老师:“老师,我想读书。”老师抱住流泪的黄杰,说:“欢迎回来。”
很久以前
小杰最高兴的时候便是果农收获的九到四月,那时父母偶尔会去帮农,果农会送帮农的人一筐果子回家,以此支付工资。傍晚放学之后,他准时守在村口,远远看到一匹矮马和两个人影时,他就迎上去,总能从母亲那里讨得一两个山楂或者脐橙。
这天也不例外,只是小杰等了很久很久,始终没有等到两人一马的影子,他坐在村口的大榕树旁边,旁边跑出来一个陌生的小女孩,说“你别等了,你爸爸妈妈不会回来了。”
她嘴里不是德堡话,但是小杰却听懂了。
“他们一定会回来的,小芳,他们会带回来一大框的脐橙和山楂,如果我拿到两个,那就分你一个,如果我拿到三个,那就分你两个。”
小芳犹豫了一下,说:
“好,我陪你等,他们一定会回来的,你也一定要分给我喔。”
小芳坐在小杰身旁,背靠大榕树。过了不知道多久,傍晚的夕阳一直没有落下,榕树的根系蔓延到两个人身上,缠绕出他们两个的形状,扎进他们的血管里。
远处传来清脆的马铃声,小杰站起身来,身上的枝条脱落,他目光清澈,盯着远方。
“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