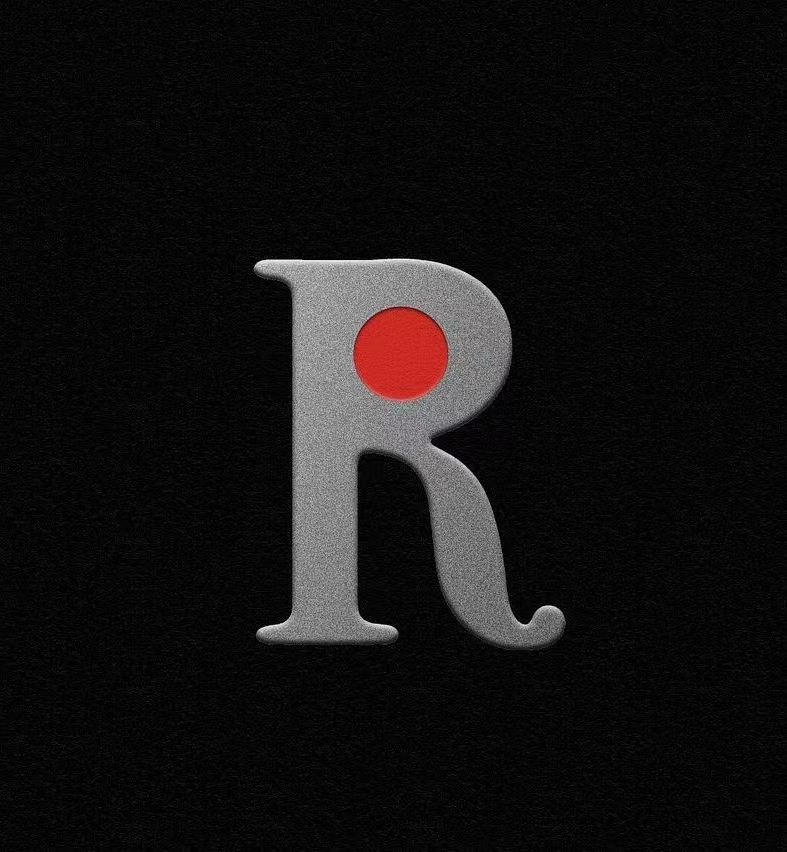不知道在气什么,大概是对人类还有要求。
我和朱丽坐在泰昌商厦二楼周大福对面的蜜雪冰城喝奶茶,我那杯早早喝完了,她还剩半杯。她两根手指掐着吸管,手掌覆盖在奶茶杯上,把大号蜜桃四季春捂得密不透风。我第一次见女人的手长成这样,手掌纤薄,边缘锋利,手指细长,顶端尖锐。张开像五把改锥,合拢像一把刀。一开始我就痴迷于朱丽这双手,现在痴迷依旧。
她的眼睛盯着窗外的周大福珠宝店,隔几分钟就把嘴巴凑到吸管上,很吝惜地吸上一口。珠宝店在吊灯的加持下,整个熠熠生辉,从那些黄金、白金或者钻石上放射出的光芒像钉子一样钉进我的眼睛,刺痛着眼球,我只好戴上墨镜。一个小时里,珠宝店来了五个顾客,前面四个一男一女结对而来,一对像是恋人,但可能不是,一对像是父女,但肯定是恋人。前者逛了逛,迅速离开,后者买了一对金耳环后离开。朱丽小声说,这个男人一看就不正经,眼神儿四处晃荡,做贼心虚一样。我说,可能怕碰到熟人。朱丽说,你瞧他那猥琐样,瞅着来气,就他了。奶茶杯在桌上一顿,意欲起身,我拉住她,说,再等等,还有大鱼。然后我们就等到了第五个人,那条大鱼。他四十来岁,头有点秃,穿着板正的西服,背个公文包,很羞涩地跟导购员询问一只钻戒的价格。朱丽说,这人准是个推销员。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也干过这行,你等着吧,他问完价格就要推销理财产品了。我说,打个赌吧,我猜他会买那个戒指。她说,闲的,才不跟你赌。五分钟后,男人付了款,从导购手里接过钻戒,极其小心地装进了公文包。朱丽诧异地看着我,说,神了。我说,我看人很准,没走过眼,别愣着了,干活吧。我们站起身,尾随男人出了商场。
显然,朱丽不是合格的扒手,但是潜力无限。从第一次见到她我就确定了这一点。她背着个小巧的双肩包,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几次试图用那只长手靠近我。以我十来年的从业经验以及多次反侦察行动中练就的敏锐嗅觉判断,这是一只天生当扒手的手,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的类型,可以说天赋异禀,如果我是一名音乐家,估计也会说这是一只天生弹钢琴的手,可惜我不是。我只是个小偷。充满天赋的小偷。
据我妈讲,在我一周岁时,全家人为我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抓周仪式,他们把我放在床上,在我面前摆好钢笔,锤子,滋水枪,菜刀,镊子。它们蕴含了一些美好的寓意,分别代表作家,建筑师,警察,厨师,还有医生。但他们没想到,在他们意志之外,这些东西还可以代表骗子,建筑工人,抢劫犯,屠夫,小偷。如你所想,我选择了镊子。我曾在菜刀和镊子之间犹豫了一会儿,是我妈让我坚定了信念。她把菜刀拿走了。在她的认知里,医生是比厨师更高尚的职业,我应该感谢我妈,不然我现在极有可能在胡同口卖猪肉,甚至沦为杀人犯。那会让她更加失望。
我抓住她的手腕,把她带出人群,领进了景区旁边的一家咖啡厅,点了两杯咖啡,当着她的面我掏出一盒没有开封的避孕套。她吃惊地看着我,说,你想干吗?我不是那种人。我说,我知道你不是,我只是想给你表演个魔术。我把避孕套打开,倒在桌子上,让她数,她说,搞什么名堂?十只。我说,你看清楚,不要眨眼。我把十只避孕套一一装进盒子,封好口,扔到她面前,说,你猜,里面有几只?她笑了笑,样子不屑,你还想上春晚呢?我说,不一定能上春晚,凭这手艺,街头卖个艺,不至于饿肚子。她打开盒子,再次把避孕套倒在桌上,手指扒拉着数数儿,数到七,她停了下来,眼睛直直看着我,说,少了三只,去哪了?我摊开左手手掌,露出三只避孕套,我发现,她的眼睛在闪光。
当天晚上,我邀请她在如家过夜,她同意了,当我试图靠近她的身体时,她拒绝了。我们躺在床上,百无聊赖,我不停打瞌睡,而她困意全无,逼我给她讲故事。我说我的小偷生涯应该从五岁那年说起。
五岁那年我刚上幼儿园。幼儿园里有很多玩具,我都很喜欢,尤其那个魔方。我玩了三天,只转对三面。到了第四天,我不转了,我把它装进书包,带回了家,一进家就向我妈求助,我妈说,哪来的?我说,幼儿园。我妈说,你这是偷。我懵懵懂懂的,以为是夸奖,高昂着头说,对,就是偷。我爸闻声赶来,简单了解案情后,说,这不是偷,顶多算借,明天还回去就行了。我妈马上制止,那怎么行?那不就坐实了偷东西?我爸说,那咋办?我妈说,别声张。没几天我又带回块橡皮泥,我妈说,别声张。再几天,我带回个变形金刚(那玩意儿人形有半米长,折叠成汽车也有三十公分,天知道我怎么在老师眼皮底下瞒天过海的)。这次我挨了我爸两巴掌,我妈说,过分了。我爸说,是,忒过分。我妈说,我说你,过分了,吓唬吓唬得了,至于打孩子吗?我爸气得直跺脚,拳头朝天挥舞,长太息以掩涕兮,曰,小漏不堵毁大堤,小病不治成大患!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我小学时的同桌家里有钱,有一次他带来学校一只转笔刀。转笔刀没什么稀奇,他的有点不一样,第一是体积,有一个馒头那么大;第二是造型,是一头翘尾巴的大象,露出肛门,动作有些不雅——后来我才体会到设计者的良苦用心——我同桌把铅笔对准大象的肛门,轻车熟路,噗一下插进去,铅笔固定在了大象肛门上,然后他一只手扶着铅笔,另一只手转动大象的鼻子,铅笔在大象肛门里咯吱咯吱搅动起来(看得我小腹一阵绞痛)。这令我非常眼红。没过一个星期,转笔刀丢了。老师翻遍了全班同学的书包和桌斗,都一无所获。
后来,他又陆续带到学校一只悠悠球,一个俄罗斯方块游戏机,一把仿真手枪,无一例外,都没能逃过丢失的命运。为这,我没少安慰他,正是那段时间,我俩的友情突飞猛进。现在,大象转笔刀、悠悠球、俄罗斯方块游戏机,仿真手枪全都安安稳稳地躺在我老家那口旧皮箱里,我妈几次想给我扔了,我誓死捍卫,才得以保存下来。我是个念旧的人。
听完故事后,朱丽笑得翻来覆去,笑完了,她说,那你当上小偷应该感谢你妈呗?我说还真是。
但我不能让她知道我的职业。
我妈当然不知道,他的宝贝儿子在技校的第二年因为“藏起”同学的笔记本电脑而被学校开除,交往了半年的女朋友也因此分手;她也不知道,我所谓的国际贸易集团高级职员身份完全出于杜撰,我没有集团,只有团伙;她更不知道,我每次出国考察给她带回来的礼物都购置于看守所外的路边摊,我不清楚老板从哪里囤来那么多外国货,比如韩国泡菜,俄罗斯硬糖。
我说,你呢,为什么要当小偷?朱丽再一次笑起来,她说,也是因为我妈,但跟你不一样,我妈很抠,一分零花钱舍不得给我,每次放学,看着小伙伴儿们钻进小卖部买棒棒糖买冰糕,买这买那,我都馋得要命。
朱丽回到家,请求她妈给她一块钱零花钱,她合计好了,五毛买作业本,剩下五毛买一根冰棍,她妈果断拒绝了她,说本子我明天去商店给你批一箱回来,冰棍太凉,吃了闹肚子。朱丽说,那就买棒棒糖好了,吃棒棒糖不会闹肚子。她妈说,棒棒糖不会闹肚子,却会让你的牙齿生虫子,牙疼可比肚子疼严重多了。朱丽不再说话,到了晚上,等妈妈熟睡,她偷偷爬起来,在妈妈的衣服口袋里翻出来十块钱,她本想少拿一点,但是妈妈口袋里只有几张十块的。她把钱装进书包,第二天带到学校,放学时她吃到了梦寐以求的冰棍。她没有买作业本。
如果事情就这样过去,这个微不足道的污点大概不会再继续腐蚀朱丽,但是朱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她把剩下的钱又偷偷塞回了妈妈的口袋。妈妈察觉到口袋里的钞票数量虽然多了,但是面值变小了,朱丽无疑成为了首要怀疑对象,一开始,朱丽负隅顽抗,可终究抵御不过鸡毛掸子的严刑逼供,打到第三下,她招了。
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朱丽没再动歪心思,甚至一想到人民币就条件反射地屁股疼。直到有一天,妈妈藏在梳妆盒底下的八张十块钱不翼而飞,那是准备过年时给亲戚小孩们的压岁钱,她很轻易地怀疑到有过前科的朱丽。这次朱丽一开始就据实以告,我没拿,我也不知道那里面有钱。
我见你动过那个梳妆盒。
我只是拿了个发卡。
你还想抵赖?
没剩几根羽毛的鸡毛掸子时隔半年之后再次奔赴朱丽的屁股,来势比上次凶猛了很多。朱丽在哭嚎中一遍遍申辩,我没拿,我真的没拿。
我叹了口气,抱住她,说,可怜,那钱找到了吗?朱丽挠了挠自己的屁股,似乎翻腾起来的回忆又准确无误地击中了她那个屡受伤害的部位。她说,还真找到了,就夹在一本《知音》里,母亲去世后,我随便翻看那本书的时候找到了它们,一张张分开夹在书页之间。
她不知道谁把钱进行了转移,大概率出自妈妈自己的手笔,但是健忘的毛病抹除了妈妈存放在脑海中的这段历史,让事实凭空消失。她把钱取出来,想了想,揣进了自己的口袋。她想她拿的不过是不存在的钱,它们不属于妈妈,也不属于别人。现在属于她了。
那以后,我看到别人从兜里掏出钱夹就忍不住兴奋,心痒难耐,不把里面的钱弄到自己手里就好像使命没有完成一样,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踏实。她说,毕业后,我做过很多工作,做得最久的是保险推销员,因为它能让我遇到更多愿意把自己的血汗钱掏给你的冤大头。
我说,你活该当贼。她说,可惜一直没人带。
我立志要把朱丽培养成一个技艺超群的小偷,好让我一身本领有个传承。我为她制定了严格的培训计划。首先是练手速,我们各自伸出一只手,一上一下,掌心相对,悬停在半空,下面的打上面的手背,打到了继续打,直到上面的躲开,攻守互换。攻方可试探,可做假动作,守方等攻方出击的瞬间才能撤手掌,早了犯规,晚了挨打。最初的一个月,她先手一次没打到过我,我先手她一次也躲不开,没多久,他的两个手背像是发酵粉放多了的面团,迅速鼓胀起来,甚至有爆浆的趋势。到了第二个月,互有胜负,她左手快一点儿,我右手快一点儿。学成。改练徒手抓苍蝇,我把她关进厕所,窗户打开,好让苍蝇飞进来。一开始她一只抓不到,过了一个星期,能抓到飞行缓慢的怀孕母苍蝇,再过几天,可以抓到灵活的青年苍蝇,之后,她又无师自通,学会了夹苍蝇。两根手指凌空一点,一只苍蝇束手就擒。那段时间,朱丽捉苍蝇上瘾,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开着窗户,正值深秋,我俩先后都被窗外溜进来的病毒袭击,流了一周的清鼻涕。
练完手速练刀法。我买来一箱红富士,给她一把水果刀,让她削苹果皮。我以为她会质疑,但她没有,她很听话,孜孜不倦地削苹果皮。起初,她削得毫无章法,苹果被肢解得残破不堪,一块块碎皮带着厚厚的果肉散落一地。没过多久,能完整削下果皮而不断裂,到了后来,果皮能够随她心意,变换成任意形状,比如一只蝴蝶或者老虎。这时朱丽才问我,你是让我当小偷还是当厨子?我没回答她,而是背上背包,说,如果我把手机放包里,你怎么取出来?她看了看手里的水果刀,说,那得换把快刀。
最后一项技能,也是最重要的,是如何逃避警察的抓捕,这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锻炼嗅觉,再有,是找到合适的下手对象。
什么样的才叫合适?
比如瞒着老婆送给情人的钻戒,比如来路不明的钱财。
偷来的钱?
还有赃款。
我懂了。
这是我在从事小偷行业十年之后才领悟到的真谛,可以写进《盗贼宝典》的金科玉律。朱丽很幸运,刚踏入这行就遇到了名师指点,少走了很多弯路。几年前,我偷了一个女人的两万块钱,那些钱在她包里待了不到五分钟,刚出银行就被我成功转移。她报了案,一周后,我被捕了,据说那个女人生了一场暴病,两天就死了。我想她的死亡大概跟丢钱没有关系,只是时间上的巧合罢了。不过这事还是让我反思了很久,出狱后我决定只偷来路不明或者去向不正的钱,这能让我最大限度免受牢狱之灾。
她将匕首掖进衣袖,疾步走向那个男人,当她和他的身体相触时,我看到她的匕首蛇信子一样跃出袖口,在男人的公文包上吞吐,又迅速收回。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看到这一幕。那是一个路口,男人毫无察觉,继续前行,朱丽右拐,看着男人走远,得意洋洋地冲我扬了扬手里的戒指盒。
庆祝朱丽旗开得胜,晚上我请她吃的海底捞,我喝了不少,朱丽只喝了一瓶啤酒。饭后,我再次邀请朱丽,到我家坐坐,她接受了。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藉此实现质的飞跃。
我向她展示了近一年来的战果,一保险柜的现金,还有一些没来得及换成现金的首饰手表。朱丽不无艳慕地说,这么多钱,十年花不完吧?我说,一个人花不完可以两个人一起花。后来,我们到了床上,我依旧没得逞,如果我再坚持一会儿,肯定能拿下,但我放弃了。我侧身抱着她,她平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悬下来的吊顶。她说,现在你经常去看你妈吗?我说,一周一次吧。她说,她没怀疑过?我放开她,翻过身子,跟她一样盯着吊灯,有点刺眼,没有吧,她很信任我。
那你恨过她吗?
我的眼睛离开吊灯,一个白色的亮斑随着眼睛眨动在墙壁上忽隐忽现,没有,我为什么要恨她,这又不是电视剧。
那你后悔过吗?
亮斑消失了,一团黑暗在眼前一掠而过,非要说一件的话,就那个女人了,如果我不偷她的钱,她也许不会死。
哪个女人?
你不认识,四五十岁了,说起来倒跟你有点连相。
啪。朱丽关了灯。黑暗从天花板倾泻而下,迅速填满房间。
等我醒来,看了眼表,早上八点,房间里依旧昏暗。窗帘拉得很严实,我不记得昨晚拉窗帘。然后我发现朱丽不见了。我从床上跳起来,跑向保险柜。如我所料,保险柜门敞开着,光秃秃的嘴巴里只剩一颗耀眼的牙齿,是那只钻戒。还算她有良心,给我留了只钻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