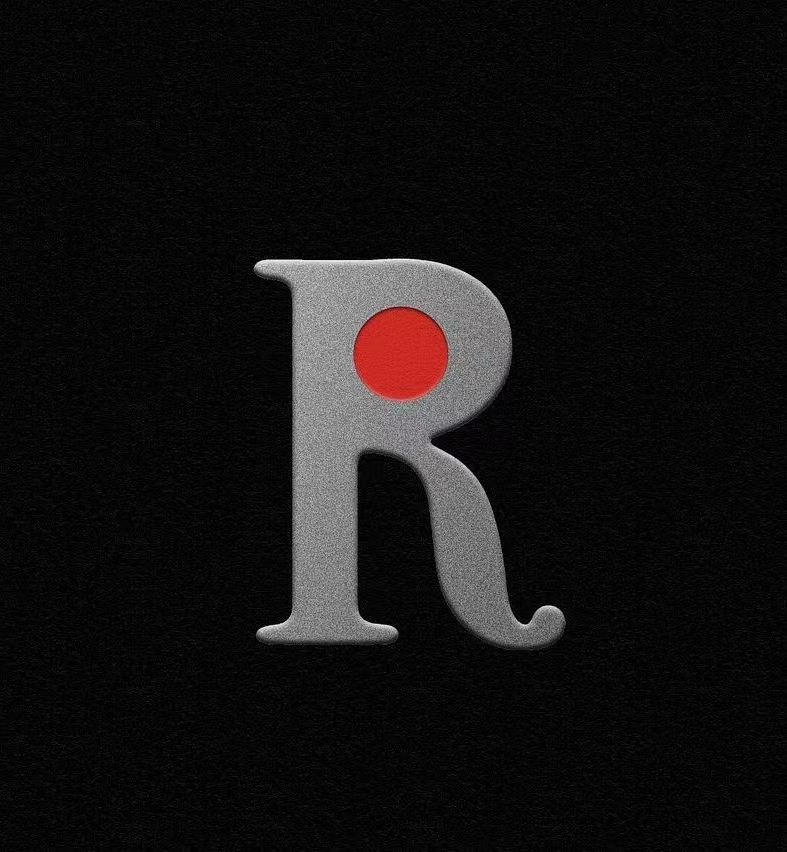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无限放大已经失去的?
1
脸上的红色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很奇怪,这次没能在我体内引发飓风。我记得上次发现它们在变大时,我狠狠对我爸发了一顿火,镜子也打了。我爸一边用秃毛笤帚扫着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一边说,打得好,不照镜子就不会心烦了。我说他这是自欺欺人。不管照不照镜子,脸上的红色蝴蝶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每时每刻都在被我感知,它们在生长,在繁衍。我爸干笑着,还好,你是个男孩,不靠脸吃饭,还好,你有才华,可以当个作家。我没搭理他,他还在叨叨,有个大导演,白癜风,脸白得吓人,人也没自卑,该宣传宣传,该出镜出镜。我说,你都说了,吓人。父亲意识到失言,腾出一只手来打自己的嘴。我想安慰他,可不知道如何开口,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我偷偷藏起一片镜子碎片,弧形的,像一把刀,等我爸出了房间,我把它从枕头底下取出来,观摩了一阵,真的像一把刀,肯定很锋利。里面有我的半张脸,从额头到下巴,一分为二,切割整齐,上面栖息着四只蝴蝶,都是红色的,有大有小,看着看着,它们在我脸上舞动起来,围成一个圈儿,盘旋,可就是不肯离开我的脸,慢慢那张脸消失了,我在里面看到了另一个自己。我上大二,成绩还行,文笔也不错,在学校文学社任社长,发表过几篇小说。没得病之前,脸还算看得过去,起码不讨人厌,交了个女朋友,痴迷于村上春树,后来她把这种痴迷转嫁到我头上。直到我得病休学。
我学着电影里的样子,横握玻璃刀,在手腕上划下,一条蛇,又是红色,钻出我的皮肤,并不觉得疼,它沿着我的手腕滑行,到我的大腿,鞋子,地板,慢慢铺展。我看着它,它变成了冷艳的火,冰冷地燃烧。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被窝里,四周一团漆黑,被子带着我飞驰,有剧烈的颠簸感,风从被缝里灌进来,带着初秋田野里饱满的生机,玉米谷子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试图包裹我。父亲在我身前咳嗽,我说,爸。他没听见,我摸了摸手腕,包住了,是布,被血浸透,黏糊糊的。
在镇卫生所进行简单的消毒包扎,医生说,别想不开。我说,想开了。他说,你想得太开,死都不怕,还怕活着?我说不怕,反正活着最后的归宿也是死。后半句并没有说出口,我担心医生给我灌鸡汤。一圈圈白色绷带在手腕上缠绕,扎紧。医生把我爸叫出去,不知道嘱咐着什么,不久两个人一起走进来,我又被蒙上被子,我爸搀着我,我只能看到自己的脚面,一双灰色的人字拖,左脚卡带夹在中趾和二趾之间,一定是我爸情急之下胡乱套上的。下了几磴台阶,我爸两手插进我的腋下,说,上车了。我从被缝里看到我家绿色三轮车的剪影,上面满载阳光。我说,爸,今天天气好吗?我爸说,好着呢。
2
这个病遗传自我妈,她在二十八岁发病,皮肤出现红斑,增大,溃烂,见不得光,听说并发症很多,发热,呕吐,关节疼痛,主要是没法根治,只能用药吊着。她在我五岁时的九月上吊自杀,其时我爸下地收玉米,我在上幼儿园。对于母亲的零星记忆聚焦在她的哭声上,那声音飘飘忽忽,二十年来时常趁我不备搞偷袭。我曾天真地以为我会完美避开遗传厄运,可它终究还是找到我的头上。我的病情要轻一些,除了不断增大的红斑和偶尔的发热外,并没有其它症状,以后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谁也说不好。
马上又到了秋收时节,我爸去地里看玉米是否成熟,他把家里的利器全部藏了起来,菜刀、剪子、锥子,甚至一根针,还有绳子。我告诉他,你放心去吧,我不会再寻死了。上次之后,我对死好像也提不起兴趣。他说,你要无聊了,就写小说,写不下去就看书,看电影也行。我说知道了。在他走后,我在房间里枯坐着,好像坐在一口井里,窗帘常年紧闭,地板能渗出水,被子我爸三天两头晒,吸收一点阳光很快被潮湿消解。床头有一本舒尔茨的小说集,翻了两页,书里的父亲一会儿养鸟,一会儿变成螃蟹,挺不让人省心的。看得昏昏欲睡,也许真睡着了,时间突然变得紧凑,像被压实的面包。我爸很快回来了。他走进我的房间,带着熟悉的青玉米的味道,他说,我在咱家玉米地里发现了一具尸体!看样子有点兴奋。
我把书扔了,它不知道什么时候盖在了我脸上,我从床上坐起来,说,报警了吗?他说,没有,开始想报警,可是手机没信号,我走出去二里地,站在一个高坡上,手机有信号了,可我突然不想报警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我想自己破案。我呆呆看着他。你帮我,他补充道。
我说,我又不是警察,你也不是侦探,不要异想天开了,万一耽误了破案时机,咱可兜不起。我相信你,他好像胸有成竹,你看了那么多小说,也写过破案的,我看过你那篇,写得很好。我说,哪篇?他说,就那篇,一个老太太丢了狗,实习警察帮忙找狗的故事。我说,那是狗。他说,一样的,这次我们来找凶手。
我说服不了他,他兀自跟我描述着案情。他走进玉米田,发现中间有一片玉米倒伏在地,开始他以为是被雨水冲倒的——前些天刚刚下过一场雨,后来发现不对劲儿,玉米秆全部从根部折断,一定是人为造成的,他再往前走,就看到了那具尸体。
我说,男的女的?他说,女的。我说,多大年纪?他说,看不大出来,中年吧,反正不算老。我说,穿什么衣服?他说,黑色运动服,一身黑。我说,有LOGO吗?他说,啥叫LOGO?我说,标签,标志,图案。他说,没有,就全黑。我说,那是运动服还是秋衣秋裤?他说,运动服吧,又有点犹豫,应该是吧,我再去看看?我说,先别急,还有其它的东西吗?比如手机、皮包、钱夹之类的,首饰也算。他说,没有,啥都没有。这次很肯定,我看到他用力点了点头。我说,那有可能是抢劫,她反抗,被劫匪残杀,抛尸在玉米地。他说,应该是吧,去年也差不多这时候,张大全的媳妇就在地里被抢了手机,玉米秆一人多高,好藏人。我说,是,天然的屏障,对了,她身上有伤吗?他手扶在额头上,想了一会,说,这也没仔细看。我说,下午再去看看吧,记得拍几张照片儿。他说,我老年机,没这功能。我说,用我的。他说,算了吧,万一别人找你找不到,不着急吗?我晓得他说的“别人”是我女友,现在应该说是前女友,我没告诉他,我们前一天刚刚分了手,是我提出来的,她没反对。
3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我爸商量,下午能不能带我一起去?我想亲眼看一下现场。他否决得很干脆,不行,你不能见光,你说看啥,我保证一样不差地给你看好了。我说光看不行,得详细记录在案。他说,那就写下来。吃了半碗白米饭,我回到房间,找出本子,上学时的作业本,只用了一半儿,我把用过的一半儿撕掉,在空白页上写下:1.尸体有没有伤口,伤口的数量、形状、大小。2.尸体的容貌特征、身高、体型。3.周围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脚印之类。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拿去给我爸。他正在洗碗,搞得动静很大,叮叮当当的,我都替碗担心。我说,爸,我给您写好了,下午您照着上面写的看。他说,放灶台上吧。我还有点不放心,说,你自己想到什么看到什么,也记下来。他说,好嘞,你去睡吧。
我躺在床上,拿出手机浏览本地新闻,并没有寻人或者缉凶的消息,看来刚发生不久,或许死者是个外地人?万一凶手回来毁尸灭迹呢?我突然担心起来。院子里有了响动,是我爸发动了三轮车,我拉开窗帘,午后的阳光闯进来,我顿时觉得皮肤火烧火燎的,脸上的蝴蝶躁动,似乎想挣脱。我说,爸,你自己小心点,最好带着防身的家伙。他指了指三轮车斗,里面有把铁锹,放心吧,你爹不傻。上了三轮车,又说,快拉上窗帘,晒。我拉上窗帘,听着三轮车轻快地颠出院子,铁锹在里面咣当乱颤。
大概不需要为我爸担心,我爸身高足有一米八,体重超过二百,年轻的时候练过拳,在我生病之前还每天起早在院子里走一趟太极十八式,嘴里呼喝不断。生病后我有段时间心情烦躁,他一打拳我就对着窗子喊,喊过几次,他把拳中断了。现在想想,这事儿我做得不对,人得有个爱好,精神寄托,当你孑然一身时,这个爱好就是最后的陪伴。你和它不一定同生,但应当同灭。
我又看了会书,舒尔茨热衷于写父亲,一个朦胧的虚无缥缈的父亲,离我如此遥远,或许我该趁着这个机会恶补一下刑侦小说,之前对此类作品并不感兴趣,现在有点饥渴。我从网上下载了东野圭吾全集、阿加莎全集、福尔摩斯全集,不知先从哪一部下手,《名侦探柯南》是不是更好吸收一点?
下午四点时我爸回来了,他把本子递给我,返回自己房间,端过来一个搪瓷茶缸,咕咚咕咚,先喝了一通水,问我,能看清吗?字有些邋遢,七扭八歪,上面还粘着泥点子。我说,差不多。他说,要不要我给你念?我说不用。1.尸体上有三处伤口,分别在肚子左侧、右腿、左肩,伤口是菱形,枣核大小。2.女性,矮胖,黑,丑,腿短而粗,耳朵比较大。3.没发现鞋印,有脚印,经查对,是死者自己的,想来死前经过了一番折腾。我说,就这些?他点点头,双手捧着搪瓷缸子,样子有些拘谨,漏掉什么了吗?他问我。我说没有,就是信息实在有限,我不知道该怎么入手。他说,慢慢想,不着急,你把你自己当成侦探,你会先从哪里入手?或者你就当成写小说。我说,这不是写小说,写小说是答案就在作者脑袋里,他一点点把线索抛给读者,现实里是,我们得根据有限的线索来寻找答案。他说,可以试试,就算破不了案,能写出一篇小说也不错,你就把我当成男主角。我看着他,面皮焦黑,像是在煤堆里打过滚儿。他嘿嘿笑,露出一口白牙,形象是差点,说,男一不行,那就男二,你是男一,我们搞一个组合,中国的福尔摩斯和华生,现实的蝙蝠侠和罗宾,当代的狄仁杰和元芳。
他还是老样子,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多严肃的事儿到他那都像儿戏。小时候他让我学游泳,我说怕,他说没事儿,我保护你,拉着我到池塘边,脱得赤条精光,抱着我往水里跳,我反应不及,先呛了一口水,剧烈咳嗽,鼻子眼睛里往外涌酸汁儿。他跟我道歉说,有点心急了,下次注意。我说还有下次?我不学了。他对我威逼利诱,说,咱们这儿是泛区,哪天来了水,不会游泳的都得淹死。我摇头。他说,临河乡的人不会水,说出去让人笑话。我摇头。他说,学会了游泳,我给你买冰棍儿。我说,我要奶油的。
那是个盛夏的午后,人们都在午睡,池塘也在烈日下打盹儿,水面像一面镜子,映着它的梦,是岸边的垂柳蓝天白云。后来加入了我和我爸。我爸托着我的肚子,我在水面上漂浮,他教我动作要领,划手腿不动,收手再收腿,先伸胳膊后蹬腿,并拢伸直漂一会。教了两遍,问我,会了吗?我的嘴巴在水里,没法回答他,我只觉得水的阻力在增大,身子也越来越沉,后来又呛了一口水,才发觉肚子下的一双大手不知什么时候撤走了。我那天没学会游泳,也没吃到雪糕,肚子里都是池水,也可能混杂着鱼的尿。
4
在我爸的央求下,我不得不动笔写一篇小说,名字叫做《父子神探》,身手不凡的糊涂老爸和身体残疾的高智商儿子,一武一文,一个负责搞笑一个负责耍帅,俗套却经典的搭配。父子俩侦破一桩凶杀案,然后卡壳了,卡在现实里。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爸在客厅看电视,我走出去,他看得入迷,没发现我。《大宋提刑官》,音量很小,为了听到声音,他不得不身子前倾,探长脖子,脑袋几乎扎进电视里。我站在他的背后,说,爸。他一哆嗦,扑通坐在地上,我感到地面颤了几颤。他说,鬼鬼祟祟的,吓死老子了。我说,你才鬼鬼祟祟,看个电视,至于吗?他说,你不写了?我说,不写了,没灵感。他说,那就歇歇。随手把音量调高。我说,您还想学验尸?他说,瞎看。我说,关于那具尸体,您怎么看?他轻描淡写说,我怎么看无所谓,关键是你怎么看。我坐在他身边,说,先把电视关了吧。他关了电视。我说:第一,伤口是菱形的小孔,那肯定不是刀子或者匕首所致,也不是挥砍,我比划着,应该是直刺,所以我觉得凶器应该是改锥之类的工具,这说明凶手并不是惯犯,杀人是临时起意。第二,三处伤口,好像每一处都不致命,那她是怎么死的?失血过多?第三,你说,周围有她的脚印,这说明她不是死后被抛尸玉米地,而是在玉米地里死的。综合可知,凶手是个新手儿,刺了死者三次,都没有致命,死者在惊慌中逃跑,凶手肯定追了一程,死者跑进玉米地,凶手遍寻不到,只好返回,死者在玉米田里失血过多,最终死去。
我爸听得入神,频频点头,等我说完,他模仿着我的语气,或者是电视里的提刑官,说,我很认同你的观点,只有一点稍微有些别的想法。我说,哪点?他说,第一点,你说凶器是改锥,你想,改锥的话那么近的距离,有可能三次都刺不到要害?我说,有这种可能。他说,你没打过架,如果没有计划地乱捅,那应该三下都朝着肚子招呼,即使死者有躲避,也不会差了太多,现在另外两处伤一处在肩膀,一处在大腿,很不合常理。如果有计划,那应该三下都奔着要害,所以还是不合常理。我惊异于我爸缜密的逻辑,我说,看了一晚上《大宋提刑官》学到这么多?他笑笑,哪里,瞎想的。我说,您接着分析。他说,我是想,凶器会不会是远程武器?我说,你说手枪?不可能,子弹伤口不会是菱形。他说,别的呢?我想了想,弓,或者弩?他对我翘起大拇指,说,我儿子这脑子,快!我说,您别着急夸我,弓或者弩的话,应该有三支箭留下啊。他愣了愣,说,我明天去找找。我说好,起身到院子里,月亮很大,挂在院子正中的石榴树上,石榴树结了不少果子。我爸也跟出来,打开院子里的吊灯,整座院子被橘黄色的光芒笼罩,石榴树上的果子反着光,半青半红,还没裂口,不过离成熟不远了。自从我得病以来,白天我不出屋,晚上也懒得动,都不知道石榴树已经硕果累累。
我爸在我身后说,早点睡吧,破案费脑子。
今晚脸上的蝴蝶很安静。
5
早上七点钟,我被冻醒了,感觉身上发冷,试了试体温,38.5℃,下了床,脚下虚浮,头晕。走到厨房,我爸已经做好饭,两碗冒着热气的玉米粥分列餐桌左右,我坐在一碗粥前,双手捧着粥碗,热气贯穿双臂,直抵肺腑,我爸看着我,说,不舒服?我说,没事。我爸大手放在我的额头,这么烫,还没事儿?我说,习惯了。他说,喝完粥吃药。我说,嗯。我爸又问,那还写吗?我说,写吧。我爸说,好,那我再去找找线索。我说,那我先看书。
我爸走后,我点开了《白夜行》,差不多的设定,主人公发现尸体,不过尸体的性别是男,不是女,地点是在废弃的工厂,不是玉米地。书里死者的身份很快被确认,而玉米地女尸的身份像一个谜。《父子神探》应该这样写,糊涂父亲开车带着机智儿子路过一片玉米地,父亲突然感到一阵尿意,于是停车跑到玉米地里解手,脚下被绊了一下,他低头发现了那具女尸。父亲虽然糊涂,但是见多识广,所以并没有被尸体吓到,他从容不迫解完手,手在衣服上抹了抹,开始检查尸体,尸体死了有一段时间了,裸露的皮肤上有大块尸斑。为了增加看点,尸体应该设置成少妇,淡妆,长卷发,有点漂亮。服饰呢?职业装,名牌,VeroModa,但父亲并不认识那个牌子,需要儿子来确定,需要暴露一点吗?不用,短裙,衬衣,LV的手包挂在肩膀上,里面有现金,手机不在,应该是凶手为了掩人耳目故意拿走了。那么,应该是谋杀,不是劫财,也不是劫色。身上三处伤口,菱形的小孔,身边有脚印,经比对,都是死者自己的。
写作再次陷入停滞,很多细节无法靠想象填充,继续看书。不久之后,我爸回来了,他兴冲冲闯进我的房间,扬手说,你看这是什么?他的手里握着三支箭。我检查了那三支箭,箭头是菱形的,材质应该是某种坚硬的木材,也许是竹子,箭头到箭身五厘米处颜色比其它部位深一些,我想是残存的血迹。
我说,在哪里找到呢?我爸说,地里。我说,离尸体多远?我爸说,不到一百米吧。我说,箭旁边有脚印吗?我爸停顿了两秒,说,有。我说,死者的?我爸说,是。我说,三支箭在一起?我爸说,在。我说,还有别的吗?我爸想了想,说,有,还真让你说着了,死者穿的是秋衣秋裤。我把每一处细节记在本子上,我爸问,有什么新发现吗?笔在我两指之间转动,我说,秋衣秋裤?他说,对,秋衣秋裤。我说,您一直跟我说的是她的脚印,而不是鞋印。他有点走神,一会儿才大梦惊醒一般,拍手说,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她光着脚,没穿鞋。样子有点夸张。我继续在本子上记录,我爸问,对写作有帮助吗?我说,有,不过有些地方要重写。他说,重写不怕,反正有得是时间。
记完了,我说,现在我能大体捋出一个脉络。我爸从客厅拉来一把椅子,坐在我面前,说,你说。我说,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凶手和死者早就认识,关系可能非同一般,或者就是枕边人。他说,两口子?我说,有可能,也许是情人。他点点头,我继续说,两人在夜里起了矛盾,更大的可能是死者知道了一些凶手不可告人的秘密,凶手起了杀心,死者意识到危险,从床上跳下来,来不及穿衣服穿鞋子,仓皇逃走。我爸说,就是本来要睡觉了。我说,对。我爸说,凶手拿着凶器追赶?我说,对,应该也没来得及穿鞋子,或者穿的拖鞋,不然追一个光脚的女性,不应该追不上,通过箭的射入深度来看,凶器应该是弩,不然没这么大力道。凶手追不上死者,朝死者射了第一弩,这一下射在肩膀上,所以并没有影响死者的奔跑速度。凶手还是追不上死者,于是大喊,内容应该是蛊惑人心的,比如你只要不报警,或者不对外乱讲,我就放过你,毕竟夫妻一场之类的。死者有点犹豫,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趁这机会,凶手射出了第二箭,这一箭射在肚子上,但仍不足以致命,而求生的本能更加激发了死者的潜能,使她跑得更加迅速。于是凶手射出了第三箭,这一箭射在大腿上。大腿受伤,影响了死者的速度,她急中生智,滚到路边的庄稼地。凶手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死者,他一定就守在路边,等着死者再次出现,一直等到天亮。这时候下起了雨,把之前追逐的痕迹全部冲刷干净。凶手只好返回。死者钻进了玉米地,一时不敢出来,她忍着痛拔掉箭,伤口开始向外涌血,她坚持向前走了一百米左右,倒地不起,最后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等我讲完,我爸拍了拍我的肩,眼神里满是赞许,他说,我儿厉害啊,就这样写,写出来肯定火。我说,现在不着急写,主要是破案的问题,死者光着脚,那奔跑的距离肯定不会很长,这说明什么?我爸说,什么?我说,说明两个人就住在附近。我爸肩头耸动,说,你的意思凶手和死者就是咱村的?我说,至少其中一个是。我爸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背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那咱调查的范围就很明确了。我说,是的,范围还可以再小点儿。他站定,望着我,还能怎么小?我说,咱村谁家里有弩,或者谁用过弩?我爸双手互拍,说,找啊,这就很好查了。
6
下午我爸出去走访,我在家里改小说,脸上的蝴蝶偶尔动一下,试图打断我的思路,我在心里对它们说,安静。它们还算听话,当真安静下来。《父子神探》需要修改和补充的细节,女人光着脚,穿着睡衣,没有化妆,所以夜里仓皇逃出,但她的衣着并不像一个农妇,那么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农村的田地里?这是机智儿子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爸这次回来显得很兴奋,他一边擦着头上的汗水一边说,儿啊,你这脑子真是好使。我说,找到使弩的人了?他说,找到了。我停下笔,问,谁?他说,你先别急,我从头说。前几天村里发生了这么件事儿。我说,什么事?他说,村里跑进来一头野猪。我说,瞎说吧,咱这平原,哪里来的野猪?我说,我开始也这么想,但要不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呢,原来是王彪去山西运煤时,买了两头野猪崽儿,猪崽儿的妈妈,也就是那头大野猪一路跟了来。王彪我有印象,为人彪悍,前几年买了辆大车,跑运输。我说,舐犊情深,它是想救它的孩子。我爸说,应该是这样,野猪在夜里钻进王彪的院子,惊动了王彪,他从窗户里看到大野猪,于是取了弓弩来,朝野猪射了一箭。野猪负伤逃走,王彪一路狂追,后来野猪钻进玉米地,没了踪影。我说,猪崽呢?我爸说,猪崽进了王彪肚子。我甩甩头,不再想猪崽的事情,我说,那王彪具备了作案条件,他有弩,那作案动机呢?我爸说,这就得你来查了。我说,王彪老婆在家吗?我爸说,没在,听说前几天和王彪吵架,回了娘家。我说,死者会不会是他老婆?我爸说,不是,他老婆我认识,死的不是他老婆。我说,那有可能是他情妇,情妇趁着王彪老婆回娘家,来和王彪私会,夜里两人发生口角,王彪要杀了情妇,情妇情急之下从被窝里钻出来逃跑,王彪携了弩箭追赶,途中射了三箭。我爸沉默。我说,王彪平时作风怎么样?我爸说,接触不多,就是爱吹牛,其它倒是没听说。我说,应该着重调查王彪,他有重大作案嫌疑。我爸却说,都是一个村的,万一不是他,还把人得罪了,不太好吧。我说,要不咱就报警吧?我爸突然有点犹豫,他说,算了吧。沉吟了片刻,又说,现在小说能写了吧?我说能写,有这些一手材料足够写小说了。他说,那你就先写小说。我说,那案子怎么办?他说,我再想想。说完就出了房间。
7
《父子神探》中,糊涂老爸发现了尸体,机智儿子经过缜密分析,判定为情杀,在附近村子明察暗访,发现某村的大车司机王某有重大作案嫌疑,王某和情妇幽会,发生了争执,王某要杀情妇灭口。动机呢?激情杀人?好像说不过去,读者不那么好糊弄。我放下笔,望着窗帘出神,窗帘是黄色的,上面印着一只大熊猫,怀里抱着两只小熊猫。现在是晚上十一点,我爸已经睡了。我走出房间,来到院子里,月亮还在石榴树的头顶,看起来摇摇欲坠,院子里遍洒银光,好像一伸手就能捞起一片月光。我想我该亲自调查一番,糊涂老爸虽然做事认真,终究受限于智力,可能会漏掉一些细节。
我悄悄出了家门。最近运动量小,身体有些虚弱,走了几百米就有点喘,走到王彪家门前已经满头大汗。他家新翻盖的房子,黑色的大铁门,门口两旁蹲着两只石狮子,门洞很高,门底下露出老大缝隙,想来野猪就是从这里钻进去的。
我继续往前走,出了村,踏上村口的柏油路,路两边是光秃秃的庄稼地,堆放着成捆的玉米秆儿。月光泼洒在路面上,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我在河里慢慢游动,水的阻力有点大,我走得很吃力,腿肚子开始转筋,脚底板也生疼。
拐上一条泥板路,河水消失了,但是地面坑坑洼洼,我走得更加艰难。这条路我小时候走过无数遍,我就是在这条路上学会了骑自行车。那时候我八九岁吧,我爸带着我去看庄稼长势,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紧紧抱着他的腰。自行车连蹦带跳,颠得屁股疼。我说,爸,你骑慢点。我爸说,骑慢了也一样,路上全是坑,不能怪我。我赌气说,你停下,我自己走路。他说,还有三四里地,走着累断你的腿。我说,那我也不坐这破自行车了。他停下车,腿从车梁上蹁下来,说,给你,你来骑。我跳下车后座,说,我不会。他说,不会就学嘛,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会的。我说,我太矮,上不去。他比划着,你的一条腿从大梁上钻过去,站着骑。我说,我怕骑不好。他说,慢慢就好了。不由分说把我领到车前,牵着我的手握在车把上。我先推着车子摇摇晃晃走了一段,我爸跟在后面催促,上去啊。我说,摔倒怎么办?他说,我给你扶着。他从后面扶稳自行车,我站在自行车左面,右腿穿过大梁,脚踩在踏板上,他说,用力。我用力蹬踏板,自行车向前平稳滑行,他说,左脚上去,我的左脚在地上撑了两下,抬起,踩上左边的踏板。他说,蹬啊。我两只脚交替用力,自行车像一条摆动的鱼,在逆流中奋力向前。自行车突然摇晃起来,在躲避一个水坑时,我失去平衡,连人带车摔倒。自行车压在我腿上,身子倒在泥里,我回头看了一眼,我爸正在我身后几十米外冲着我咧嘴笑,我一下悲愤交加,放声大哭起来。他跑过来扶起我,我挥舞着拳头打他,他说,你怎么这么笨?我说,你不是说给我扶着?为什么撒手?他说,我不撒手,你永远学不会骑自行车。
这条路跟我小时候没什么两样,还是那么多坑,我深一脚浅一脚走着,感觉身体在一瞬间轻盈起来,那些红色的蝴蝶挣脱我的皮肤,在我眼前飞舞,形成一团巨大的火焰,它们炙烤着我,使我浑身滚烫。很快我就看到那片孤零零的玉米地,左右的庄稼都已收割,只有它们倔强地挺立在夜色里。我一头钻进去,打蔫的玉米叶子轻抚着我的脸,痒痒的。蝴蝶被玉米秆儿分割,四下飞散,落到天上,成了星星,它们照耀着我,指引着我,直到我抵达那片空地。
那是一头野猪,它躺在地上,干瘪的乳房和泥土混合。死之前大概有诸多不甘,所以面目狰狞。它的身上磷光闪动,飞舞,也许是萤火虫。野猪旁边有个新挖好的土坑,里面插着铁锹。我爸一定是在等我的小说完成后,再将它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