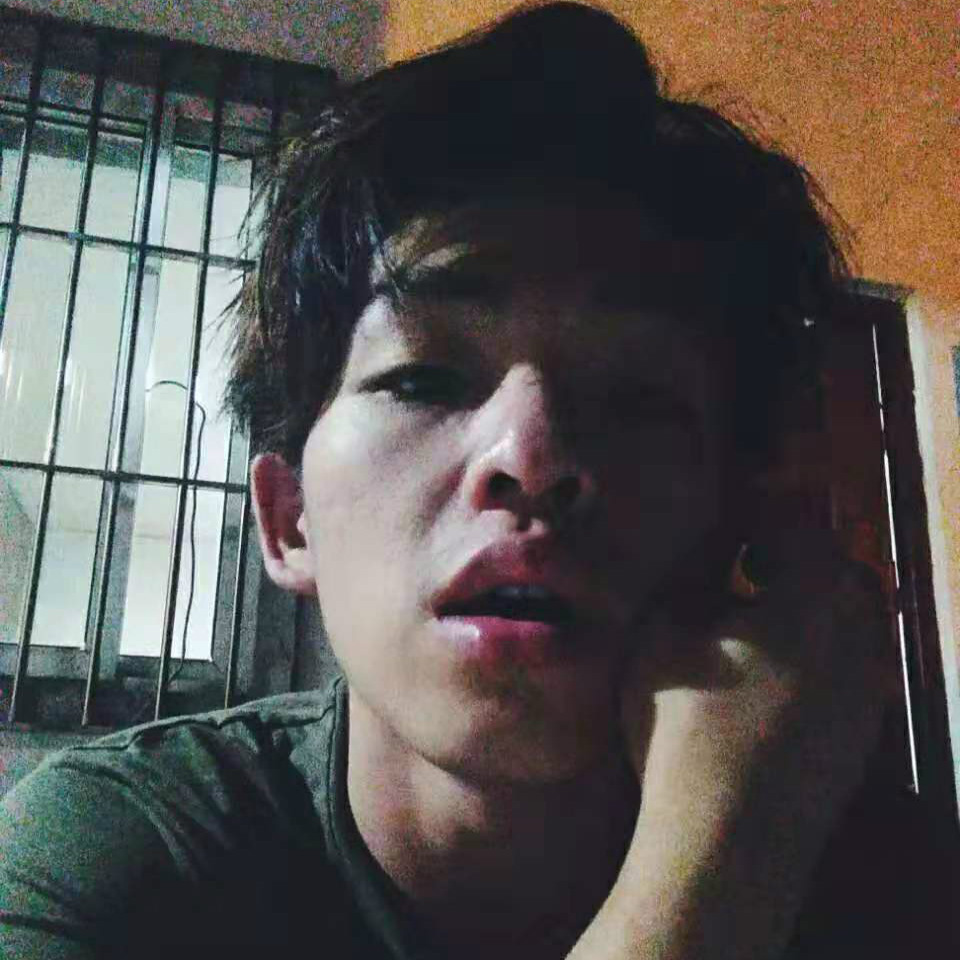何旅订了周日晚上九点二十的机票,廉价航空,从本市新建的第三航站楼飞往很像火车站的家乡国际机场。廉价航空加上廉价时段,比廉价还廉价,他把这票价调侃为空中绿皮车。具体一些的话,是坐到山海关之后补卧铺的绿皮车。他偶尔会怀念绿皮车,每一站都停靠,每一站都有广播,祖国河山,如此多娇,每个大城市都衔着无数小城市,小城市搂着区县农村,回家的一路能听到许多陌生的名字。每听到一个陌生的地名就等于拔掉一根刺,慢慢他从刺猬变回了肌肤柔软的小动物,最后火车哐哧哐哧开过隧道,把他送到被群山环绕的家。飞机则淡薄得多,他上飞机闭眼,中间醒来两次,两三个钟头,家就被推到近在咫尺的地方。不真实,他每次下飞机的时候都这么想。
他半躺在沙发上抽烟,现在流行抽细烟,他坚持抽紫云,上学的时候紫云是烟中珍馐,他只抽过几支,一直念念不忘。挣了第一笔工资之后先买了两条码在家里,每天一包,限量供应,实在瘾大也不动存货,出去买包别的烟顶上。两条紫云永远码在桌子上,如同符号。他抽烟有一口没一口的,烟灰比剩下的部分还长,在指间摇摇欲坠,他把手探出去,略一哆嗦,烟灰散在地砖上。曾经这位置有块地毯,黑灰相间,短绒的,腈纶材质,新买的时候踩上去脚心发痒,心头发热,很让人舒服。后来几回喝多了,连吐带用烟头烫,已经不成样子了,在他把它烧出个北斗七星的次日,女友把它卷起来扔了。何旅酒醒后大发雷霆,抽了她两个耳光,用力过猛,女友一下打成了前女友。现在没人管,烟灰随便乱弹,他开始想,也许那块地毯早该扔。
母亲发来的消息还躺在手机里:儿子,你爸于今天下午去世了,速回。
烟燃尽一支,他又点燃一支烟。他想家里的一草一木,单纯想起,慢慢摆放。他总要提醒自己不能想起的次数太多,否则那就是想念了。想家是令人不齿的事情,更别提要回家见父亲,哪怕是最后一面。对他而言恨就是恨,母亲却总在给他找妥协的理由。想到这儿他把烟掐死,拉开窗户,风很好,他借着外面的光看表,晚上七点,本以为会更晚些,夜晚也许被突来的死亡拉长了。事已至此,想再多也于事无补。他穿上鞋,准备出门喝点,窗户就那么开着吧,生动。
去酒吧的路上他想起了自己的爷爷。爷爷在世时常挡在自己身前,父亲一抬手,老头就眉毛一横,破口大骂,通常以操字先声夺人,后面混搭你妈和你奶奶,不太尊重女性。去世前几年身体硬朗,常穿一双胶鞋,穿梭于街道之间,带何旅时则改变行程,直奔小卖部而去。可惜老头去世太早,没挨到何旅懂事儿,于是对何旅来说,那场葬礼最痛苦的事情就变成了该不该请假。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何旅告别了漂亮的美术老师,被裹进了送葬的队伍中。大人们哭天抢地,他干打雷,不下雨,几次晃神到了美术课上。这回又是葬礼,他还没想好哭不哭,毕竟父亲的遗体还躺在别的女人家里。
酒吧的气氛并不热烈,人人都心事重重似的在遮遮掩掩之下推杯换盏。他叫了杯啤酒,精酿,点精酿的主要原因是酒吧不卖雪花。隔壁坐着一对男女,窃窃私语的声音稍大,正商量着去谁家的问题。何旅听得烦躁,说,不行就去我家吧,没人。男生看了他一眼,正和他的目光撞上,面子有点挂不住,作势要理论一番,女生把他拦住,说算了算了,这人有病,别理他。两人匆匆离开,何旅闷下一大口酒,闭上眼睛,幻想自己跟着他们出去,跟了几个路口,拐到居民区,那应该有盏路灯,一闪一闪的,像在卡巴眼,路边恰好出现了一堆砖头,他随手捡起一块,颠几下。砖头有点坠手,这他能感觉到,接着他快步赶上,对着男生的后脑勺砸去。
咣当,他把酒杯撂在桌面上,长出一口气。
老板,来杯啤酒。旁边坐下新的客人,嗓音有点宽,带着点磁性,似曾相识似的。很多配音电视剧的男主角都有这样的声音,何旅看了他一眼,脸盘挺大,胡茬刮得很干净,浓眉大眼,不戴眼镜,很像配音电视剧里的男主角。何旅想了一会儿,确实不认识。他接着想那个头破血流的男生,想女生在一旁尖叫。具体而微地想,尽量把细节想瓷实了,这让他感觉舒坦。
朋友,一个人?旁边的男人对他说。
何旅抬头重新打量他,三十岁中段,灯光太暗,阴影之下细节不详实。他说,我?男人把手里的杯子举起,说,一起喝两杯?何旅没理他,这人也许喝醉了。他的一位同事,钟爱在酒过三巡后表演魔术,纸币劈筷子,徒手变硬币。另外一个工作认识的领导酒品极差,酒后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小何,女人如衣服,懂不?何旅不爱想这人,想起他时嗓子里像被塞进个鱼钩,总有腐烂的记忆在跃跃欲试,想趁机上钩。他闷头喝自己的酒,攥了攥拳头。
朋友,下杯我请?男人再搭话。何旅说,我认识你吗?男人说,一杯酒而已,非得认识?何旅看他,你啥意思?男人说,没啥意思,就喝两杯,说说话。何旅往后看,酒吧几乎坐满了。他转过身说,那我来杯贵的,事先声明,我话少。男人隔空和他碰了下杯,仰头,喉结一动,喝完把杯子磕在桌面上,声音清脆。其实我今天办了件大事儿,实在想找个人说道说道。朋友,贵姓?男人说。何旅说,章,立早章。男人笑了,说,谢谢,我就是想记住你。何旅说,没必要。你想说啥?男人从裤兜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送到何旅眼前,来一棵?何旅瞄了眼烟盒,不认识的牌子。他听老家的人说过,想害谁就递给他棵烟。他自审了一下,接过烟,凑近了接男人另一只手上的火儿。火光映衬下,男人的脸显得十分温和,无害,像是许久未见的老朋友。
你知不知道伊朗·阿明?男人说。何旅说,不知道,干什么的?男人说,不知道也没关系。一个独裁者,暴君,非洲的,性格反复无常,老婆能组两个班,子女加强连。谁不听话咔嚓一刀,头砍掉,哐哐哐,身子切成几段,煮了吃肉,吃完了还得念叨两句,太咸,加点糖好了。何旅说,这是真事儿?男人说,也可以是个故事。人一死,什么都成了故事。我忽然想起来的。何旅说,有点猎奇,像地摊杂志写的。男人说,也不尽然。何旅说,怎么讲?男人揉了揉后脑的头发,说,人和人的相同点总多过不同。算了,这故事不讲了,没意思。你再喝点什么?何旅说,随你。他听出来了,这人有东北口音,算三分之一个老乡。
男人说,那就聊聊我,听不?何旅说,都行。再给我棵烟?男人敲出一支,递给何旅,说,我这故事有点复杂,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何旅点头。男人说,我家原来有个店,刻章的,刻私章,也刻公章,主要业务是私刻公章。给塞二百块钱,我爸啥都敢刻。后来逮到几次,罚了不少款,牌匾就改了,刻章两个字中间塞个小字,私。面子工程,塞五百,还刻公章。何旅笑了,说,胆挺大。男人说,可不,为了挣钱都是。下岗买断这点钱全盘了这店了,也不会干别的,就这一门手艺。好在稳稳当当,挺有匠人精神,你多塞点,还给你做旧,抠几个豁儿。那时候穷是穷了点,但是挺幸福,一家三口。何旅说,你挺有意思。男人说,咋的呢?何旅没吭声。男人说,反正咱俩也不认识,现在离半夜还远,瞎聊呗。
何旅点点头,问,之后呢?男人说,之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何旅说,你爸。男人说,啊,我爸之后不太顺利,进去了。出来之后严令禁止我爸再刻章,营生没了,他就天天喝大酒,昼夜不分,醉生梦死。喝了大概两个多月,我妈和他闹离婚,两人大吵一架,好话赖话顺嘴胡勒,结果我爸一气之下,自杀了。何旅不知道接什么话好,抿了一口酒。男人说,别吃惊,没死成,非得横穿马路,想整个意外事故讹点钱。结果一上道,车都让着他走。灵机一动,改蹲在公交车站点,哪辆车出发就往哪辆车上贴。也没成功,让司机一顿臭骂,硬坐了好几站,下车还得原路走回来。到家越想越憋屈,气得够呛,多喝二两散白。
男人说完喘了口大气,摇摇头,对何旅说,想笑就笑吧,我说着都感觉招笑。何旅说,你爸不容易。男人说,不容易,属于和生活斗争失败了。我和我妈离开他仨月不到,喝死了。嗨,出殡时候给我热够呛。何旅说,夏天?男人说,深秋,离冬天不远了,也就这么个季节。天气不热,烧纸的灶子热,风大,吹得纸钱满天飞,都带着火苗子。往里续纸时热气往脸上砸,连灰带汗,在脸上都滚成泥汤儿了。我还得念词儿,三条大路您走中央,西南大路亮堂堂。旱路您坐车,生安亡稳回故乡。水路您乘船,保佑儿孙福满堂。这点泥汤儿混着灰全进嘴儿了。何旅说,东北都这样,讲究多,你又是儿子,该送送他,尽孝嘛。其实咱俩属于老乡。男人用手拄着下巴,说,我知道,你说两句话我就听出来了,有缘分。干听我在这巴巴了,要不你唠唠?何旅说,唠啥?男人说,唠你自己,唠别人,随便。
何旅他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什么事都有个动机。后面常接着你偷我两块钱的动机是什么,或是你今天不写作业的动机是什么。他抽烟是为了思考,喝酒是为了放弃思考,烟和酒,好朋友,两个配在一起能想起该想起的,也能忘了该忘了的。他不清楚这男人请他喝酒的动机。不过这不碍事,喝完这杯,再喝一杯,酒精会在凌晨占领头部,新的一天就到了。那时候他会直接回家睡觉,把这人连带他的动机抛之脑后。
我没有有意思的事,何旅说,想不出来。男人说,随便说,随便想,没事儿。再来一支?何旅摆摆手,说,不来了,这烟配这酒,发苦了,抽完口干。男人说,行。寻思给你打开打开思路。何旅说,不用,我就顺着你话头说。男人说,讲究爹?何旅说,对,不过我爸没你爸那么跌宕起伏。男人问,身体还行?何旅说,刚没,后天出了,票我都买好了。男人说,不好意思。何旅说,没啥不好意思的,多年不见了,生老病死,都有准备。说实话,比起难受,我心里更像是踏实了。男人说,我懂,病久了。何旅说,也不是。男人说,明白,他在你心里早死了。何旅说,说不清楚。我爸文化人,写一手好字,教初中语文,早些年还教政治历史。人其实不错,穿得板正,五官端正,声音也好听。谈什么必引经据典,你说错个音,一定当场纠正过来。这一点不管面对谁都一样,有点病态,开大会当面揪过校长的错误。校长当场就把我爸表扬了一顿,转头把人叫到校长室,扇了四个嘴巴子。就那天回家,我背诗背不下来,白日依山尽,黄河怎么也入不了海流。我爸肿着两面脸皮,给我来了两个热乎的耳贴子,骂我有辱斯文。
何旅说完叹了口气,摸了摸两边脸,隐隐感觉被扇过的余热还在,也可能是酒精上脸了。男人说,这嘴巴子应该算校长头上。何旅说,没啥,家常便饭了。男人说,是,棍棒底下出孝子,都这样。何旅问,你信吗?男人说,出孝子?何旅说,嗯。男人说,狗屁。你先等我会儿,我出去买包烟。何旅说,出门左转,五十米左右,有个便利店。男人点头。
何旅往椅背上靠了靠,吧椅的椅背很小,弱不禁风,后背贴在上面总觉得不实诚,感觉随时都会倒过去,头撞在桌角之类的地方,脑震荡再震荡,里面摔成一片糨糊。他在想谁能把他送到医院,关键是,谁能来看望他?前女友一定不会来了,她现在说不定天天刷着朋友圈,备好鞭炮,等着他的讣告。接着他想到死去的父亲,想到他们俩至死也没再见面,想到母亲也曾像自己一样坚定,想到他的另一个家。何旅叹了口气,换了个安全点的姿势,闷掉最后一口酒。
男人回来时身上附着了夜晚的空气,稍微改变了氛围。男人说,我抽烟不抽最后两根,留个底儿,要不心里不得劲。何旅点头。男人说,不好买,多跑了两条街。差点迷路,外面挺冷,你穿这些出门得裹紧点。老家今天都上冻了。然后他把烟拆开,点了一支,随手把烟盒放在桌子上,撕开的口对着何旅,说,咱俩唠到哪儿了?我跟没跟你说,我有个后爹?何旅说,没说过。男人把袖子一撸,说,这酒吧人不少,我看还往里上人呢。何旅说,开到三四点,氛围还行,没有戗毛戗刺的二流子。
男人点点头,磕烟灰,说,我后爸,其实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从生理上讲,他是我亲爸。但是我小时候那会儿,他就是我爸不在家时,老来串门的一个叔。反正就按顺序叫吧,方便。对了,我叫你老弟行吗?瞅着你比我年轻。何旅说,行,都行,我有点乱。男人说,老弟,我那个死了的爸是这个,知道吧?男人比了一个乌龟的手势,接着说,丧盆子我摔稀碎,也算对得起他了。你说这玩意,爹还有失而复得的,世界多他妈奇妙。何旅说,懂了。男人接着说,我这后爸,不是个物,天天和我妈干仗。我妈脾气也爆,多少能支巴两下。无所谓,主要是他俩干仗,我妈就没赢过,今天头开瓢,明天眼睛肿老高。说实话,打挺狠,医院没少跑。何旅说,那咋不离开他呢?男人扔掉烟头,啧了一声,说,能离开就好了,我俩住的房子是我后爸的,楼不是啥好楼,家属楼,破窗破门破家具。但是离了这破地方,我娘俩就没地方住了。
不如就去我家吧,没人。何旅突然冒出一句。男人一愣,拍了拍何旅的肩膀,说,老弟喝多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但是谢谢你啊,我现在挺好的。何旅说,没事儿,酒有点上头,我再喝一杯吧。男人又叫了杯酒,说,喝完这杯别喝了,适可而止,人一喝多了,难免就丑。唠会嗑,挺高兴的。何旅说,是。男人说,反正吧,从小到大,我家什么东西都是旧的,就一样东西新,你知道是啥不?
何旅说,啥?男人说,凳子,木凳子,铁凳子,那时候没有塑料凳子,你说为啥不生产塑料凳子呢?轻飘的不占地方,还便宜。那些厂子咋寻思的?何旅说,可能铁的结实。男人说,对,坏就坏在结实上了。你坐过吧,铁凳子,三个腿,铝管儿的,早先有些自制的,凳子腿实心儿的。上面弄块硬塑垫子,硌屁股。何旅说,坐过。男人说,就这凳子,巅峰时期,我家一个月换三回。何旅说,咋的?男人说,我感觉,这凳子能坐一辈子也不带坏的。我后爸,就用它打我妈,凳子能活活打散架了。男人做了个用手抓东西的姿势,向前用劲儿挥了两下。我只能拽着他裤腿子,跪着求他。男人用手扶住额头,叹了口气,说,没用。他两只手搓脸,叹了口气,扭头看着何旅,轻声哼了一下,不知是笑还是痛苦,他说,后来你知道还换过啥吗?何旅和他对视,咽了口唾沫。
男人说,菜刀,炉钩子,锅碗瓢盆,炒勺。见啥拿啥,菜刀使的刀背,砍得我妈头上都是软的,感觉一按能出水儿。何旅说,这人该死。男人说,是吧,该死,我那时候特想弄死他,干不过他,一扒拉我一个跟头,他打我,我妈就抱住我,结果挨更多揍。我说,妈咱俩跑了吧。我妈说,儿子,咱们往哪儿跑啊,咱们娘俩能去哪儿啊。我说,妈,我弄死他。我妈一把搂住我,说儿子,我就想让你好好活着。完后我就哭了,我妈也哭了。
何旅想起父亲,自从被学校开除后,性情大变,原形毕露,左手圣贤书,右手擀面杖,拳打妻子,脚踢儿子,仿佛他们才是他出轨的罪魁祸首。不幸的人也有相似之处,他想,起码眼前这人的恨还有处宣泄,从这一点来看,他比自己幸福得多。自己的父亲没经过自己的同意就擅自死去了,更不屑于希求自己的原谅。
是不是没啥意思,这故事?男人说。何旅说,没,挺有意思的。我意思是,我能理解。男人说,这事儿我不爱说,可是也不怕说。我们没啥错。我妈最开始也不知道他有家,后来也没想到能把他工作整没。谁也没想害谁,可是事儿它就这么发生了,你有什么招?何旅问,后来呢?
男人说,后来,也没啥,那头的家回不去了,人家说啥都要离婚,他就跑来和我妈过,也没领证。我不乐意,我妈非说他都改了,没招。但是动手次数少多了,我怀疑也是因为我长大了,他有点怕我。我书包里永远揣把西瓜刀,开刃的。他瞄到过,我故意露的。再后来,我就出来了,见他的机会也少多了,我这辈子都没认过他,一直管他叫叔。我现在都有孩子了,姑娘,五岁,挺可爱的,你应该看看,招人喜欢。活泼好动,背古诗小嘴巴巴的,已经背到小学三年级的古诗词了,聪明,有点遗传我。就是到现在还没见过爷爷,奶奶视频里看过,爷爷一露头,我就把视频挂了。真的,还是恨他。我妈非得和他过,做子女的,也没法说。何旅说,可能就是做个伴。男人说,这人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从来都没听他说过一次对不起,我总怀疑他还打我妈,我看我妈那个脸色,不是好颜色,眼角一整发青。咱也整不明白,个人选的路,个人走吧。
男人用食指和中指敲桌面,发出笃笃的声音,眼睑低垂,眼睛左右动,在想事情。大概半支烟的时间,他说,不过我把他杀了。
男人说完停了下来,似乎在观察何旅的反应,但是他眼睛一直落在杯子上,随着气泡上升,下降。周遭的声音霎时静了许多,何旅听到身后的两个男人在谈论鸡,农村鸡,城市鸡,价格口味,市场表现,发展前景。侧面的女人咽下酒的声音很轻,吞咽动作也是分性别的。酒吧的远处还有人在讨论埋的问题,也可能是霾,听不大清楚。周围的分贝似乎低了许多,又似乎没人侧耳倾听这男人刚才的话。
何旅犹豫了一下,克制住了从椅子上弹起来的冲动,他说,别拿这个开玩笑,哥。男人眼睛里的情绪随着一个硕大的气泡腾空,不是开玩笑,字面意义上的,我把他杀了。何旅往左右看了看,确定他们是无人关注的。他问,啥时候的事儿?男人说,今天下午,新鲜热乎的。一搓手还能感觉到他的呼吸,粗,重,像旧风箱,像让风穿透的破鼓。何旅说,哥,这是文学作品?男人说,鸡巴作品,真人真事,亲身讲述,如假包换。何旅说,哥,你先喝口酒,好好寻思寻思,没啥过不去的坎儿。男人说,老弟,我没疯。何旅说,你先喝一口,压一压。男人说,你放心,章老弟,咱俩萍水相逢。这事儿是我自己的事儿,跟谁都挂不上,刮不着你,碰不着你,我就是想找个人说道说道,憋着难受。何旅没吭声,男人的手有点抖,烟灰窸窸窣窣往地上掉,剩下半截烟屁胆战心惊地燃烧,男人喝了口酒,说,你没说错,的确发苦,发干。
何旅说,哥,你说得对,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可能觉得你认识我了,但是你也不是真认识。有一点我能确定,酒挺好,剩下一点我确定不了,就是你的好坏,我活了三十年,看不准人。但是今天酒喝到这儿了,你既然憋屈,那就敞开了说。我可以当小说听,也可以当真事儿听。我可以记住,更可能是忘了。这都由你决定,你也放心。男人说,明白。最后一杯,喝完各回各家。何旅说,那今天是咋回事儿?男人说,今天?其实我不是有心的,可以说是失手。何旅说,你不想杀他?男人说,不是,我想,但是今天没想,本来没想。他都瘫了,不行了。老弟,你见过快死的人吗?何旅说,没见过,本来有机会。
男人说,我后爸,我见他时候,他都迷糊了,说话断断续续的,不认人。说是病灶已经转移了,多点开花,分店遍布全身。我见他那会儿,估计脑子也被占领了。但是还往出蹦字儿,拼不出个数,都不是整句子。他说,水……水……我就把水送到他嘴边,倒进去一点点,怕他呛到,结果这点水都让嘴唇吸收了。他整个人还是干枯的,我一看就明白了,没救了,就跟用水壶灌溉沙漠似的,没用。往里续了半杯吧,忽然眼睛亮了。跟我说话,说孩子,这怎么飞起来了。我说,啥飞起来了?他说房子,房子飞起来了。我知道这是出现幻觉了。他又说,雪怎么这么大啊,咱们飞到哪儿了。我说,飞到对流层了,马上进平流层,进去能暖和点。
他点点头,脖子梗着,维持着僵硬,好像在向外看,又好像没看。过了半天,终于缓缓把脖子放松,躺了下去。后来断断续续醒两三回,最后一把醒来,往四周看,屋里就我俩,他瞪我,眼珠子锃亮,他说,小逼崽子,你看我整不整死你。我说,叔,你说啥呢。他说,小逼崽子,你不是偷我钱,和你妈合计害我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说,叔,你误会了,都过去了。他说,都他妈赖你,我就该掐死你。我说,叔,别的。他说,掐死你,啥事儿没有,我看你妈还跟不跟我过。然后他把手从被里探出来,动作幅度很小朝我伸过来,抬起来几厘米,意思是要掐我。章老弟,你可能不明白,这么多年了,哎呀。我当时不知道咋回事儿,一股火就上来了。他一直在那骂骂咧咧的,我就用枕头把他脸捂住了。本来想堵他嘴,越堵越骂,越骂我气越大。最后,堵了一会儿吧,终于消停了。
何旅深吸一口气。说,人呢,现在在哪儿呢?男人说,家里,医院早就不给治了,占用资源。家里等死呢,现在算是等着了,美梦成真。何旅说,你也不算故意的,意外都是。男人喝酒,说,间接故意,你要说第一下不是故意的,的确。后面堵那几分钟,要说我一点整死他的心都没有,我自己都不信。何旅说,我感觉就算你不捂他,他也活不长了。男人说,过不了今晚上,那时候应该是回光返照,口齿清晰,就是脑子还不大灵。何旅说,何必呢。男人说,你呀,就是想得太少。何旅说,啥意思?男人说,没啥,喝酒吧。
夜风很凉,街上已经接近全黑了,远处主路上的光像是从遥远的岛屿上传来的,中间隔着无法游过的海峡。他们又抽了半盒烟,聊了近一个小时,酒吧的老板头靠着墙壁,微微打盹儿。最后一杯让何旅醉了,男人结账后和何旅互相架着,坐在路边望向远处。何旅说,哥,这事儿,我帮你保密。男人说,嗯。何旅说,哥,咱俩同一天没有爸,咱俩属于兄弟,你明白吧?男人说,不一样。何旅说,哥,啥也不说了。我先上个厕所。
何旅摇摇晃晃站起来,走到街角,背对着街道褪下裤子,风吹得他一哆嗦,一股尿呲到脚上了。男人也在街的另一边撒尿,两股声音叠在一起,此起彼伏。何旅喊,哥,你要上哪去?男人回他,回家。声音在路的两头荡来荡去。何旅傻笑了一会儿,提上裤子,往男人那边走去。他想起了父亲在这样的夜里面,摇摇晃晃,推门回家,父亲会即兴来一段歌,然后把何旅揪起来打拍子,顺便背段古诗词。那时候多好啊,背段古诗就不用挨打。何旅拍拍男人肩膀,说,哥,你家住哪儿,用不用我去帮你忙?男人说,不用,老弟,我一个人的事儿。何旅说,外道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男人说,是,但是问题也得分开解决。何旅两只手抱住男人的肩膀,说,哥,那就在这分开吧,祝你好运。
何旅晃晃悠悠往回走,抬起手腕想要看看时间,卖表的说他表针是夜光的,结果只有在夜里有光的时候才能看清。他把手机掏出来,打开手电筒,照着手表,看了半天,两点二十。有条微信,五个小时前发来的。
母亲说:儿子,你爸不是自然死亡,警察初步判断是他杀,有窒息痕迹。为配合调查,我已去你三姨家住,勿念。
风很凉,他被吹了一个激灵,浑身冒汗。他把这几行字反复读了三四遍,一个不现实到现实的想法出现,膨胀,挤压出酒精,填满了脑内的每一条沟壑。男人的脚步声正在变轻,变远。他拔腿往回跑,边跑边喊,哥,哥,等一下!脚步声消失,男人站定了,大半身子沉在黑夜中。他们隔着一条马路,何旅说,哥,我还不知道你姓啥。男人的嗓音有点飘,他说,我姓李,也姓何,现在主要姓李。对了,刚才忘跟你说了,我建议你最好别回家。听哥一句,有挺多事儿,知道了不如不知道,你好好想想。说完他转身走了,何旅站在路口,听着自己的呼吸声慢慢变重,远处孩童的啼哭,近处风声的呼啸,都在逐渐清晰。这是他人生中最敏锐的一刻,世界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灌进了他的灵魂里,幸福和不幸交织,羡慕和仇恨重叠,他觉得自己能看得很远,能跨越时间,能跨越距离。
他悄无声息地跟着男人走,走过长江一路,穿过建设街时捡了块大石头,心跳剧烈,最后沿着幸福大道走,走了不知多久。他听到水声激荡,天色正在放亮,现在是时候了。他从外套兜里掏出已经捂热的石头,加快脚步,左手拽住男人的后脖领,右手扬起,用尽全力向男人的后脑勺砸去,一声闷响,又一声。男人没来得及回头,便直挺挺地往前倒,带得他趔趄了一下。何旅把他翻面,探了探他的鼻息,半天没有感觉,扶着他脑袋的左手感觉到了温热。男人的后脑发出咕哝咕哝的声音,血正向外涌。何旅脱下外套,包住男人的头,用袖口在脖子处打了死结,这时男人的胳膊抽搐了一下,一把将他抱住。力度巨大,挣脱不开。男人嗓子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喉音,他们用这样怪异的姿势拥抱着。半晌,一口气舒到尾声,紧绷的胳膊垂了下去。何旅起身,把尸体拖向河边。
他拖得很吃力,中间歇了几气儿,河流的声音忽远忽近,像在刻意捉弄他。东方泛白时,他终于到了河边,水声吵闹,听得耳根子发痒。他烟瘾犯了,摸了摸兜,里面什么都没有。他弯腰去摸男人的裤兜,掏出烟,点燃,猛吸了几口,觉得口感很像紫云。吸完烟轻松了许多,他想起了自己的前女友,那时候不应该打她,那块破地毯早就该扔。前女友现在应该正躺在安全,温暖的梦里。他觉得从今往后,不会再有任何人受到伤害了,想到这他觉得安稳,干脆闭上眼睛,躺在了河沿儿上。
再睁开眼时天已全亮,但太阳仍掖在地平线下。清晨的空气丝丝沁过衣服,不远处有人晨练的脚步声。何旅赶紧向旁边看,后脊发凉,男人的尸体已经不见踪影了。他站起来环视四周,没有任何痕迹。这时候他手机响了,他解锁,点开。
母亲说:回家时在省城停一下,把欣欣接回来。
何旅回:欣欣是谁?
母亲说:何欣,你爸那头的孙女,你的侄女,虽然没见过面,但始终是要回家的。世上有许多错误,但总与孩子无关,这事你听我的,不要固执。欣欣他爸会和你碰面,你不要不礼貌。爱比恨更难,但也更轻松。
何旅放下手机,茫然四顾,清气变浊,一切都成了不规则的形状,带着似是而非的嘴脸。他感觉自己是初次降临在这个世界的婴孩,寒冷,瑟缩,不知所措。他用意志撑着自己站立,摇摇晃晃,试图分辨清楚眼前事物的声音和形状。终于,他颓然瘫倒,一屁股坐在地上。
一个人从右边搂住他的肩膀,胳膊温热有力,这人说,你呀,就是想得太少。
他听到这声音,有点宽,像是配音电视剧男主角的声音,像是父亲,他扭头看,男人正对着他微笑,那张脸上的皱纹在快速蔓延,面目逐渐模糊。然后他转过头,望向河面,汽车正从河面上驶过,水花溅在轮胎上,有鱼和水草在河里起舞,燕子推开水波。它们沿着同样的方向流动,一路向北。在河流的尽头,朝阳正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