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与社会有种隔离感怎么办?
感觉与社会有种隔离感怎么办?

第一眼看到脱节这个词就觉得跟自己很搭,无时无刻不有脱节的感觉,自从社会人格建立伊始,就把自己归于边缘人序列,从不参与主线,支线也属于边角料类型。倒是活得安逸,有一种得过且过的凑合感,但样样也在努力应对。应对这个词也消极,还显得有些不负责任,但就是这么回事。
谈起社会,五花八门,天南海北的,时代的,科技的,常识更新的,今儿哪里冒出来个未知彗星,多少年后近地。什么电影上映了,没看过都融不进那个闲谈的圈子。政治大亨爆了丑闻,颠覆了认知。明星意外陨世,留下超级大额遗产。这些东西忽近忽远,在大大小小的屏幕里制造与己无关的情绪实体,有兴奋的有焦虑的,真如巨大的染缸,个个不管拒绝与否,都深陷其中。与社会脱节,也许本来也只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围墙始终建在你的外面,你再想逃,也只是扩大了距离,而丝毫跳不出去。
相反,与社会脱节,在我来看,却是一个美好而有些奢望的追求。巨大的抽离感是深层灵魂吐纳自我的必要土壤,外部所谓社会的纷杂干扰更像针刺,时刻让你不得不保持格外的参与感,仿佛你的存在是必不可少无可替代的,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众所周知的,你的自我价值就在巨大的PUA下蠢蠢欲动,萌萌欲发。真相格外残酷,老话也常言,地球没了谁都转,社会不以个人为转移。当然如果量级够大,那话另说。
多年前关注过一个人,孙心圣,名字大概是这,三十来岁,接受过电视台采访,进过大学讲堂,属于八十年代的行走圣经。一个人背着包全国转悠,其实跟流浪也差不多,头发蓬乱,胡子拉碴,桥洞,树丛,公园,旱厕,都睡过,但心态极好,不向往日常规规矩矩的社会生活,内心算是有浪子的大智慧。看过几段采访,谈吐说话逻辑非常清晰,那时候可能稀奇,没有直播,也没有假直播,流浪还是过于先锋了。也谈到留在某地认识了姑娘,擦出爱情的火花,但最终还是无法抗拒出走的命运,实在的社会太无趣,于是选择再次远游。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大概也算主动脱轨的一类人。
二〇一三年暑假,我从成都出发,骑着自行车到拉萨,走川藏线,历时二十四天。期间手机几乎不用,完全撇去社会关系,做好净身的准备。路上遇到几个搭子,目的一致,心灵无比单纯,大家在或是宽阔或者狭窄,一会儿暴雨一会儿烈日的道路上猛瞪着双脚,全似离弦的箭,射向大社会的反面。这群人也很有意思,初衷也是各不相同,算是苦修,也算是挑战,那会儿并没有直播的说法,记录在我们看来也并不重要,就是去看布达拉宫,一路上感受临时的脱节,这被我誉为是最为接近神性的手段。在一个下山的途中,我接到一个电话,于是刹车,将自行车推到一处草坡,头顶是半环绕山腰的云,护栏外是湍急的河,电话里说,孩子期末考试不太行,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办法,能不能来家做几个辅导?我简单答了几句,肉身像被瞬间拉回去,在办公室里坐着,眼前是成沓的作业,红笔漏了点墨,对勾的一角浓重。挂了电话我把手机关闭,自行车链条的吱啦声划过耳际,远处的道路变成了渺小的一个点,是靶心也是出口。我重新骑上车。
可能是工作原因,有大段的社会空白,每个假期我都像与社会脱节,完全沉浸在某项活动里,或精神或肉体,日子也开始过得糊糊涂涂,丝毫没有时间观念,睡眠变得破碎,懒惰成为见缝插针的偷袭者。但无比享受整个过程,无外人打扰,和不以任何其他强加情绪为转移的自由无束,难得可贵。与社会脱节,还是与社会接轨,也并没有自我想象的那么重要,焦虑的可能是自我难以平衡的状态,如果你现在正在丧失某种参与感,那就享受自我被疏离和排斥的孤独,那是来自内心遥远的召唤,往往随后祥和的情绪便像一汪止不住的泉水,汩汩向你温暖地涌来。
责任编辑:梅不谈 onewenti@wufazhuce.com
征稿信息见微博@ONE一个工作室 小红书@ONE一个编辑部 置顶内容。
回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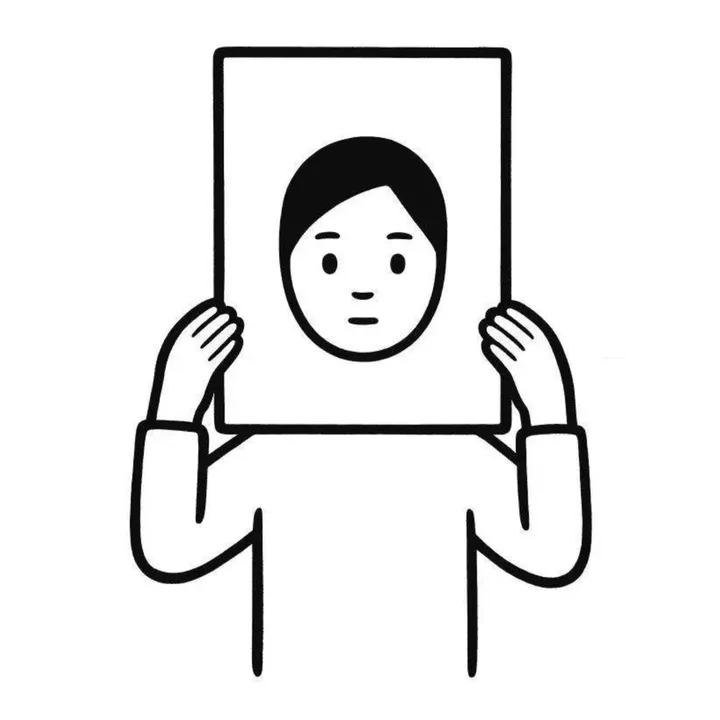
|
西小麦 @西小麦打字中
一个写字的。
|
相关推荐
| 问答 |
从小到大,你经历过什么样的语言暴力?
|
| 问答 |
读很多书可以改变人生,是不是一个骗局?
|
点击可下载ONE一个ap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