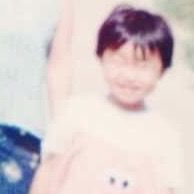没有人知道,我回去过多少次。也没有人知道,我回去经历过什么。曾跟朋友们聊过,在微信群,用大段大段的文字。朋友们总是回:哈哈哈哈哈。
各人有各人要回的地方。也许,是推门就被热汤暖雾揽入胸怀的地方;也许,是旧钥匙插不进新锁孔的地方……归途之情怀几许,难得他人遥相呼应,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浅浅在此记下几回,博君一“哈哈哈哈哈”。
其 一 回
寒假,领着一队导师同门。他们第一次来井镇。如果没有我,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来井镇。其实每次我用井镇所属的地级市介绍自己的家乡时,内心都不是百分百认同自己是这个市的人。我从小到大去市里玩的次数屈指可数。不过,当发现别人知道我的市,甚至能说出市里的特色,我还是惊喜。毕竟我们市的名字,不在高中地理书上。然而当我进一步介绍我的县、我的镇时,便再无人知晓了。
这次来我的镇,一是带着科研目的,二是趁寒假感受本地独有的风情。
没想到一进井镇就把他们震住了。
春节将至,街边成排的早餐店,只剩一串格子状的空地。井镇把这排早餐店的老板叫作“过早帮”。他们是湖北人,在全国各地做早餐生意。一般不会单打独斗,而是一家挨一家,一起占领当地最繁华的地段,在异地他乡彼此照应。后来他们有了资本,买房置业,为了两地生活方便,就把一排店做成了一列车。每一节车厢就是一栋房。每年春天磬磬哐哐地开来,列车驶进街道的港湾,停妥,开门,就是一排早餐店。每年冬天轰隆隆开回湖北,过年。车走,就剩下这串空地。
导师同门视此为奇观,驻足不前。我振奋地催促他们,去我家尝尝奶奶的厨艺。我带他们走街串巷,边走边介绍等会儿会吃到的美食。他们跟我一样期待。
可刚要出水井巷,我们立即缩回脚步。眼下,一道几十米高的悬崖,刀切过的白萝卜一样,脆生生地立在井镇。这里曾是沿坡而筑的街道,井镇处于丘陵地带。我过去懒于爬坡上坎,羡慕平原的城市。没想到井镇如今也平了,只是平得太奇葩,坡下推得一川平,徒留坡上的房子矗立在悬崖。为什么会这样?我问旁边的人家。他们说,坡下建新镇,坡上留老镇。这么高的悬崖,从哪条路下去?他们说,没有路,因为我们镇的人都会飞了。
我不会飞,我再也不是井镇人。其实我早已不是,我从初中就离开井镇,户口迁移到县城,大学又考去外省,一步一步,被动主动地离开。我被井镇惹生气时,会发誓再也不回来。后来回来过很多次。回来,就像打扫卫生时翻出柜子深处一叠蒙灰的信件。是我的,又差点不是我的。有意义,又没太大意义。可以扔,又不舍得扔。信件里的字眼,陌生又熟悉的回眸,需要怎样的翅膀,才能安全穿梭于眼尾的闪电?
导师同门不会飞,但是不伤心。他们再次为井镇叹为观止,顾不上我的心情。奶奶来电话说饭好了,等我们。让她想办法来接我们,她来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悬崖边徘徊两个小时。家里的饭早已凉了,奶奶没有再来电。导师同门也不急,只有我一个人在焦灼。我想纵身一跃,看自己是否会飞。导师说,走吧,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就是出路。
不回家了。转身直奔我们的科研目的地,井镇乡下的清风洞。清风洞在夏季往外送冷气,是井镇人的避暑胜地。现在是冬天,清风洞门口的凉亭茶馆空无一人。我们越往里走,越暖和。洞内怪石嶙峋,豆大的探照灯下,我分不清物体的大小,分不清时间的快慢。我们在洞内谈天说地,洞就是天地。我们的歌声被或近或远的石壁弹回,奏成多重唱的回音。我恍然有了论文的思路。我们是哲学系。
从清风洞出来,我坚持要请导师同门吃饭,以补地主之谊。在一个老旧的小饭店,他们终于尝到井镇的风味。趁着酒兴,学术探讨天马行空,我为眼前的一切满意,远方和起点在此刻形成闭环。
但生活太擅长扫兴。坐我左手方的师兄,一个高高胖胖的北方人,在酒精的显影下,有东西从他的温和亲近里暴露凸出,像钟乳石,在桌下硌着我的身体两侧。我被挤压在中间,只能呼,不能吸。挣扎,尖叫。桌上仍是一派其乐融融。在座没有一个人帮我。
直到我穿越回小学校园,空气才开阔了。
天气不冷不热,几个老同学在骑一辆自行车,她们都说其中一个怀孕了。我为这个消息高兴而失落。曾经我们那样要好。
一个家里开理发店的同学夸我大卷发好好看。我不信,我没有做大卷发,我是短发。她举起两把镜子,一前一后。我看到我的背影,亚麻色的发卷是被轻风拂起的波浪,微微一层,好看得不像我。在我还没来得及为变美而骄傲时,镜子里宽大丑陋的额头抢先让我自卑。除非对面部大动干戈,否则我不会变美。我再一次陷入原生自卑的重复。
老同学们被沸腾的人声吸引走开,俯在操场边的栏杆上,看校门外的车水马龙。这是井镇的新现象。一到周末,人潮奔涌着去隔壁的几个镇打工挣钱。经济下行啦。同学说,她周末在隔壁镇的发廊挣很多,数字之巨大,让我重新审视洗头发这份工作的技术含量。同学看出我的疑惑,坦白是灰色收入。我理解了。她说那儿很繁华,像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值得我去看看。她们不知道,我去过。
其 二 回
有次回去是傍晚。面包车拐进井镇客运站,一条金鳞大鱼映进挡风玻璃,霞光照眼。我正下车,车顶上沙沙沙,像大米撒进铁盆。下雨了?却见路人跑过来,路边店铺的人也跑出来。生面孔不少,熟面孔更多。
薇姐也在人群里。“咋了?”我问她。
“下饵了。井镇今年是饵季。”她来不及正眼看我,佝着腰,一手举盆儿接饵,另一手不闲着,拣起地上的。
很快,天上的饵停了,地上的饵也被人拣完了。天地干净得如梦初醒。
细看盆中的饵,土黄色,鹌鹑蛋大小,形状不规则。薇姐说:“今天的饵泡酥酥的,人们爱吃这种,闻到气味就都来了。要是太硬扎,香气散不开,远处的人还没注意,近处的人一下子就抢光了。”
“来,幺妹。”薇姐递给我一颗饵。让我想起小时候,每回在街上碰到她,只要我叫她,她就会从零食袋里掏出一根虾条,或是一块锅巴,又或是一枚巧克力圈……递给我说“来,幺妹。”
“井镇以前不下饵呀!”我尝着饵的滋味,是醇醇的谷物香。
“今年开始下的。饵季刚来那会儿,掉下的饵可大个了,一张嘴都包不下。吃完一颗,十天半个月都不想吃。后来天上就不掉大饵了。”薇姐品味着她的饵,“不过也不会太小,太小,人们懒得拣。”
“为啥会下饵呢?”
“钓人噻。”薇姐扑扇睫毛。这么多年不见,她的眼睛还是那么有神。她毛发旺盛。有次我们偷偷去乡下的清风洞玩耍,她偷偷谈的男朋友骑摩托车来接我们。她把下巴枕在男朋友的肩膀上,手臂揽着男朋友的腰。我坐在她背后,看她又多又粗的头发,用漂亮的筷子挽成坨,翘起的发梢因为拉直过,像一把稻穗高扬。吊带背心上方,裸露的皮肤很白很香,后背的汗毛根根分明,像是铅笔描的。“不晓得今晚是谁被钓走。”薇姐说。
“人被钓走?被谁钓走?”
“不晓得,没人见过。被钓走的人都没回来。”
“谁被钓走了?”
“多得很。街上、乡下都有。饵重的时候,钓走街上的。饵轻的时候,钓走乡下的。”
“人们为啥会上钩?晓得会被钓走,为啥要上钩?”
“为了吃荤饵呀。吃荤饵呢,也不一定会被钓走。有的人吃到一点边儿就跑。有的人吃得深,但也能跑脱,只不过被钩破嘴皮。要吃荤饵,就得冒险。”
“为了吃饵,去冒险?有那么非吃不可?”我再次低头看饵,才注意盆边印着“薇薇烧烤”四个字。
“嗨呀,看来你没吃出来!”薇姐又递给我一颗。味儿变了。是老家的烧烤味。烤焦的广式腊肠在竹签上滋啦,咸甜扑了一层麻,混着葱姜蒜水的炭火焦香,咬开嘴里淌油,喉头急不可耐想要一口冰啤酒。
“你心头想的什么滋味,饵就是什么滋味。你要求低,吃打窝的素饵就能满足。你要求高,只能靠荤饵才能满足。”她说到此,嘴边一撇惆怅转瞬即逝。街边亮起路光,薇姐的睫毛在眼角投下一片阴影。我想起她结婚时,司仪问新郎最爱她哪个五官,新郎说睫毛。在来宾一片哄笑中,司仪请新郎亲吻薇姐的睫毛。“风越大,饵越香。”
我忍不住笑:“风越大,鱼越贵。”
薇姐说:“我不是说台词,是说事实。起风的时候,饵容易飘。要被人吃到,必须够分量。”
薇姐从小就是个人物。小学同学说,薇姐是我们学校的校霸。我半信半疑,因为从没见薇姐打过架,按理说校霸是打架很凶的人。同学说薇姐很有势力,我不知道她的势力何在。
后来她爸开了养殖场,我爸在那儿投了一点钱,同时在那儿干活。我爸让我向薇姐学习。学她说话做事大方大气,十几岁就能跟长辈聊到一起。十几岁就能做一手好菜。学她每晚睡前默想:我今天干了啥事,我明天要干啥事……在薇姐茫茫多的优点面前,我一无是处。
“听说有混合口味的荤饵。”薇姐很激动。我正在想象混合口味是什么味,虾条锅巴混巧克力?麻辣滚烫混甜香?薇姐好似看破我自以为是的猜测,解惑说:“比如,找大钱混合当懒王,被尊敬混合当小人,家婆娘混合野婆娘。”
前方就是她的烧烤店了,薇姐远远叫了一声老公。从烧烤架里探出一张烟熏火燎的脸。不是骑摩托车的新郎。而是另一个追过薇姐的男孩。现在是中年男人,以前是男孩。爱穿球衣球袜,比我大四届,比薇姐小一届。男孩他妈早就看上了薇姐,买MP3,买手机,塞钱,一样接一样让男孩给薇姐送。薇姐没要。
“诶?”
“换了个。”薇姐晓得我要问啥。
“咋换啦?”我压低嗓门儿,停下脚步,视线穿透烧烤架玻璃的油污,生怕那边的男人正尖着耳朵听。“上一个呢?”
“被钓走了。”薇姐回头笑笑。
其 三 回
有时我回去,不以我的外貌,不以我的性格,不以我。比如我叫“陈小纷”那回。
名字是有颜色的。“贾铮铮”是黑咖渐变。“陈小纷”是白里一点蓝。
我穿了白色的中长款羊绒大衣,尖尖的领口露出蓝色的细线针织衫。身材很细,步子很快,把迎面的空气劈成两片风。地很平,湖很静。我不在喜悦,不在悲伤。
井镇的人们看见我,没有好久不见的冷场或热情。就像我和他们天天见,我只是一个刚下班的街坊邻居。只是一个看着长大的好孩子,成为实至名归的好大人。我没有错过井镇的一切,见证了街坊邻居的生老病死,参与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每个阶段同学的婚礼。我没有过更大的世界,但脚下有更粗壮磅礴的根系。
在他们的眼光里,我看到一个工作体面的我。也许是县医院最出色的外科医生。一个头脑最灵光的注册会计师。最铁面无私的女法官。不知道。但我很满足。不是满满当当的满足,是空空荡荡的满足。不为昨天郁闷。不为今天焦虑。不为明天迷茫。空空的,神志清明。
回家换上睡衣,挽起披肩长发,脖子后露出一颗黑痣。在砖瓦房的塑料壳镜子里,我长得像某个女明星,大眼睛。
第二天是周六。睡到自然醒,穿上粉色的卫衣,去湖边参加同学会。
野花和波光,在湖畔点彩成油画。清风握着柳条,蘸春水练习瘦金体。一群人里,有我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每个阶段的同学。
我拥有十足的拍照技术,能定格每一个精彩的瞬间。当一个男同学带着脏话的叫喊炸开草坪,我火速到他跟前蹲下,拍下他新买的球鞋陷在撒野的泥坑里。当一个女同学举着蒲公英,我瞬息站到白绒球的斜上方,抓拍下被她噗嗤吹来的一顶顶白羽伞。我教另一个女同学怎样把蝴蝶一样的蚕豆花别在耳后,怎样保持高中课间走廊上微笑的弧度……
当我热烈地欣赏眼前的一切,也有人悄悄欣赏我。他的眼睛似桃花灼灼,笑意让卧蚕饱满。他跟着我,给我参谋拍照的角度,帮我背双肩包,给我递给充电宝,递纸巾,递可乐。
我问他:“你是谁?”
“我!麦冬!”麦冬是陈小纷18岁时的男朋友。但他只喜欢过陈小纷一小会儿。“我们重新在一起吧。”今天他重新喜欢上陈小纷。比18岁时更喜欢,好像中间分开的十几年不存在。当初是他想分手,但他从不说分手,他满不在乎地耗着,等陈小纷把“分手”说出来。
我想撇开他,专心享受我的拍照。跟他多说一句,都会错过让某个伟大作品诞生的瞬间。我加快脚步跑开。好热,抖抖卫衣的领口,露出后脖子,没有痣。
没痣的时候,我是燕凡。燕凡爱社交,爱拍照,擅长制造热闹和色彩,轻盈而气血充足地活在当下。麦冬重新喜欢上的是这样的我。他曾想喜欢这样的陈小纷,但18岁的陈小纷学不会。也不屑学。陈小纷只喜欢一小部分的麦冬。陈小纷不喜欢那个只懂得喜欢燕凡的麦冬。燕凡不喜欢这个不懂得喜欢陈小纷的麦冬。
转眼到了周日,我有一场考试,考场在县里的高中。监考老师还是曾经的班主任,他老了,棋盘一样平整的头发里,白子围剿了黑子。他看我在试卷边上写下“陈小纷”三个字,说,你不是。
我是。我是燕凡,也是陈小纷。
这堂考的是数学。我并不怕。首先这几年我会了很多题,其次我知道自己可以全身而退。这是我在每晚的梦境里,练就的本领。也是我在生活中,保存脆弱内心的惯性。我知道,副作用是我一直没有迎来大的突破,好处是我乖乖活着,不会死。每当噩梦来临,我都会安抚身边害怕的人:别怕,这是我的梦。只要事情走向来到我承受的边缘,只需一个眼睛或身体某部位的行动,我就会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