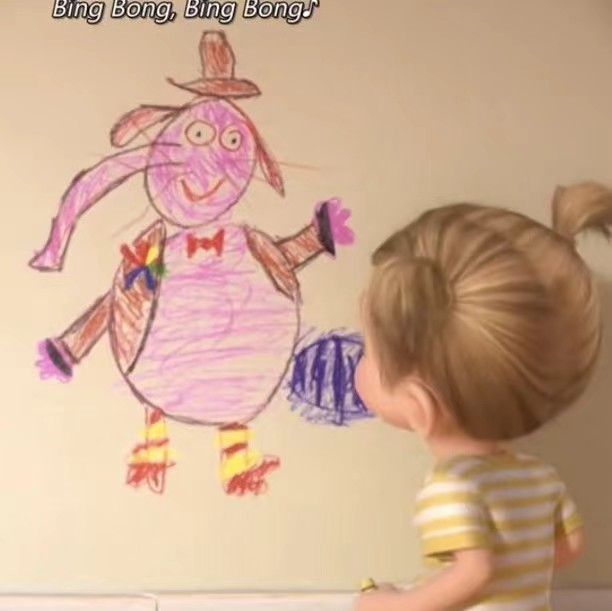香的两端,一头通向死,另一头孕育着新生。
香客们慢慢挪成三列,左升官,右发财,中间保平安。绯红色胀出了小汀的妆容,呼吸和抱怨被一遍遍沉沉地摔在地上:“哪里是最后八十一阶?明明长得很啊!”
我盯住脚下莲花石阶,只要前面那人一抬脚,就赶紧伸腿补空。
登完最末一阶,香火更浓,小汀问我:“是这里了吗?”
我从包里抽出宣传单页:“还没到,要翻过山的。”
“啊?”
“没办法呐,进山只有大光寺这一条路。”
我们去的灵福寺,是个很小的寺。怪得很,这座山以大光寺闻名,却叫灵福山,从唐朝就有记载。大光寺在山顶,古树蔽日,高墙连绵,香火极旺。翻过山,走七八百米,才是灵福寺,脚下小径也仓促句号。
我在佛学协会的杂志上看到灵福寺的广告,聘大学生做暑期佛慧夏令营的辅导员。
“连薪资都没有。”小汀瞪着我。
“诶,这叫积功德。”我按下报名热线的号码,“要不,你别来好啦?”
“哼,别想甩掉我!”
灵福寺确实小,且寂寥破落,只一座灵福塔出挑。青砖青瓦,底层回廊式,二至七层挑廊式,塔顶为八角攒尖,玲珑却雄伟。有些小孩子高喊,“冲啊!变身!”。不一会儿就白着眼跑回来,“烦死了!又上锁!”
“去年能上去的!”
“又不是藏金阁!我爸爸比他们有钱!”
“‘藏经阁’,经是书的意思。”小汀绷住脸面逗他们,“是放暑假作业的,你们还要上去哦?”
而屋前呢,是大片深深浅浅的水塘,屋檐垂雨,水洼摇晃,等候随滴随落的清净。有时,银杏树乒乒乓乓落下白果,让倏忽而过的飞鸟啄去,树上悬着的木牌随之晃动,“心香一瓣”四个红字原地舞蹈。除了几位常住香客,寺院人迹罕至。孩子们都不能投入循规蹈矩的生活,就在那水洼地里来回跑动,阵雨偶袭的微凉天气也能满头大汗。双手合十的僧人们穿廊而过,瞥见天真烂漫的小孩,也忍不住止步片刻,笑容从大殿里俯冲下来。
小小院落,这时候仿佛可爱无他。
明明同是辅导员,小汀却一步不离地跟着我。发学习卡,她贴在我后面,发讲义,她也贴在我后面,盯着手机屏,发短信向所有不看好我们这份工作的朋友抱怨:“山路真难走,蚊子能抬人,和尚一个都不帅。”
其实,帅不帅不重要,脾气差才可怕。“本来是不请女施主的,可今年的营员里有几个是女孩。往年呢,都放在旁边的疏林庵,但是她们这几天要迁址了。所以,只能拜托你们。”监院仁观法师神情肃穆,偶见他微微一笑,比一现的昙花更稀罕,即刻绽放,速而凝固,表情交接不露痕迹。“腾好两间房,你们带女生住。要记得,午觉睡下就不要随意走动了。”
但小孩子哪有那么驯顺?小汀已经把面膜敷在脸上,躺在那边翻美妆杂志。我只好把调皮鬼一个一个拉过来教育,不许这样,也不许那样。没几天,小汀坐收渔翁之利,和她们相熟起来,从背包里翻出几颗牛肉粒,就能收买人心。我心里隐隐不快,每天给她们拿书拿包拿鞋子的都是谁?哎,这么小就这么见色忘义,分得清美女和“普女”。
“你这叫——”我不清楚什么是更合适的词,搜肠刮肚憋出三个字,“大不敬!”
小汀立即反驳:“谁大不敬?昨晚在回去的路上,你还不是吃了烤翅?”
“那也不能在寺里吃呐。”我把包装纸从女孩们手里一一收回,藏进口袋里,“你们几个,吃好了就去睡觉,不准再跑了,听见没有!”
这些都是附近乡邻的小孩。大光寺香火旺,当然不会分出精力做活动。灵福寺的住持能度法师就看准了这个“市场空白”——送小孩来学禅宗,自然会捐些功德,小孩长大了,对灵福寺有了感情,自然会成为这里的香客,日后还愁香火不旺吗?年届七旬,竟然有这样的睿智和眼光,连潜在客户的商界理论也用得娴熟巧妙。
只是很多孩子都来过三四年,方方面面了然,甚至生厌。无奈家里人要么忙要么懒,没有时间看护,加上暑假无聊,在这里可以见到小伙伴,才被哄骗来。不出一个礼拜,小汀就从她们口中套出了和尚们的八卦。
“那个最凶的,就是吃饭时老是瞪我们的那个,像不像长了老鹰的眼睛?他老婆和别人跑掉了,肯定是被他瞪跑的。”宝妹对小汀说。
花妹正坐在床边抠脚丫,这时也抬起头来插话,“我奶奶说,他跑到大光寺烧香,想让他老婆回来,但是失败了,他就非要出家。大光寺里和尚那么老,那么厉害,才不理他呢,他就到这边了。我奶奶说,那个管烧饭的铁头陀也是老婆不见了,所以他们老待在一起疗伤。”
“疗伤”这个词,从八九岁的小孩口中冒出来,真让人好笑又费解,然而我真的佩服她们的想像力,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叫“鹰眼”,粗脖子大脑袋的叫“铁头陀”,还真是很贴切。
只听见小汀继续问:“仁观法师呢?”
“和林舒月大姐姐一样。”花妹漫不经心。
“是林舒月小阿姨!”宝妹纠正。
“是疏林庵的那个姐姐吗?”小汀说着,指指自己,又指指我,“我们都是姐姐,不许叫阿姨。”
“行啦,赶紧睡觉,下午要抄经书。”我给其他几个孩子掖好薄毯,“你们就不顾吵到别人。”
“明明是你们先问的。”宝妹和花妹异口同声,扭过身子不愿理我们。
“还没问那个最小的和尚。”小汀埋怨我。
“就不告诉阿姨!”花妹转过来补了一句,又生气似地转回去。
等她们睡熟,小汀说,“诶,不是离婚就是失恋,不是跑了老婆就是死了老婆,一点新意都没有。”
我暗想,呵,应该是没有“心意”才对吧?遇到难事,心情不好,烧烧香就突发奇想当和尚?不过,看破红尘还能因为什么呢?总不能都像新闻故事里写的,某宗灭门案的疑犯窜逃十七年,从香客变住持,还多次出国交流佛法,那样多骇人。
经文抄了半个月,心也没抄安静。没了好奇,斋饭好像也没有那么可口。又到了钟点,把小孩们排成一行领进斋堂,在长条桌长条凳前按固定位置坐好,开始念《供养偈》,报答佛恩,而后向寒林饿鬼施食——就是把几粒米饭撒到外面台阶而已!
桌上三只碗,照例摆成倒“品”字形,里侧是饭,外侧是汤和菜。四样菜,混杂在一只碗中,像忘了洗的调色盘,红烧抚触白灼,目测全是黑不溜秋。
“又盛这么多,哪里吃得完?”小汀才对我怨声,鹰眼的目光就载道飞来,扫射出一片红彤彤的光,好似在提醒——只给十五分钟,不能讲话,也不能发出咀嚼吞咽的声音——纯属强人所难。
刚捧起碗,铁头陀便踱过来,将菜碗和汤碗推至我们面前的桌沿,阻挡我们用斋时将碗放下。我小声对他说:“太多啦!”
“好吃!”他答得莫名,还挤眉一笑。
吃程过半,饱嗝就从嗓子眼儿溢出来,悬空端碗的右手承不住重量,不停地抖。大家颂“结斋偈”,我却只能把含在嘴里的饭菜慢慢压进肚里去。忽然想起小红帽中的大灰狼,最后被缝了满肚子石头,胀胀的心酸。
一出斋堂,铁头陀被小汀一把揪住:“不是都和你讲了,少盛,少盛一点!”
他委屈地叹口气,但还是弯着笑眼,“你们两个呆瓜,真会冤枉人。今天菜里有海藻,还有冬菇。那可是仁观法师去日本学习的时候,人家赠他的,就那么两小包,一直收着。觉得大家胃口不太好,才拿出来。我特地给你们多盛一点,换别人,才不会有这样待遇。”
我捧着鼓鼓的肚子苦笑,不知道自己是沾小汀的光,还是倒她的霉。
小汀仍不依不饶:“可是饭也多。”
铁头陀更像被咬的吕洞宾:“菜多饭少不怕咸吗?”
旁边一直沉默的小和尚这时意味飘忽地接了一句:“借花献佛追姑娘……”
铁头陀青黑的面颊恼成红黑,拿“去洗碗了”给自己解围,又气不过,一边走,一边扭过头来骂:“才来了两个月就不安生,信不信我现在就叫师父把你请出去!”
小和尚赶紧缝上嘴巴,默伴午后闷热的风。四四方方的庙宇,封住所有声响。又过了几分钟,他挪到小汀旁边。跑不动的风,是一种暗示。
他说:“下午别去抄经了。”
小汀说:“你说了能算呀?那我该叫你什么法师?”
他说:“我还没法号呢。”
小汀说:“那你这个光头是?”
他说:“天热嘛。”
小汀伸手去摸他的头皮,小和尚愣了一下,并没有躲。
突然,又有风涌过。
“明天疏林庵搬迁,要去人帮忙,你们两个去一下吧?”风是仁观法师带来。
“我们这边怎么办?”小和尚看看小汀,“总要留下一个吧?”
小汀看向我:“那就你去吧?”
我宁可盯住仁观法师的扑克脸:“应该怎么称呼那两位?林姨和舒姨吗?”几天前,她们来给孩子讲课,僧人们这样喊过。
“嗯。”仁观法师点头。
“就这样?”
“就这样。”
后来拼凑了许多版本的叙述,我才大致梳理清楚:疏林庵住了三个人,林姨、舒姨和林舒月。林姨年纪最长,有了她,才有了庵。她一直没嫁人,庵堂是她的祖宅。舒姨是外乡人,原本是大学老师,丈夫和女儿在事故中丧生后,她轻生却被人救下来,不知怎么就到这里来落脚,“疏林庵”三个字就是舒姨取的。
严格说,她们都不是尼姑,只吃斋念佛而已,但日子久了,乡民也把她们当尼姑一样敬重,有米有面有菜有油,都舀一点过去。虽然都已经到了婆婆的年纪,但还是被大家唤作“林姨”和“舒姨”,大概这样才更亲切。
最可怜是林舒月,她是弃婴。她们是在一个秋天的清晨发现她的,天空正在分娩日出,奶白的月亮浅浅淡淡,舒姨后来和一些香客提起过,她的女儿叫“宛星”,宛若流星,才舍她而去,所以她给这个孩子取名“月儿”,就算圆缺阴晴,总会陪着她们。
我赶到的时候,已经来了不少乡民,帮忙搬东西,功德箱、香炉、跪垫,一样样从一扇小门里往外拿。
我跨过门槛,走过三四米长的漆黑过道,进了院子。
里边的格局有点儿像四合院,中间做正殿,有佛像,而左右两边,一面是厨房,一面是储物间。正殿后面隔出一间禅房,林姨喊我进去,拿来海青帮我套上。照照镜子,才半分钟不到就立地成佛,一双沾泥的慢跑鞋却老是被不够长的袍出卖。
时辰已到,和大家一起搬佛像,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都是小小一座,被放倒,扛上肩,两三人分担一座,倒也轻松。
说起迁址,只因为政府要修路,现在的位置恰好在规划路线上。林姨和舒姨倒一点儿都没有挣扎,要是能把山这边的路也修起来,亦算功德一桩,不枉乡邻们多年照顾。于是大家商定,把疏林庵从灵福寺的西边挪到东边去。而我也是那时才得知,灵福寺的那一大片水洼地,本来也是要重修大雄宝殿的,但是疏林庵要搬迁,能度法师和僧人们一商议,钱就花到这边来了。路修好,或许香火能旺一些?先有香客,再有宝殿,这也无妨吧?话说回来,灵福寺和疏林庵是多少年的交情了?
就这样,一座新修的尼姑庵突兀地静立在那里,仿佛一夜之间从天而降。大殿里,新修的佛像高高矗立,底下供奉糕点和水果,宽大竹篾上,刚蒸好的寿桃馒头热气缭绕,与香火缠合,乡民进来庵里磕头,钱币扎入功德箱里磕头,散得叮叮当当。人们进出,泼洒笑声,让这搬迁更像个节日,恐怕连屠夫都已笃信,自己见证过这场仪式,不管信不信佛,都可自动获得庇佑,能好好地度过荒时暴月。
快到中午,我被叫去五观堂外帮忙洗菜,莴苣、土豆、黄瓜像一艘艘无帆的船,以不同的婴儿睡姿航行于一只巨大澡盆。林舒月蹲在一旁淘米,细长的身子一半泡在阳光里一半浮在阴影上。我把那澡盆往边上推一推,在阴凉地上腾出一个水印落款。
“舒月,过来点儿。”我说。
她一撅屁股,靠进来,脸上挤出一排白牙。可比小汀的白多了。
上了年纪的妇女们负责烧制,青椒莴苣炒豆干、土豆白芸豆烧素肉、黄瓜蘑菇炒木耳……一样样盛出来,装进饭盒。我擦干湿漉漉的手,站起来接过,正要派发给大家,却被林姨和舒姨拉到一边。
“那个……你有没有男朋友?”
虽然疑惑,但点点头。
“和你一起的那个女生呢?”
又点点头。心里厌恶,还真是八婆,难不成想给我们做媒?连尼姑到了这把年纪都要参与这么不讨喜的凡俗之事了吗?
“像你们这么大的女孩,是不是要有个男朋友才称心?”说完,望望林舒月。
我一下猜准她们的心思,不知道若点头还合不合适。
风烛残年,万事不关心,惟放不下一二要紧。话题熄落下去,哑得像雨伞忽地被收拢,却要滚动出泪珠来。吃饭的时候,她们仍把我夹在中间,也不管“食存五观”,却只剩“散心杂话”。林姨说:“月儿也不小了,以前,我就想把她留在身边,可是现在,想法不一样咯。”
“您舍得?”我的视线开动过去,飞驰到另一张桌,林舒月那用来招呼的生涩笑容上。
“我心里真的不愿意,但子女的人生是他们自己的,不然我们就太自私。看你这个样子,认为我会反对的,是不是?其实呢,还是我先提的,我没嫁过人,但不是不晓得感情意味着什么。”林姨很郑重地交代我,“你有没有适合的同学啊?不行的话,没有考上大学的呢?”
舒姨听到这话,显然不悦:“虽然是我自己教,但丝毫不比在学校念书的差!”
“和我们住在这里,她遇不到什么人,你们同龄人的交际,是不是能更广泛?”林姨有心讨好地看着我。脸上的皱纹好似天罗地网,让我无力招架,渐渐蜷成被吃定的网中鳖。
而那张网越收越紧:“我有时也去大光寺看看,来烧香的要么心里有人,要么心里有事,一看就不合适,怎么看怎么不合适。”
“但我舍不得月儿……”
“不是都商量好,这件事情迟早要办。”
“谁能确保物事长久?我们真的在老……”舒姨的声音颤动得像远处蜻蜓的翅膀,我的眼光躲得茫然,它们飞得这样低,又要下雨了吧?她大概看出了我的惧色,又语重心长,“我也没有别的期望,只要人老实,过日子肯疼她。”
营期过半,小汀借口打坐时伤到腿,告了两天假,其实趁着雨天公园人少,赶去和男友约会,结果发来短信:“没想到草地那么湿,根本没办法露营,只好回家煮火锅。”小汀问我,为什么暑假做义工而不去看男友,她以为我还在热恋中,其实我五年前就和他交往,不声张是因为没什么可声张的,双城记就是这种不温不火的停战模式,记忆里的甜蜜都可屈指,但诵经、抄经、禅坐、行脚,也会有他的名字在心里可数,任性暗涌抑或剧烈搅动。“啪”——这时,小孩就在脚边摔倒,仁观法师带着贴身的风冲过来,“你怎么还愣在那儿?”
附近有了亡者,僧人们赶去超度,休课一天。寺里仍守了几个孩子,我和还不会念什么经的小和尚留下看家。幸好有雨声,不用再说什么话题去织补闲寂空气,偶有香客兀然造访,氛围才徐徐暖融。
小和尚冲我眨眼:“你双盘好厉害,居然一个多小时。小汀三分钟就伤到腿,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
约会咯,我心说。
雨愈大,天愈显现出清亮的白。送走又一位香客,小和尚说:“你好像从来不拜?”
我说:“我不喜欢有所求,聚散不由人。”
“无所求,‘不向外力求,不为己身求’,师父常说的嘛,”他说,“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拜佛就是打个招呼,和说‘你好’一样。去试试?我给你敲罄。”
“以为自己是维那师?”
“反正师父不在。”
跪在垫上,闭了眼睛,“顺其自然,业因果报,坦诚接受”,不像心愿的句子,怔怔念了几遍。人像抽空一般,除了呼吸,什么都无法拥有。
“你哭了?”小和尚错愕地看我。
眼泪不绝涌出,湿了整张面颊。
“慧根呐!”小和尚晃着脑袋,“你去隔壁疏林庵落发吧,反正她们现在宽敞了,要人手。”
白他一眼,方才的真空心境撤离无存。
“你求什么啦?”这搅局者还在问。
“不求什么。”
升学、升职、恋爱、生死、团聚、离散,都是人生中的必然,为什么要去祈祷?忽然间,我却想起林舒月,收拾完饭桌,她坐在那片阴影里拨念珠,宽松的肩膀支撑一张苍白的脸,却还是透出一点清奇的好看。我那时真想走过去,“你在求什么?男朋友吗?”
已到夏令营的尾声,下完所有的雨,就燥热起来,山也不可逃脱地泛起红晕,好像被夏色灌醉。
林姨和舒姨送了绿豆汤来解暑。我说起小和尚的谐趣注脚,林姨说,“拜一拜也好。歪理是歪理,也许就有了正途。讲歪理的人内心都有缘故,轻易不示人。”舒姨讲得更加玄奥,“西方诠释学有‘衍义’之说,古人有‘诗无达诂’之谈,道理呀,因时因人而生出歧异……”铁头陀在一旁听见,抱紧了脑袋,“哎,又来上课了……”
临走,她们送给我们一人一个手工制的平安符,红符黑字,正面写“众缘和谐”,背面写“子德芬芳”,底下系个平安结,小汀喜欢得不忍释手。小和尚见了,便兴冲冲跑过来,对小汀说:“我的这个也给你吧。”
经念百遍,孩子们依旧吵,小汀和男友煲电话粥,午觉像绞肉一般,被砧成一粒一粒,迷糊之境,心跳得哀沉,像是深夜雪地里的脚步,一下一下扎进没过膝盖的白。我再不想和小和尚说话,他走来,我就绕开。经过走廊另一头,看到门外的过道上整齐地摆放着几双罗汉鞋,忽然想到自己不久前曾经好奇把脚伸进去。回家路上,又贪恋起烤翅来。
最后一夜是传灯法会,善男信女挤进寺里,像萤火聚圆又散成一线,手捧莲花灯,莲花处处开,亮满整座山,“南无本师释迦摩牟尼佛”,诵了一路。风有些大,摇曳的羸弱烛光去帮那些焦暗的病危灯芯,刚刚碰面,就都熄掉。小和尚拿着打火机,跑后跑前。
“你们猜能度法师的灯为什么不熄?”他帮小汀把莲花灯点燃。
长长人流的最前面,火光始终通亮。
“佛祖那么偏袒他?”小汀揶揄。
“仁观师兄一直拿着打火机跟着呀,一对一服务!”小和尚大笑,又来点我刚灭掉的烛火。
“小孩子的就不要再点了,反正发了手电筒。”我伸手护住重燃的火苗。
“你终于肯和我讲话了!”小和尚把我拉出队伍,“为什么好几天都不睬我?”
“为什么把平安符给小汀?”酝酿了好几天,鸡翅皮都噼噼啪啪焦黑了十几串,这一口反咬得自然干脆。
“你也喜欢?”他刚一嚷,就被我的阴沉脸孔斥住,赶紧压低声音,“你要是喜欢,和林姨多要一个不就是了?林姨那么偏心你。”
“那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我扭头就走。
“都是她们自己做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在后面继续喊,“好、好、好,不一样!那有办法……弥补吗?”
“带我上灵福塔。”
“啊?”
“带我一个人。”
它像一口枯井,倒立在地面上,仄仄的木质楼梯吱吱呀呀,越想一口气爬上去,两腿越觉得沉重,小和尚跟在身后,怎样都甩不掉。墨色加持的寒气从那些石壁里汩汩冒出。
“我费事拿来的钥匙,你说不爬就不爬?”小和尚逐渐逼近翻脸的边缘。
我受不了那张玩世却不乏恭敬的脸,非要偷取一声谅解。
“你根本就没明白!”
“无理取闹吧你就!”
“对啊,就是无理取闹了!怎么样!这段时间,应该是我工作比较尽心吧?应该是我比较了解佛法吧?我以为在寺庙里,至少应该有点什么不一样!”
一尊尊斑驳的石佛像,谁也没有背过身,就那样缄默地看着我和小和尚的对峙,尘埃原是肆意泼辣,这时却庄重起来,都老老实实定格,不再淘气叨扰,不再敢去让人心头一痒,鼻子一酸。
我把火发在这个快要散架的面庞上,想起他。
一个暑假了,也没有想来看看我?反正每个暑假都当各种各样的义工,反正每个节假都只这样过?反正不欢才在聚散故事里久演不衰?反正开学以后,这一页就翻过去,也无须折角留念,闹崩就闹崩吧!
直到秋天,我才意外地回收了安慰,和小汀同时收到小和尚的短信,态度诚恳,一字不差——“后天要走了,明晚见你们一面,好吗?”约在大光寺的山脚下,小和尚翻了山来会我们。远远看到他瘦瘦小小的身影孤零零立在那里,像块半生的年糕等着捂烫,小汀有些心慌:“之所以还俗……是不是……被我们在暑假搅扰的?”
没有路灯,偶有加夜班的卡车飞驰而过,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颠簸出奇幻的尖利。不晓得是忍受了蚊虫叮咬,还是吞吸了飞扬尘土,小汀看起来躁郁又低落。我们都没什么话可说,车灯一次次把小和尚的影子投射在四处,像小时候看过的皮影戏动画,此刻站在心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平安符给我:“我去疏林庵要了一个,我说的是,我自己要的。”又说,“你们常回来看看大家,这几天,师兄们都念叨着呢。”
小汀说了整晚惟一一句话,两个字:“你呢?”
他冲我们笑笑:“找别的工作啊,当和尚这活儿好像不适合我,又挣不多。不过也没有白当,交了好多朋友,高兴时,我还会念段好听的经文。”
快要中秋,月色的音量被拧到最大,掩盖了卡车的鸣笛,也送远了小和尚离开的脚步。
我还是与男友和好了,托他一起帮林姨问了许多人,他的一个同学表现出兴趣,我回去告诉她们,但忍不住提示:“是人类学专业的,成天做什么田野调查,不晓得要不要提防?”舒姨马上甩手:“我们才不见。”话风传到灵福寺,连鹰眼都跑来怨我:“这样心思不纯,赶快回掉!”只有林姨宽慰:“你最细心,麻烦再多多留意。”
这几年,新的志愿者都是我负责校招和培训,有时他们打电话给我,“这里的汤怎么这么咸”,我就晓得,铁头陀又放了两回盐,可是大家都装不知道。有几年的腊八节,我去给他帮忙,两个人对面对,我放碗,他盛粥,不言不语,偶尔撒出一点,他才“啊”的小声懊恼。
送粥的时候,他盯住善男信女一双双手臂,猝不及防地问我:“小汀怎么样了?”
“都说了好多遍,嫁人啦。”
“嫁给谁?”
我不想理他,同样的导火线要烧十公里,他才能惊爆般记起来。只和他说:“她家宝宝夜夜哭,都去电线杆贴告示了,‘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
他这回却接得快:“会哭的小孩长大后才有人情味。”
而后,锅就凉在那里,好似冷不防地硌着他的美梦。
我分手的时候,鹰眼特地告诉我,去把那些旧物旧言,要么扔掉要么删除。
“煮熟的鸭子能飞,真是一点也不假!喏,你就是一棵树,你想这样长吧,偏偏这边挨一剪刀,你想那样长吧,偏偏那边又挨一剪刀,你想怎么过,就不给你那么过!怎么都过不好!”
“我快被你剪死了。”我冷冷看着那棵秃树。
他放下剪刀,又恢复成扫地僧的样子,清理满地的枝杈,“你别去打小报告,我剪自有我的道理。扫掉,忘掉,干干净净。”
其实我知道,他还藏着二十年前的老照片,它们现在就和他的牙一样,泛黄又缺口,默不作声,总在心里尖叫。
只不过,林姨和舒姨见我那么心碎,反倒杯弓蛇影,为林舒月的事情争过几次,竟也不再拜托我……
我想,该写的我都写了吧,所有的相逢也常常是潦草收尾的。可时间是一个巨大的容器,所有的浓缩和所有的稀释都骤然间释放,劈头盖脸就扔回生活。
我没有见到林姨最后一面,这大概是近几年里,最遗憾的一件事情。我再次回到这里,院子里的草木都已长得胖乎乎,也没人打理,暴晒之下,垂头的垂头,疯长的疯长。
林舒月一见我,就把海青从柜里拿出来,让陪了整个早上的几位居士去休息。来吊唁的人并不比那次搬迁时候帮忙的人少,但进来,出去,一个个击鼓传花一般地哭过,就告辞了。是见林姨最后一面,亦是来递一句安慰,生怕舒姨又要想不开了。他们或长或短地和舒姨说过几句,却发现她前所未有地干练和镇定。舒姨一次一次站起来招呼,招呼完就坐回去。
到了晚上,她才开始目光迟滞,我们都以为她累,叫她睡一会儿,她说:“这种场面你们没经验,不晓得怎么应付。”一听这样的话,林舒月就绷不住了,砰地一声跪在地上。
舒姨说:“你们回去吧,你们都回去。”
我说:“可能赶不上夜班车,留下算了,反正明日还要忙超度的事。”
林舒月也不肯走,我才晓得,她已经搬了出去。
就搬进了原先那个四合院——反正政府后来都没有再提修路的事。
夜凉得小心翼翼,夏虫也闷声不叫,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仿佛都要蹑手蹑脚。舒姨好像个枯了枝叶的花盆,焦裂泥土被人们哭进一点泪,就不动声色地沉一点,直到很晚很晚,连夜归的鬼魂都轻柔罢工,这些泥土才彻底稀释,瘫成一团,老泪纵横,蜷在床上,米水不进。
送别林姨的场面很素洁,大光寺也来了和尚,这时却成为主力。能度法师和他的散兵游勇已把《无量寿经》念得呜呜咽咽,念得像一封封长信,也有时,念得像一封发霉的情书。好多乡民后来都说,那是他们念得最好的一次,把疏林庵念成了人间情味最浓的地方。
休息的时候,仁观法师对舒姨讲:“不管去了哪个世界,也不是这个世界了。从小喝的绿豆汤,今年说没就没,才是真的没了……”
舒姨说:“我一直说,‘肯定是我先死’,虽然小几岁,可是我腿也不好,心脏也不好,眼睛也不好……哪里晓得不好的反而成‘老不死’了……‘老不死’才最不好……”
我的视线一瞬间失焦,等擦干了泪,突然见小和尚打坐在那里,和僧人们一起念着。他的头发剪得好看,像雨过天晴的一轮月圆。
晚上,舒姨让我回去,又让林舒月跟着这轮圆月回去四合院。我才弄清楚,那也是不久前的事情:小和尚好不容易攒够首付的钱,回来捅破这层窗户纸,舒姨却说,她唯一的愿望是——“不要月儿离我太远”。
小和尚对我说:“其实这个媒总归还是你做的,那天我来讨平安符,当时没觉得什么,后来每次想要念经,念头就深一点。”
我哑在那里,真想把鹰眼拉过来,和他说,喏,剪掉枝丫,不是还可以长出意想不到的新芽,“意外”里面也有好的啊,干嘛想不开当和尚?但我明明也一样,醉生梦死在过去,锯不断。
每年祭日,能度法师上坟,舒姨就走得远一点,让他和未进门的嫂子,还有去替他当兵的哥哥,静静地待上一会儿。那天,林姨的事情都办完,舒姨才对我们说:“林姨什么都为自己考虑好了,就葬在那个人身边。阿弥陀佛,死了那么多年,她终于可以活过来了。”
生活中持续着窸窣的声响,狼吞过暴风雨的大海也露出和往常一样的平静。舒姨就走得远一点,走到她给亡夫和亡女迁来的墓碑前,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土地小腹隆起,像是生命在其内孕育。
那里的草越来越丰茂了,每一个叶片,都长着两只眼睛,看看人间,看看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