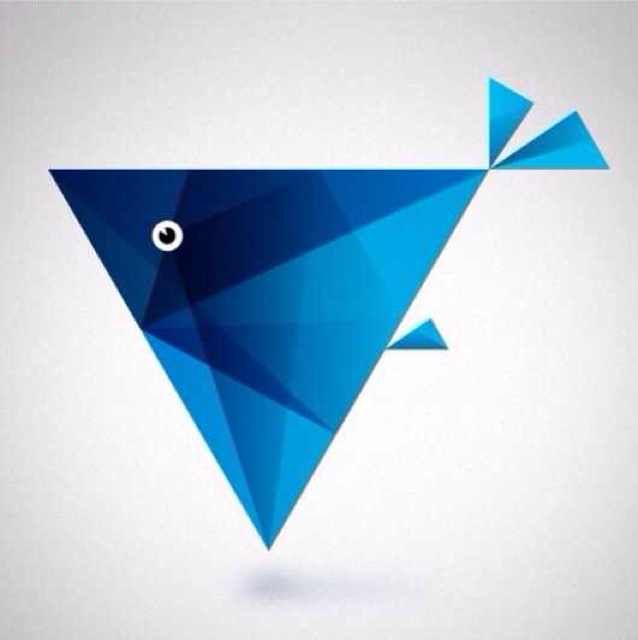一、透明翅膀
我听到一个孩子的尖叫,那突如其来的叫声将我带到多年前的一个午后。他在村外的麦场中间,一边跳着一边指向远处的天空,焦急地向我嚷着。我感到奇怪,他跳得很高,落地时却没有一丝声音——落地的那一瞬间似乎丢失了重量。我顺着他的指引望去,看到北面的天空飞来一片黑压压的蜻蜓。它们速度很快,好像被一阵风追赶着,转眼便飞进了麦场,悬停在我们四周。扑啦啦的振翅声突然升起,弥漫在整个阴郁的午后。我用眼睛看其中的一只蜻蜓时,它便快速地飞远,我不住地转头乱看,它们便像炮弹一样被我一发发射出。村庄和田野全部被蜻蜓群包围了,空气中全是潮湿的气味,我似乎看到远方的一条河流已经复苏。
那个孩子早有准备,他举着一把扫帚,在麦场上快速奔跑,很轻易地捕捉到了许多蜻蜓,用狗尾巴草串了长长的一串儿。他每捕捉到一只,便将手高高举起,向我炫耀。我两手空空,于是爬上场边的柳树,折了一根粗粗的柳枝当作捕捉的工具。我开始在麦场里胡乱挥动柳枝,学着他的样子不停地跑动。整个下午我都在追逐着它们灵动的身影。我使劲呐喊和奔跑,有几次几乎要捕捉到它们了,但它们总能飞出更诡异的路线,从容地逃之夭夭。于是,我产生了怀疑,它们可能只是一些影子,那些运动的影像可能是我天真的臆想。那个孩子临走的时候,再一次向我炫耀,他在我转身的瞬间消失了,我急忙转头,再没看到他的身影。
黄昏已经到来,我停止了奔跑,那些蜻蜓在我停止奔跑的一瞬间纷纷向远处飞走,逐渐飞入远处的混沌。半天的时间毫无所获,使我有些生气,我使劲将柳枝扔向远处,慢慢返回家中。天空中的云层似乎更厚了,整个村庄被沉沉压着,晚间可能会有一场大雨。
我看到一个奇怪的村庄,我一步步走过去,它便开始从昏暗中浮现。我按着记忆找到了我的家门,街门向东开着,比黄昏更黑的是两扇老旧的木门。院中有了油灯的光亮,整个院子都在轻微地晃动,我喊了一声,母亲便站在了屋门口,笑眯眯地望着我。奔跑了整个下午,我突然感到口渴难耐,那口靠在墙边的水瓮被挪走了,我不知道去哪里喝一口水。我开始在院子里转着圈寻找,才发现许多东西都挪动了地方。一棵曾被砍掉的树又重新长成了新栽种时的模样;一只羊从圈里伸出头,狠狠打了一个喷嚏;一条黑狗使劲低着头沿着墙根儿溜进院子,仿佛做了天大的错事;几只鸡昂首挺胸迈进鸡窝,跳在一根横担的木棍上。
母亲开始在院子里走动,她发现了我的身上有些异常,便将我叫到近旁。她让我转过身去,从我的背上抓下一只蜻蜓。我既惊讶又兴奋,和母亲一起在油灯下观看蜻蜓。它的样子有些吓人,翅膀不停地扑扑扇动,我便觉得它会咬我的手。母亲将它放在屋里的窗纱上,说它会吃掉屋子里所有的蚊子,我们将有一个安静的夜晚。
那个夜晚,我久久不能入睡,一直徘徊在睡与醒的交际线上,整个世界变得飘忽不定。我看了一眼安静的蜻蜓,它一动不动地趴在窗纱上,再看一眼,它的翅膀似乎变大了一些,再看一眼,我竟觉得它的翅膀有蒲扇那么大。透过它的翅膀,我看到了院子里的夜色。我听到越来越多的蚊子围着我乱叫,便开始喊我的母亲,喊了三声她还在睡,我就缄口不言。
天亮以后,蜻蜓螂消失了,我找遍整个屋子也没找到它的影子。我跑到院子里仰头望着天,望到满天的雨云正在聚集,它们不住地涌动,像烟囱里冒出的浓烟。我不敢走出家门,又开始喊我的母亲,没人回应我便知道她不在家。那些家禽都去了哪里?整个院子空空荡荡,像多年无人居住。我正要出门寻找母亲,天空突然下起了骤雨,整整下了一个白天。那是一场熟悉的雨,我应该在那场雨中行走过,又不敢确定。那场雨的雨滴出奇大,雨声却出奇小,大地像棉花,稳稳地接住了嗖嗖下坠的灯泡。
二、燕子来时
骤雨使村后的大坑涨了半坑水,青蛙叫了一夜。夜里的村庄被青蛙的叫声分割成许多层,近处是厚厚的一层,远处开始七零八落,更远处慢慢沉入了一片寂静。我醒来好几次,每一次都觉得青蛙的叫声离我更近,甚至觉得有一只已经爬上了我的屋顶,“咕咕呱——咕咕呱——”不停叫着。
天亮以后,我来到坑边,期待着能捉住一只青蛙。但它们听到我的脚步声后全部跳进了水里,在一串串涟漪中向着对岸游去,靠岸后使劲一蹬后腿,蹲在岸上,喘着粗气望着我。我感到很失望,我的木棍敲不到它们,便低头在草丛里寻找一些土块或石子。
我不停地扒开草丛,一只燕子突然飞起,猛烈地扇动翅膀,草丛被打得东倒西歪。我吓了一跳,急忙退后几步,看到它又落进了草丛。我再一次凑上去,终于发现它的腿被一团乱麻缠住。我开始对巷子里纺麻绳、纳鞋底的妇女们产生厌恶,小声地埋怨着她们。
那天之前,我从未近距离看过一只燕子,我只见过它们在天空飞翔时快速掠过的黑影。雨前和雨后,它们变得异常活跃,上下翻飞着,追逐我看不见的昆虫。我追过它们,我在村后的路上不停跑动,整个村庄便开始上下颠簸。我气喘吁吁地坐在草地上,整个世界慢慢停了下来,它们早已经飞得没了影踪。
我将乱麻一点点从它腿上扯开,将它握在手中,它小小的心脏开始猛烈跳动。我将它举过头顶,一口气跑出了村庄。它始终闭着眼,像是睡着了,更多的燕子开始低低地绕着我飞,它们在一起辱骂我。四周无人,我便开始同它讲话,我故意将话说得晦涩难懂,它小小的爪子紧紧抓着我的手指,像抓着一截干枯树枝。
我问了许多问题,像问它,又像问自己,最后变成一下午的自言自语。天空低低地压住我的头顶,延伸成一幅触手可及的图画。我的村庄变得更加矮小,那些返回村庄的村人变成暮色下的蚂蚁。我使劲将燕子扔向了天空,它有些吃惊,下坠一段距离后,猛地升起,头也不回地向远处飞去。我在后面追了几步,便停了下来,我本来想喊两声,但那一瞬间我只是远远地望着。
从那以后,我总觉得它在天空看着我,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了许多年。我常常看到一个安静的小院,许多燕子来回飞舞,它们不落在院中的树上,只是快速飞来,在我没来得及辨认的时候又快速飞远。燕舞莺歌的白昼变得漫长,帘幕无人,空留下宁静的门宇。
有一年,我惊喜地发现两只燕子一直在院子里飞进飞出,屋檐下多了一个燕窝。我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偷偷在屋檐下安了家,却感到自己与它们是老相识。我时常站在燕窝下面张望,有时也喊一声,引得它们变得焦虑而不住地盘旋飞舞。
公燕每天不停地飞进云层,又带着满嘴的虫子从云层飞下来,我开始相信云层后面也有一片广阔田野。它以一种俯冲的姿态返回燕窝,接近燕窝时又使劲扇着翅膀减慢速度,最后总能稳稳地站在燕窝边缘。这时的我躲在一扇窗户后面,透过玻璃看到的景象有些模糊。我趁着公燕飞进云层时搬来一架梯子,缓慢爬到燕窝下面,仔细听里面的动静。我什么都听不到,燕窝里面始终静悄悄。我开始多次在梦中爬上一架梯子,许多乳燕的叫声从头顶的云层后面不断传来,我等了好久,始终不见一只燕子飞出来,一着急便从梦中醒来。
我见过它们并头言语,也听过它们激烈吵架,燕窝里始终没有孵出乳燕使它们开始相互埋怨。一只燕子飞走了,过了几天,另一只也飞走了。之后的两年,我都会挂上旧竹帘,但始终迎接不到老相识。后来我离开了村庄,燕窝一直空了许多年,听母亲说,那里住进了一窝麻雀。
三、流萤飞舞
那一晚,村庄里又停了电,只有月光为人指路。我低头跟在两个比我大的孩子后面,往野外走去。四野是一个无际的虫笼,黑夜远到天边。虫鸣从草丛里向上升浮,近处的叫声星星点点,远处的连成浓浓一片。我紧紧踩住他们的脚步声,趟开一路虫鸣。我知道他们要去野外捕捉萤火虫,但向着野外的小树林走去时,仍然有些胆怯。他们手电筒的光左摇右晃,他们微弱的说话声飘忽不定,他们看到小树林黑黑的剪影时跑了起来,我也跟着他们越跑越快,接近小树林时又慢慢降低速度。手电筒的光亮熄灭,我们猫着腰缓缓地摸进小树林,那里胆小的夜行昆虫纷纷隐匿自己的行踪。
我们分散开,各自小心翼翼地蹲进草丛。我隐约看到他们已经变成了石头。深夜恢复了原有的秩序。树木上,放松警惕的鸟偶尔使劲扑闪几下翅膀,它们不在夜里叫唤。一个小光点在远处缓缓升起,它在追着一些我看不到的东西,另一个光点在后面尾随着它。它突然熄灭了光亮,另一个光点便犹豫着飞向别处。越来越多的光点缓缓升起,开始相互追逐,一瞬间,远处变得杂乱无章。我见这是美丽的画面,自己也变成了一块石头。
他们两人蹲在不远处的黑暗中,有光点靠近时,便像青蛙一样弹跳出去,用双手合成一个笼。受到惊吓的光点快速地散开,不久又缓缓地汇聚。我蹲在原地,光点不来靠近我,它们似乎知道那块安静的地方有一只更大的虫。我开始向着一个光点缓缓爬行,伸出一只手等待它自投罗网,它浑然不知,在我的手心上方悬停了许久,终于被一个天降的笼缓缓合围。它开始在我的笼内震动翅膀,碰壁以后来回爬行。我没准备容器,我的双手合成的牢笼遮蔽了它的光亮,我仿佛捧了一件稀世宝贝。
我心满意足,便想赶紧返回家中。内心愈焦急,时间便显得愈加缓慢。我再一次变成一只静静伏在草丛中的大虫。我不能喊他们,我的喊声会扰乱深夜的秩序,我沉静缄默,开始独自等待。很久以后,他们终于从黑暗里站起,手中的玻璃瓶,像一个闪烁的灯笼。我跟在他们身后返回村庄,在接近村庄时我们相互告别。我捂着光明,走回院子,对黑夜的恐惧从此便离我远去。
我又躺在那张小小的木床上,淡淡的月光透过窗纱。借着微凉的光,隐约可见昏暗环境中的屋顶和墙壁。我放开双手,它便重新升起,飘飘悠悠,像一颗缓慢的流星。它在不停地转圈,像涟漪一样一圈圈向外散去。我睁大眼睛,缓慢随它转动身体。它碰了几次屋顶便飞向墙壁,碰了几次墙壁便飞向窗纱,它伏在窗纱上开始休息,明暗的交替让我觉得它在大口呼吸。屋子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囚笼,院中的星星在召唤它。我突然觉得它不属于我。夜晚是它的天空,它是天上的星星。
夜已经深了,我推开窗户,它便飞了出去。我用目光追了它许久,它飞得比梧桐树还高的时候,我便觉得天上多出了一颗星星。星星晃了几下,静止了。
四、满沟蝴蝶
我又看到了那条两人多深的土沟,沟底长满了齐腰高的茅草。一只蝴蝶在我的前面飞了很久,它终于累了,落在了一棵茅草的尖上。我伏低身子,悄悄地凑过去,趁其不备,猛地一扑。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只蝴蝶惊起时变成了两只,两只又变成四只,四只又变成八只,转眼间整条沟里便飞满了五颜六色的蝴蝶。它们轻微而富有节奏地挥动翅膀,忽闪忽闪地,像满树的叶子在晃动。
刚才并没引起我注意的白色花朵,一下子开满了整条土沟,在轻微的风下,整齐地摇着头。土沟在很早之前是一条河,河水干涸以后,河底长满高高的茅草。我爱来这条沟里割草,几镰刀下去就可以装满我的柳筐,接下来的一个下午,我便有许多时间去做别的事情。
蝴蝶飞起以后,见我站在原地,并未上前追赶,便又飘飘忽忽地落回了草尖上,降落的时候天空像下着一场五彩缤纷的雪,我的周围瞬间又回归了平静。我听到沟沿的土路上似乎有牛车的响动,一个老人吆喝牛的声音由远及近。牛经过时,低头瞥见了我,我也瞥见了正在赶车的爷爷。他将白手巾当成蒲扇,拿在手里不住地摇晃,走进远处的树荫,慢慢消失掉了。更多的人从远处的路上走来,全部又在树荫下消失,那棵树下似乎有一个敞开的洞口。
我喊了几声,声音只在沟底行走,爬不上高高的沟沿。我再一次喊了几声,声音变成了一阵风,吹动满坑的茅草胡乱摇晃。
我想爬出土沟,沟沿上有我家的棉花地。我开始小心翼翼地寻找一个斜坡,我记得有一个斜坡,可以从沟底爬上去,此时我却找不到它。我不知道自己如何走入了这个深沟,一个梦突然将我扔到了这里。
那群蝴蝶全部沉入草丛,我开始挥舞镰刀,面前的草丛被我割开了一条小路,身后的草丛又晃晃悠悠地长起。我的付出看似徒劳,像在收割着时间与空气。于是我又站在原处,开始思考整个下午的来龙去脉。我进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只有思想在运动,整个人已经像一棵草一样直直地站着。整个天空倒过来,所有景物都倒过来,我躺在了草地上,眼前的一切都变得那么虚无缥缈。
我拍了几下手,声音闷闷的,像在拍一口破锅,我便打消了大喊的念头,将许多话语隐藏在内心里。我的内心从没人能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无端地走进了一片梦中的草地,我的镰刀还没有锈蚀,甚至闪着光亮。
五、秋后蚂蚱
我没听到一声号子,甚至没看到一个人的劳作,秋收在一夜之间便完成了,田野敞开了巨大胸膛。天气逐渐转凉,蚂蚱的行动越来越迟缓。太阳升起前,它们只能缓慢地爬行,太阳升起后,它们需要晒很久的阳光才能使身体回暖,进而跳跃或飞翔。我总在适当的时候出现,手拎着木棍,脚踢着土地,口中念念有词,缓慢追赶着它们,像在追赶看见长度的生命。再飞一次吧,它们短暂的一生没有做出令人震惊的事情,那就再飞一次吧。
蚂蚱群飞起来很壮观,像一阵疾风卷起满地的干树叶,哗啦一声向前挪动一大段距离,我再疾跑几步,便会有另一股风。
我用极为夸张的动作猛跑了几步,面前的几只蚂蚱便惊慌地逃窜,我不想捕捉它们,只是靠夸张的动作吓唬它们。它们奋力滑翔了一段距离便纷纷坠落回地面。没有了庄稼的庇护,它们开始变得手足无措。那可能是它们最后一次飞起,一场霜降后,它们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它们没见过冬天,天寒地冻时,它们早已经变成相互拥抱的雕塑。
远处有一片忘记拔掉的棉花柴,那户人家懒惰的男人正在家中睡大觉,秋收以后他便开始冬眠。那片花柴孤零零地站立在广阔的田野里,成了一处难得的庇护所。我从不同方向将蚂蚱赶进花柴地,它们飞进去后我便停在花柴地的边上。我不愿进入,高举的花柴有可能撕破我的衣服,尖尖的花壳有可能划破我的手背,我就静静地看。它们有的在地面爬行,有的缓慢攀上了花枝,又在一个瞬间,一起静止了。
我从不同的方向走向那片花柴地,整个野外的蚂蚱似乎都被我赶了进去,再没一只惊起时,我便觉得冬天真的要来了。田野里的蚂蚱都找到了归宿,它们早已将希望全部产于地下。地下的呼吸声连成一片,与小麦一起跨越漫长冬季。花柴要在那里静静地站上一个冬天。几天以后,我再次来到花柴地的面前时,看到了一组组雕塑,每个花枝上都爬满了蚂蚱。它们相互拥抱着,变成更多干枯的花枝。它们一动不动,无声地进入一个冬天。我正要离去,一阵风吹动一地花柴,哗哗响着,我仿佛听到了生命的短暂与不熄、脆弱与强大、缓步与飞翔。生命已经在一个春天的脚步声里开始轮回。
六、空中跑道
那是突然飘起的云吗?我不知道自己在问谁,那个下午,光秃秃的野外只有我自己。放眼望去,村庄的微小房屋,玩具一样散落在几棵树中间。百草枯萎,云朵低低飘浮,天空便显得无限高远。雄鹰在缓慢盘旋,俯瞰村庄和田野,胆小的野兔只敢深夜出门捡拾遗落的草叶。
雄鹰飞了一会便藏进了云里,不久后云里飞出一架很小的飞机,从远处拉来一条线,线在空中逐渐扩散,变成更多形状变幻的云朵。我看到了一条空中的跑道,那是从村庄升起的一条跑道。不管是孩子时,还是多年后,我长久地记住了那条空中跑道。每隔几天便有一架飞机经过,那条横跨东西的跑道便再一次在天空展开。我知道天上也有一条漫无边际的路。我只远远地仰望飞机,我的父亲却近距离见过飞机,但他一直对我隐瞒了那件事情。
那是更早时候的一个午后,正在午睡梦中的我感到一架飞机贴着村庄飞过。屋子在轻微震动,屋顶开始簌簌落土。声音经过村子上空不久便戛然而止,我怀疑那架飞机遇到困难,迫降在村子东面广阔的荒地上。果然,没多久,一个灰头土脸的人扛着一个大号的摇把来到了我家院子。他与我的父亲相互打着手势,在院子中间交谈了很久。父亲用自己小一号的摇把,摇响了自己的拖拉机,载着那人向村东驶去。
我追出家门,没看到他们的身影,只看到一条空空荡荡的道路,路上飘着一溜黑烟。村里人赶到那片草地时,他们早已经离去,草地上留下了许多条轮胎拧出的深深的沟壑。父亲离开了村庄,在我看来,他驾驶拖拉机拉着一架飞机沿着新修建的柏油马路一直向东开去。一直开,便能开到渤海的边缘。
几天以后,父亲在一个深夜里走进村庄,村里人都说他将拖拉机停在村外很远的地方,自己悄悄走进了村庄。我正半睡半醒,看到他怀抱着一个大大的包裹,匆匆钻进屋里,将包裹往桌子上一蹲,一堆整齐的钞票便露了出来。我揉了一下眼睛,母亲便将那个包裹藏了起来,转手给了我一只会跳跃的铁蛤蟆玩具。
我一直等着父亲给我讲运送飞机路途中的所见所闻,但他始终不提那件事,像与那人做过一个永不泄露秘密的保证。我们偶尔谈话时,我故意将话题往飞机上靠拢,他便显得坐立不安,总会找借口结束谈话。我对飞机更加着迷,便经常在野外的空中跑道下等待飞机。
母亲又在喊我,村庄又开始在远处的昏暗中浮现。我感到奇怪,我从没听到过母亲在村庄里喊我,那声音轻飘飘地,一阵炊烟一样慢慢浮着。我不想回答,我觉得那是一个漫长的距离,我的声音丈量不出它的长度。
我没有翅膀,没有飞翔过,所有的飞翔我都心驰神往。我看到一年的轮回,便看到了年年的轮回,生命本质就是轮回。
我在那个下午开始久久地失望。我向村庄跑去,越跑越快,便开始拍打着双手,有风从脸颊往后吹。差不多半小时的时间,那条空中的跑道便弯曲、变形、飘散,慢慢和高空的云朵融为一体,整个天空变得触手可及又漫无边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