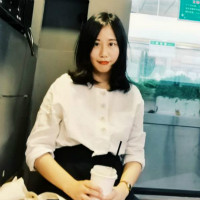1.
这是他们挪至这片山区的第七个夜晚。她的失眠并未痊愈,甚至有越发猖獗的迹象。她坐起身,抚摸了一下空空如也的胃部,手又不自觉下滑,移至子宫处。空的,都是空的,像一间又一间无人居住的房间,甚至连杂物也没有。
她下床,步入洗手间,拧开水龙头,静静看水流涌入灰土色的盥洗盆中。她伸出手,掬了点水,浇灌自己枯萎的面部——镜子里的那张脸干瘦、惨白,像是在沙漠中跋涉了数月的旅人。她“啪”的关掉灯,低下头,聆听自己在黑暗中的喘息,很明显能感到那是一头微弱的兽在濒死时发出的求救。
累月的失眠让她记忆力受损,她一度忘记了自己来到此地的原因,模模糊糊里,有几个画面窜出来——车是顾森开来的,她坐副驾驶。来时也是一个夜晚,空中并无半点星辉,狭长道路两边是高耸的山。车驶入蜿蜒道路时,常会遇到那种不见前路的瞬间,但转过去又柳暗花明。顾森握住她冰冷的手说:“试试吧,说不定有用。”
她是发了疯才会报名这个辟谷班,已经在这里饿了七天七夜了,除了进食过一些水、馒头和小枣外,她没有吃过其他食物,顾森有时会来看她,但多数时间还是留在市区里忙公事。大部分夜晚,她只能痛苦地蜷缩在床上,静待天明。
“是饥饿让我们确认了身体的存在。”
老师在课堂上言之凿凿地讲,现代人诸多疾病都源于营养过盛,人类对地球的破坏正在加速这颗星球的衰败,北极熊将在三十年后灭绝。夏季以来,北极圈多地发生火灾,这正是自然的旨意,警告我们要珍惜资源,极简生活。所以首先就是要抛弃你们吃的那些食物,你们的问题不是吃太少了,是吃得太多了。
她想起第一节课时,一个满面红光(看起来明显富态)的胖妇人没收了她带来的所有零食,那些食物被装入一个黄色大桶,被两名年轻男孩推了出去。又隔了五分钟,一个长须长发,道士模样的中年男子携木剑走上讲台,演示了一套行云流水的剑法,据说此人是道门中人,修习辟谷之术多年,身体朗健。就在她因剑法眩晕疑惑时,有人俯在她耳侧说:“这位道长在潜心修道前得过癌症,后来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痊愈了。”
她环顾四周,班上的学员老少皆有,男女各半。离她较近的男人凑过来自报山门,称自己叫罗望,是一名网站编辑,因深受失眠之苦,无奈之下报名了这个辟谷班,男人说完后又盯着她问:“那你呢?”
她精神有些恍惚,脱口而出“失眠”二字,那男人就仿佛久觅食物已久的兽,眼中闪过一丝光亮,逮着她继续追问:“你失眠多久了?”
多久了?她也记不清了。应该是从孩子从子宫中出走那日算起。一年前,她和顾森的婚姻走到了悬崖边缘,正在她以为自己要坠崖时,腹内忽然多了一个胎儿,这胎儿像藤蔓一样将她从岌岌可危的崖底捞起。但没过多久,那藤蔓就在一个深夜分崩离析——她流产了,原因不明,医生称或许与环境有关。
在那之后,顾森决口不提离婚之事,她便也懒得再大哭大闹。彼时恩爱甚笃携手创业的夫妻多半是这个结局罢?女主人一旦从他的事业中真正抽离,他便忘记了她当初是如何起早贪黑为他忙碌那摊事业。也不是不可以东山再起的,但总归难些,会有诸多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也许顾森还会请人炮制她是恶妻的公关新闻,这一切一切,都让她疲惫,但疲惫却不能将她带入睡眠。每夜睁眼等天明时,她都觉得是天罚。
2.
辟谷班为封闭式训练营,课程共分七个疗程,每七天为一个周期,总共四十九天。最初的几周会慢慢减少学员的食量,等到最后一期则是彻底的辟谷修行——只喝水,不进食任何食物。
白天,众人会聚在一起上课,上课时,要闭目,双手举起,绕过头顶。导师在讲台上念:“跟我一起,打开百会穴。”最初,她并不知道何为白会穴,还是罗望冲她眨眨眼说,“头顶,就是头顶正中央。”她皱眉问道:“那这里怎么打开呢?”
她想起儿时随奶奶上山晨练,每至半山腰时,奶奶便要在一个凉亭内停下来,朝她招手再见,示意其要留在亭内练功,这种功无需借助任何器械,仅仅就是这样,将手高高举起,闭上眼睛,感受天地灵气。
“感受到了吗?你们把宇宙吃进了肚子里。”
她差点就要笑出来,但还是忍住了,对于这种东方秘书伪科学,她向来没有兴趣,但不得不承认,在闭眼的刹那,她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灵平静,一种置身人群却仿若穿越山林的静谧感。导师介绍称这便是一种新的“吃饭”方式,不摄取食物,而是依靠吞食宇宙能量过活,久而久之,人的身体会适应没有食物的感觉,同时起到一种彻底的净化作用。
“吃完饭”后是打坐时间,他们的手机统一被没收,所能做的就是曲腿、盘坐在地上,望着远处那一座山。已是深秋时节,地上有些金黄枯叶,她喜欢坐在叶子上,这样会让她想起坐在莲花里的佛,直接接触大地寒气攻心,总要隔着些东西才好。
“看到了吗?观音的头露了出来。”罗望指着远处说:“你去过那吗?”
她摇摇头,谎称不知道,其实心里是在逃避。她当然去过那座寺庙,那是一座兴建于清代的庙宇,后在民国时期被烧毁,五十年代时重建,并逐渐扩寺发展。五年前,众人捐资,在寺内竖起一座高达数十米的观音像,而捐款名单里有顾森。那时他们的生意正遇到问题,她还碰巧遇见车祸,虽然车祸的代价只是骨折,但仍旧使人感到了命运的捉弄,也就是在那时,顾森耗了一大笔钱捐给寺庙,成为观音像的其中一位捐资者。自那之后,顾森的生意好像真的受了佛祖庇佑,逐渐有了起色,而代价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好像是一物换一物,彻底被牺牲掉了。
她低眉,想起殿内菩萨,菩萨为何总是低眉呢?她在一本书里看过,说是众生皆苦,菩萨除了不忍看,也是没有能力看才低眉的。这时罗望忽然避开导师的目光,偷偷朝她口袋里塞进去一颗水果糖。
在这里,藏匿食物是被明令禁止的。她记得刚进山时,在村口看见有人卖烙饼卷肉,她还流着口水说有机会去吃吃,岂知道进来后,不仅吃不到这乡野美食,连普通的食物都吃不到了。
她皱眉,用那种不发出声音的口语问罗望:“为什么?”罗望回过头去不看她,然后双手合十,对着那尊巨大的观音像说了一声:“菩萨保佑。”她停下来,看他的侧脸,觉得有些神似顾森,但顾森现在已经不这样了,他没有棱角,也没有轮廓,更不会偷偷塞给她一颗糖。
3.
罗望约她夜会时,她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这里谁也不认识谁,极适合露水姻缘,前天夜里,她就看见一名男道士牵着一个女学员的手,悄悄步入后山树林。她这个年纪的女人,没什么不可失去的,也没什么不敢尝试的,或者说,在这无聊而乏味的课程中间,她需要一个调味品。
他们先在一个废弃的仓库接上了头。
她择了一个木桶坐下来,身体摇摇晃晃的,罗望把她扶起来,让到一个长方形箱子上说:“坐这里。”说完,罗望又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火腿肠说:“吃吗?”她笑了,难道现在的男孩前戏要做到如此无聊吗?仿佛在一个延长线上铺满了心形石块,走上去硌脚。见她皱眉不食,罗望又从身上掏出了更多的食物——压缩饼干、巧克力能量棒、干脆面等。她静静看着他,像一个国王巡视前来献礼的异邦术士。
“你都不吃吗?”
“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这个?”她故意叉开腿坐,让裙摆中露出一条间隙,但罗望好像对此全无兴趣,而是恹恹说:“吃饱了才有力气出去走走。”
“我还以为你找我来是有什么别的事情。”
说完这句话后,罗望总算明白了她的意思,但他尴尬一笑道:“姐,我真不是那个意思,我……”男人说完将她的手捉至其下体处,她摸了一下,那里软趴趴的,像是还不放弃希望,她又使劲捏了几下,对方仍旧没有任何反应。她想起罗望之前说过自己的年纪,今年也才二十七岁而已,正是当打之年,怎么会这样?
“如果你真的不想吃东西,那我们出去走走吧?”罗望伸手,将她从木箱上拉起来,她拍拍身上尘土,随着对方步出仓库。去哪儿呢?她不清楚。未来要去哪儿,她更没有想好。抬头望向夜空,今夜月明星稀,也无高人给她做出任何指点。
罗望把食物又塞进宽大的外套内,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步入了一片小树林,树林边有微弱的光透过来,她恍惚进入了迷宫,似乎稍有不慎,就要坠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地狱。又继续朝前走了几步,能听到地上有一些滑动的声音,她不知道来自于蛇类,还是鼠类,这让她不安,不敢再前行半寸。
“到底要去哪儿?”
“马上,马上,一会儿就到了。”罗望把手电筒交给她,她握着手电筒,像握着一串光束,能自己发光的东西真好,可她只能借助光源,照亮前路。
走了五分钟,他们到了一处洞穴口,罗望把手电筒拿过来,扫了一眼地面说:“你看。”她循着光源方向望去,那是一尊又一尊凋敝的佛像,大部分佛像上的漆色有脱落,有一些上面沾染了烟火痕迹。
“这都是被遗弃的。”罗望拿起一尊无头观音说:“这些神像可能都是老化后被扔在这里的,还有一些或许是之前的供奉者信仰发生了变化,像我奶奶,前半生信佛,后来把佛珠和神像都扔了,改信耶稣基督了。”
她置身在那古旧佛像之间,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信仰被抛弃,佛像会坍塌,一切都在毁灭……她静静的望着洞穴外,那里有一些小生灵匿在树丛中,眼睛像天上掉下的星星,散发光亮。
罗望倚靠着墙壁坐下来说:“我以前是一个性瘾患者。我在社交网站上注册了几十个号,化用不同的身份,约过上百个女人。年纪最小的是初二学生,年纪最大的是一个五十岁的离异女人。最频繁的时候一天要约三个。那时候精力旺盛,喜欢的可以一天做五次,我都不知道自己哪来的精力。”
她定定地望着眼前这个清秀的男人,夜的光浴在他白净的脸上,让他呈现出一种圣容。儿时,她曾随母亲去过教堂,教堂里有一个黑布包裹的小亭子名曰忏悔室,那时母亲每周都要跑那儿去忏悔,她不知道母亲有什么话必须周周和主讲。现在,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间忏悔室,而那个年轻的男人正把头轻轻靠在她的膝盖上倾诉。
“后来呢?”
“后来有一次,我约了一个女人,比我大七岁,我对她没什么感觉,她似乎也对那种事兴趣缺乏。做完后,我穿好衣服,准备走,她突然拉住我说,可不可以留下来坐坐。我们这种人最怕的就是约来的人玩出真感情,要纠缠。于是我起身想逃。结果那个女的说,她得了绝症。她求我,求我和她再做一次,我挣扎了一下,还是开门,走了。”
“会不会是骗人的?”她把手电筒对准洞口问:“这种事也太巧了吧?”
罗望摇摇头说:“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她的死讯,死因是抑郁症,跳楼自杀的。发信人是她闺蜜,说这条信息是她特意让她发的,还说谢谢我。”罗望把头埋进两腿之间说:“我后来想,这种人是真的有病吧,我只是来约炮的,居然当我是菩萨。我救得了她吗?我连自己也救不了。”
她站起来,想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但起身时,高跟鞋踢倒了一尊佛像,后面的佛像也像多米诺骨牌般,尽数倒塌,她又蹲下来,忙不迭把那一个个无头的、断肢的、被削鼻的神像一一归位。
“其实我带你来这,不是想说这个的。”罗望指指洞穴深处说:“我是想告诉你,从这里出去,穿过这个洞,能到村口的小卖部,可以买点吃的,这个地方是我一个人发现的,他们都不知道。”
她看了一眼手电筒对准的方向,那里的确有一片刺目的光。
3.
山中一日,世上千年。
来到这里后,她时常感觉现实世界的渺远,好像彼时成长、生活的地方现在已融化成了一片汪洋。她常在下课后独自沿树林走到陡峭绝壁间,远眺对面的佛像,那隐在云层中的半截菩萨,永远低着眉。
那日夜会后,她和罗望的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她不再抗拒于和他接触,反而和盘托出自己的底细。她时常会提到顾森,提到对方近几年对命理风水的癫狂,比方说,没半年要找风水师来公司勘察一次,每隔一个月,公司所有布局都要调换一遍——鱼缸朝北不对,要移到西南处;沙发坚决不能和鱼缸挨在一起,会破财局……公司员工因此叫苦不跌向她抱怨,她也只能插科打诨过去说风水好了,公司赚钱多了,给大家涨工资。但工资到底是没涨,而员工流动率却增长了三倍。
“你很讨厌他吗?”罗望问。
谈不上讨厌,只是彼时携手共进的同路人现在像中了蛊毒一样——疯狂、偏执、不可理喻,他们几乎不能进行平等的交流与沟通。她有时会怀念彼此都还是穷学生的时代,一碗麻辣烫就能吃得开心,而现在,没有什么能让人开心。
辟谷班进行到第三期尾声时,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甚至连说话都要节省力气,罗望倒依旧精神奕奕,这显然和他偷食有关,但好景不长,某天中午,罗望被导师叫进办公室问话,没隔多久就怒气冲冲地跑了出来,对她说:“没了。”她这才知道那洞穴秘密早已被发现,现在洞口通道已经被彻底封死,这也意味着他们即将迎来真正的辟谷期——滴米不沾。
中途弃课的并非少数,不过有的并非出于自愿。课程进行到第二十三天时,某日清晨,众人来到练功的那片空地上,忽然看到一个男人把自己埋在土里,只露出半截脑袋,那时天光乍亮,男人的脑袋像是土里长出来的一样,众人诧异地看了一会儿,终于在导师的提醒下开始刨土,把土刨开后,只见男人浑身赤裸,神情恍惚。这个男人叫辉哥,在西北和内蒙古一带做矿业生意,有严重的头疼病,访遍名医无果,最后只好求助于这个辟谷班,人们猜测,许是平时习惯了大鱼大肉不加节制的生活,这突如其来的“饿”让他出现了某种幻觉。
辉哥被家人接走后,人心惶惶,有的人当即提出要退班,但导师告知,若中途退出,那一万块的培训款将不会退款。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导师从隔壁山上的万佛寺请了一个老尼过来诵经。
“你们要记住,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诚心,心诚则灵。”导师挨个给他们脸上洒上清水,称之为甘露,说药到病除。有人应和道:“行百里,半九十,再坚持坚持。”
她其实早就坚持不下去了,但顾森不来接她,她也找不到下山的办法。好几次,路过村口时,她都希望迎面进来一辆出租车,可是什么车也没有,唯一有的是村民的驴车,坐这种交通工具出去大概要耗上十天十夜吧,这让人绝望。
没过多久,她连散步的力气也没有了,每次练完功,只能待在床榻上叹气,有时候连叹气都显得奢侈,因为每耗一分气她就感到“饥饿感”在加重。
“吃糖吗?”
每次她快要坚持不下去时,罗望就递给她一颗糖。是水果糖,橙子味,用透明玻璃纸包装。吃完糖后,把玻璃纸留在手里,对着太阳或灯光一照,能看到七色的光。她像小时候一样,把那些糖纸一张张攒了起来,用清水洗净,放在房间内的台灯下。
渐渐地,她对罗望起了一丝窥探之心,而对方也对她毫无防备。某次下课后,她蹑手蹑脚跟在他身后说想进他房间看看,他也就大方爽快将她让进来,供其肆意参观。为了防止她生出戒心,他没有关房间门,而是拿一张木制椅子隔住了门与墙,以此表明其心迹坦荡。
“不用这样的。”她笑了笑假装拒绝,其实全盘接受了对方的好意。罗望和导师吵了一架后,情绪上有些低落,见她还在孜孜不倦的看这房间,找了个借口遁入卫生间——“我去刮刮胡子。”她说好,旋即像个侦探一样在房间内嗅来嗅去。房间里有一丝淡淡烟味和橙味混合的味道,像极了她过去爱用的那款香水,后劲十足,她拉开椅子,坐上去,把握着桌子上的水果糖,在那些细碎如钻石的小东西旁躺着一支黑色的笔。
她认得出来,这是一支录音笔。大学时,她念新闻系,实习采访时经常用到这个道具,那时的新闻业还没有如此凋敝,她盼望着做一个时政记者,但毕业后,同校学长顾森拐她去做生意,她便与自己的新闻理想渐行渐远。
他带一支录音笔来做什么?
她把录音笔打开,听里面的录音,一开始全部是一些诗歌,罗望有着迷人的嗓音,念那些外国诗颇为合衬,第一首是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 在哭我。
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 无缘无故在夜间笑, 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望着我。
还没来得及听下面的内容,罗望已经洗完脸走了出来,见她拿着录音笔,对方笑笑说:“被你发现了。”她也不退让,乘势追击问:“你来这里的目的和我们不一样吧?”罗望点了点头,没有回话,但她已猜出大概。学生时代时,有师兄卧底传销集团写出一篇震惊社会的新闻,后来在聚会上,她向师兄讨要非虚构写作秘诀,对方就说了两个字——“真实”。真实,这意味着记者要深入虎穴,拿到一手采访资讯,料想罗望也是如此。
“你是记者吗?”
“也不算,算半个吧。现在还有什么记者吗,据说全国登记在册的调查记者不足百名。”罗望拿毛巾擦干头发,身上散发出一股水果糖的香气。她想继续追问下去,又觉得浑身乏力。罗望见她这样,建议道:“吃颗糖吧?”她撕开糖纸,将那橙子味的颗粒塞入齿间吮吸,咀嚼,好像是在吮吸罗望的身体。
那颗糖吃完后,她就睡着了,她不知道是太饿还是太累,只隐隐约约记得自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4.
再次醒来时,已是翌日清晨,她发现自己睡了足足有十二个小时。房门还敞开着,有凉风徐徐进来,她的身上有一件男士粗针织毛衣。她揉揉眼睛,把毛衣挂到板凳上,环顾四周,罗望并不在。昨晚发生了什么,她已经完全失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是她自流产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一个觉。她感到体力充沛,甚至还能记起梦,梦里她变成了一头非洲象,在草原上缓慢行走,有盗猎者向她射出麻醉枪,她因此倒地,昏昏不起。
她步出阳台,眺望远山,清晨的雾霭将观音的脑袋完全隐去,什么也看不见了,远方一片混沌。在楼下的操场上,宽衣大袍的“同学们”聚在一起,像隐匿山间的谪仙。
她匆匆跑下楼去,加入了众人之间,罗望却消失了,仿佛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她摸摸外衣口袋,忽然发现口袋里沉甸甸的,多出了一只木雕观音像。
“要集中精神,接受最后的考验。”导师拿着书慢悠悠走过来,打了她的腿一下说:“坐下,坐下,打坐,你迟到了。”她心里还想着罗望的事,但放眼望去,遍寻不见。
她闭上眼,依照导师的意思感受天、地、风、气体的流动,味道的变化,她曾经听过一节课,说每个人都是要死的,在死的那刻,人又会回归天地之间,那时课堂上有人举手问:“如此说来,人活着其实毫无意义,是一个从虚无到虚无的过程吗?”演讲人扶扶眼镜笑着说:“你这样说是没错的,但我们必须赋予其意义。”后来每次遇到谎言、欺骗,对人生意义感到模糊时,她都会问自己,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呢?人给这一生赋予意义,是否只是为了骗自己活下去呢?就像这个所谓的辟谷班并不能真正医治好任何人,只是另一种行骗手段呢?
想到一半时,她睁开了眼睛,变成了一具怒目金刚。就在她起身准备离去时,忽然看到罗望缓缓朝她走过来。她又立刻闭上了眼睛,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
那日课堂上,他们彼此无言,说不清是不愿交流,还是饿得没有讲话力气。下课后,罗望也没有打招呼先行离去,她一个人绕到了后院,因为后院的树林里藏着一辆车。
她记得那辆车,车是顾森所购,一辆二手车,从前他们为了一件生意上的事杀过人,砸死人的是她,埋尸体的人是他。那案子做得漂亮,多年来无人发觉,但从此像一枚钉子刻进二人心中,她与死者无冤无仇,杀人纯粹是为了顾森,但现在说出去也毫无意义了,那等于将自己送进牢狱。
方才罗望回来时,裤腿右侧蹭上了油漆,和这辆车上新涂的漆一模一样,她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5.
她去找罗望,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对方对她的态度也依旧热情。
“我好饿,我们出去找找吃的吧。”
“好啊!”
罗望没有任何戒备,两人沿着旧路,闯进了山林。路上,一片黑暗,她并没有再胆怯,因为她心里已经有了一把闪光的刃。
他们缓缓走着,走了足足有二十分钟,终于抵达了一处坡地,远处,那尊几十米的观音像正低眉俯视着这片大地。
罗望在她身边踟蹰了一会儿说:“这里有什么吗?”她从身上卸下一个小袋子说:“这里,我这里有一些观音土,可以充饥,吃几颗就能饱腹。”
“观音土?”
“对,我之前健身的时候,为了减肥,就吃这个,饱腹感很强,吃了就不饿了。”她抓住罗望的手,将其手掌摊开,倒了一些观音土在其掌心上,罗望拿过去,半信半疑地吃了几口说:“有点点甜味,像小馒头一样。”
“嗯,吃吧,多吃一些。”
她拿起一枚观音土,在月光下照了照。十年前,她第一次和顾森踏上某个做瓷的小镇,拜师学艺,其中一名技工就曾经拿出这种土告诉她——饥荒年月,人们食草和树皮果腹,后来连这些也被吃完了,人们就找到了一种高岭土,吃一点就不饿了。找到这种土的人大喜过望,以为是菩萨显灵,救济世人,于是称其为观音土,谁知道,没过多久,有的人因过量食用观音土,腹胀如鼓,憋胀而死。
“这是世上最绝望的食物。你以为吃下去就好了,其实完全是假象。”
见罗望手里的观音土已经吃完,她又倒了一些到他掌心,对方向她投来感激的目光。她也擦了擦眼角边不经意流下的泪水,将那咸味的水喂进嘴里。远处,那观音不知何时已经换了一张金刚的脸,怒目,面对着惶惶草木。